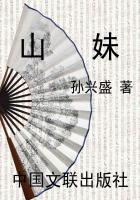丁楠的心一瞬间就乱了,她知道自己应该不理。但是,那时的丁楠却抑止不住地想去见他,想抱着他委屈地痛哭。于是,她站起来,又俯下身子对孙颜悄声说:“我有点事,得先走了,你帮我照顾下你同事。”又看了看李实,说道:“我有点急事,得走了,你俩先吃着聊着,我们回头再说。下次我请客。”
两人都有些惊异地看着她,孙颜很快恢复如常,说:“行,你去吧。”
李实也点头笑笑说:“回头见。”
来到餐厅门前的马路上,丁楠给孙国维拨了电话,尽量用平静的语气问:“你在哪儿?”
“我在你家小区外面的马路边,你在哪里?”孙国维在电话那头说。
“行,等着我吧。”她挂了电话,马上打了个车回去了。
半个小时后,她让司机在离小区远一些的地方停了车,下了车,向小区走去,一边走,一边想着见到他说什么。
他远远看见了她,她也看见了他,看见他仍保持着他那出世般的温厚淡泊的气质。怎么说呢,往日丁楠和一帮俗友聊天时,经常地,一个人会调侃另一个人说,瞧您这气质,一看就是大街上走的那种人。那么孙国维的气质呢,他走在大街上,会立刻让你感觉到他的不同,倒不是因为帅,就是气质,那种空灵绝尘的,那种清高隐逸的温厚淡泊,就如一轮素月。
她第一次见他时,觉得他疏离空洞,后来相处久了,观察多了,才觉得那更是一种空灵清高。但无论是哪一种感觉,他都实实在在给人一种诧异感。
孙国维对着走过来的丁楠问:“你干吗去了?”
丁楠不喜不悲,脸色平静道:“相亲去了,你能去相亲,我为什么不能呢?”
他的脸色变了变,一下子握住了她的两只手,摇动着问:“我都要为你疯狂了,和别人相亲,满脑子想的都是你,我不去见别人了,你也不去见了,好不好?好不好?”
“我们去你学校吧。”她答非所问地说。
“不上去了?”他仰头看了下她住的那座楼,问道。
“不上去了,你不怕被人笑话啊?上次走得那么狼狈。”
他说“好吧”,牵着她的手,两人向车站走去。
到孙国维的学校门口时,已是下午三四点的光景,初夏了,闪烁的光斑自西南方透过一旁的大树斜洒在两边的柱子和笔挺的哨兵身上,隔着铁门的间隙望进去,校园里绿树成荫,正对着的大道上偶尔有人走动,一切静悄悄的,很安逸的画面。
“军官证或身份证?”年轻的哨兵看了他俩一眼说。
孙国维掏出军官证递过去了,但是丁楠没带身份证。
“上两次来,没要看身份证啊,我没带呢。”丁楠看看哨兵,又看看孙国维。
孙国维于是向哨兵求情,“是啊,没想到要看身份证呢,能不能通融一下?只登个记什么的?”
“不行,里面出事后,最近都要检查的。”哨兵毫无表情地说。那张秉公办事的脸,一下子让丁楠想起了小时候学过的课文《列宁和卫兵》里的卫兵。
“那怎么办?身份证还在城里呢,回去取不现实啊,你就帮帮忙,登记一下吧。”孙国忠继续向哨兵求情,一边告诉丁楠,前几天,有个疯子一样的人在里面砍伤了人,所以这几天可能查得比较严。
哨兵毫不理会,不再说话,眼睛漠视着前方,专心站岗。
“喂?不行是吧?不行啊?不行给你们连长打电话,我就不信了,小子,我来这工作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呢。”孙国维见哨兵不理,急了,嚷起来。
“给连长打电话也没用。”哨兵说了句,但仍然不看他们。
“那直接进去,走。”孙国维说着,拉着丁楠的手直接往里走。
哨兵终于不淡定了,伸手拦住他们,说着:“不行!不能进!”这时从传达室又出来一个年轻的哨兵。孙国维还在嚷着让他们给连长打电话,两个哨兵说着让他们配合之类的话。
就在孙国维和两个哨兵力争时,丁楠突然感觉三十岁左右的孙国维和二十岁左右的年轻哨兵站在一起,竟显得那样的沧桑,她的心头升起深切的心疼和怜惜,那一瞬间,她发现自己早已体谅和原谅了他。
最后,后出来的哨兵无奈,只得询问了孙国维的情况,又看了下他的军官证,登记了一下,让他们进去了。
刚进大门不久,迎面遇上一个穿着军装的女军官。老远,孙国维就向丁楠介绍,这就是我经常跟你说的我的老乡兼同事王淑萍,她今年也考研了,也参加复试了,估计九月份也会去上。待走近了,丁楠仔细打量了一下眼前的巾帼英雄,和她年龄相仿的样子。孙国维给她俩做了介绍。
穿过校园低矮的灌木小径时,不时有男同事向孙国维挤眉弄眼打招呼,有人问:“孙国维,女朋友?”他就笑笑说;“嗯,呵呵。”
他的宿舍,还是那么的干净整洁,一如他的人。那时还不流行星座,多年以后,丁楠算一算,才知道孙国维也是处女座的,都说处女座的人有洁癖,看来不假。
房间里有两张单人床,一张床被子枕巾的叠放得整整齐齐的,另一张多堆了一些床上用品。靠窗户放着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桌上摆放着一些书和文具。门后面有一个衣柜,衣柜旁是洗脸架和一些洗漱用品。一切很简洁的样子。
孙国维曾说过,这个房间原来是他和同事好友肖伟同住的,自前年肖伟转业到地方后,就他一个人住了。
五点半时,孙国维去食堂打饭了,丁楠坐在椅子上看桌上的书,这时她的手机响了,她一看,是李实的信息,说:“丁小姐,我对你印象很好,我们可以继续交往吗?”
她一愣,随即回了一句,“对不起!”
半晌,手机又响了,李实说:“为什么要说对不起?我害怕听到对不起!我心不要对不起!”
丁楠苦笑了下,想这也是个有趣的人,没再回。
九点多时,孙国维收拾着那张放了两床被褥的床,一边对丁楠说:“这是肖伟以前的床,我收拾下,晚上我睡这,你睡我那张床吧。要不带你去王淑萍的宿舍?你看呢?我不会伤害你的!”
她伸出手,从身后抱住了孙国维,将脸贴在他的后背上,说:“不,我愿意!”
月初了,一轮皎洁的月芽挂在窗外的天空,月光如水般倾洒在屋里,窗前高大的灌木丛有疏落的阴影投进来,在地上形成抽象的光斑。一切那么安详。
他从身后抱着她,在她耳边轻声说:“宝贝,我爱你!”她没有吱声,他的手摸过去,摸到了她一脸的泪水。他把她的身体扳过来,面对着自己,连声说:“对不起!宝贝!对不起!”她将头埋在他胸前,渐渐呜咽成声。
周日上午时,两个人都很惆怅,眼睛都红肿红肿的,他把毛巾在冷水里浸了浸,拧了把,递给她,让她敷眼睛。她不时会失神地看着窗外,他看着她,眼里是歉疚和疼惜。吃完午饭,他说:“我们去市里逛逛吧,我们去逛华堂。”
两个人牵着手去逛了华堂,他陪她看女装和女鞋,说:“我特意带了二千元钱,想给你挑一些衣服,马上要去上研究生了,添一些新衣服吧。”
她连连说:“不要,不要,女人都只是爱享受逛街的乐趣而已,不一定要买的。倒是你,要出国了,应该穿好点,给咱中国人争点面子。”边说边把他推到了男装专区。
多年以后,丁楠常常想起那段话:一生至少该有一次,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不求有结果,不求同行,不求曾经拥有,甚至不求你爱我,只求在我最美的年华里,遇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