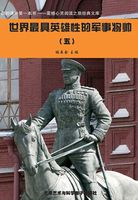董竹君(1900-1997),女,江苏海门人,女权运动先驱。13岁被迫沦为青楼卖唱女,后结识革命党人跳出火坑。因不堪忍受封建家庭和夫权统治,再度冲出樊笼开创新的人生,先后创办富祥女子织袜厂、飞鹰公司、群益纱管厂、锦江川菜馆,任旧锦江饭店老板。上海解放后,创立锦江饭店,并将自己的全部财产献给国家。曾任第一至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董竹君,称得上妇女中的佼佼者,关于她的身世,有种种传闻84岁的全国政协委员董竹君,一头银发,精神矍铄,曾住在北京东城的一座小巧而幽静的四合院里,安度着晚年。她有四女一男,三个女儿在美国,其中两位解放后曾回国工作过;三女儿一直在国内工作,现在也经常奔波于中美之间,想方设法为祖国四化多做些贡献。
她的儿子是党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虽然历经坎坷,赤子之心不变,如今健康情况差些,依然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奋发努力。董竹君自己呢,早已是静心养老的年岁。在美国的女儿们三番两次让她去住一段时间,因为思念她们,她终于风尘仆仆去到美国,但不满一年,尽管生活条件很好,女儿们也孝顺,她却住不去了。她在异邦又思念着故土,惦记着这座居住了二十多年的北京小四合院,更想赶回来参加一年一度的全国政协大会。她谢绝了女儿和亲友们的挽留,回来了,而且不打算再去。这是两年前的事。女儿们只得抽机会轮流回国来看望年迈的母亲。
董竹君何许人也?现在的青年人对她是陌生的。但是,在旧社会,在上海、四川一带,董竹君却是个颇有名气的人物,称得上妇女中的佼佼者。她在四川、上海兴办过若干大大小小的工厂、企业,特别是上海锦江饭店,她从接受他人义助两千元原始资本开始,苦心经营,由锦江餐馆和锦江茶室发展成为颇有名气的大饭店。关于她的身世、能力,在旧上海滩上曾有过种种传闻。如今,这一切都已变成一页历史。但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一个妇女何以有这么大的本领,成为上海锦江饭店这么大企业的创始者,经营者?特别是在斗争尖锐复杂、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岁月里,她头脑清醒,从争取女权、创办事业,到同情、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这又是什么缘故呢?
笔者对她的过去早有所闻。在经过若干日子的长谈,并翻阅了有关资料之后,被她的不寻常的生涯深深吸引住了。于是在漫漫冬夜,写出了这篇传奇,奉献给读者。
一只魔爪悄悄伸过来……300元“印子钱”把12岁的董竹君送进了“堂子”
今天的上海延安东路,七十多年前是一条又脏又臭的墨汁般的小河,土名“洋泾浜”,当时是上海英、法两个租界的分界线。在这条臭水沟的两旁,密密麻麻地拥挤着一间间低矮、破旧的小草屋。董竹君就在这里度过了苦难的童年。
董父是苏北人,逃荒到上海,当了一名黄包车夫。母亲是苏州人,以做零工、当娘姨为生。由于贫病交加,董竹君的弟弟、妹妹都夭折了。这位小名“阿媛”的机灵漂亮的小姑娘便成了“独养女儿”。由于这个原因,当父母身强力壮之时,起早贪黑地干活,居然让她进了一个收费低廉的私塾,读了几年书,粗识文字。勤快能干的母亲,在替别人做活之余,每天总把那间破陋的船篷草屋打扫得干干净净。年幼的董竹君,尽管一年到头难得穿一回新衣服,却总是清清爽爽,打了补丁也不碍眼,还有那聪慧的眼神,白皙的皮肤,穷邻居们都称她“棚户小西施”。吃的是粗茶淡饭,能不能沾点荤腥,取决于拉黄包车的父亲的运气。每天傍晚,小阿媛总是倚在低矮的门旁,等待着父亲归家。有时候,远远望见父亲一只手提着小瓶子,另一只手拎着小纸包或用根稻草吊着什么,她就会一面高声叫喊“阿爸”,一面连蹦带跳地迎上前去。经验告诉她,父亲今天生意不错,打了烧酒,买了荤腥,虽然不过是半斤猪头肉,或者几条银刀鱼。但是,更多的时候,父亲是肩头上搭着那条发黄的擦汗毛巾,拖着两只穿着草鞋的脚,垂着头,缓缓地走着,两手空空——小阿媛立刻像泄了气的皮球,知道阿爸一定触了什么“霉头”,拉车没赚到钱,或者赚钱不多……
小阿媛料想不到的是,就是这种辛酸的童年,就是这仅有的一点点欢乐,也会过早地被旧社会的魔爪一把揪断。
她10岁那年,父亲得了伤寒,长时间在死亡的边缘上挣扎。母亲为了照顾父亲,只能做一点点零活。三口之家,糊口尚且困难,又怎能看病吃药?
家中能卖的都卖了,能当的也都进了当铺,而父亲依然卧床不起。母女抱头痛哭,惊动了左邻右舍。但他们也是些吃了今天不知明天的穷汉,谁也无能力救急。这时候,一只魔爪悄悄伸过来了。他貌似同情,怜悯的好话说上一车,拍着胸脯出面作保,借给阿媛家“印子钱”。于是,10元、20元、50元……小阿媛啥事不懂,但父母亲则心里发毛了,何以有这样的好人呢?家里已经当尽卖绝,难道就不怕他们逃债?只是已经山穷水尽,也顾不得多想了,兴许真的遇上大善人了呢?他们也没有想到,人家早已看中他们的细皮嫩肉的小囡——阿媛了。
“印子钱”快借到三百大洋,父亲的病好转,瘦得不成人形,几乎连行动的力气也没有了,又怎能再去干老行当——拉黄包车呢。董家依然靠借债度日,生活一天天走向绝境。
一个阴沉沉的冬天的上午,小阿媛刚刚吃过多日不见的粢饭团。这是她最爱吃的,在父亲重病之前,差不多每天当早点吃了去上学的。已经很久了,她经常没有早饭吃,有时顶多喝点父亲养病剩下的豆浆,她不明白妈妈怎么舍得一下子给她买了两个粢饭团,她一口气吃完了才抬头,多久没有这样饱餐过了呵!父亲蜷缩着身子,靠在床帮上,母亲坐在床沿手捂着脸,谁也不说话。长时间的沉默,使小阿媛感到气氛异样。
“阿媛,爸爸对不起你呵!”父亲没头没脑冒出一句,声音便哽咽了。
“呜——”母亲终于克制不住,泪如涌泉。
小阿媛惊呆了,她扑向母亲,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阿媛,你莫哭,你是聪明的孩子,懂事的孩子,孝顺的孩子!你知道……”
父亲的泪水也夺眶而出,终于没有把话讲完。
不知过了多久,总之是谁也没有眼泪了,三双哭红的眼睛互相对望着。
父亲咬了牙,说:“阿媛,爸爸身子骨垮了,再也没有力气拉车了!爸爸重病两年,借了几百元印子钱,利上滚利还不清,再拖下去就要吃官司了。爸爸没有法子,眼看一家子活不下去了,只得……只得让你先去学唱戏,而后……而后……”
而后是什么呢,父亲的声音又哽咽得说不下去了。小阿媛虽然只有12岁,但已知道许多事。她早从大人的嘴里得知,离这儿不远的四马路有许多“堂子”,里边有许多做“生意”的姑娘,唱戏就是做“生意”的一种,她看见父亲这副模样,更感觉到未来凶多吉少。她呜呜哭出声来,跺着脚说:“不去!不去!我不去……”
“阿媛,你听话。”父亲终于打起精神说,“你不去也不成,爸爸也是万不得已呵,你能看着咱们家走绝路吗!爸爸已经将你押给“长三”堂子里去卖唱,先学半年再到堂子里做“小先生”,不是做“大先生”,只卖唱,不卖身。对付3年,过了3年就可回到家里来的。他们答应3年给300元钱。有了这3百元钱,债可以还清了,爸爸身体慢慢会好起来,还可以再拉黄包车!3年时间很快就会过去。阿媛呵阿媛,你这一去,不就是救了咱们全家了吗?
你可要听话呵……”
事情已经不可挽回,更何况能救父母的命,使双亲绝处逢生呢!回想起私塾老师讲的“二十四孝”的故事,面对这铁一般冷酷的现实,这年幼苦命的小姑娘又能有什么选择呢!
一位年过半百的阔佬在听她唱戏时,忽然把老鸨叫来,问要多少身价,想买她出去当丫头,实际上是做小的约摸学了半年京戏,其间小阿媛仍住在家中。一天,来了两个鬼鬼祟祟的男人和女人,同父母亲嘁嘁嚓嚓简单地讲了几句。母亲流着眼泪,颤抖着说:“阿媛,要听话,你跟着他们去吧!”
阿媛明白,这是去堂子(即妓院)的日期到了。从此3年之内,不许回家。但早已有了精神准备的阿媛,既不惊慌,也不悲哀,只是木然地听从摆布。那女人笑嘻嘻地给她里里外外更换新装,戴上首饰,十分轻巧、麻利地给她梳理发辫,擦脂抹粉。那男人还掏出一对大红“喜”字蜡烛,在阿媛家唯一的一张破方桌上点燃起来。一切料理停当,那男人即大声提示:“我们要上路啦,“小先生”快给父母磕头!”
阿媛又木然趴在地上给父母亲磕了三个响头,依然没有眼泪。
坐轿不久就落下来了。这堂子离阿媛家不过半小时的步行路程。她刚进大门,便从各个房间里跑出若干男人和女人。他们交头接耳,指手划脚。
“呵呀呀,这个小姑娘,我知道,姓董,叫阿媛,戏文唱得好格哩!”
“长得满标致,就是个大脚板!”
阿媛听任他们评头论足,把嘴撅得高高的。但他们并不罢休,又议论给阿媛起个什么艺名来。阿媛在二楼左厢房坐下,他们又进房门把她围起来,仿佛非让这位新来者张口不可,依然嘁嘁嚓嚓不停地拉话。正当阿媛由拼命沉着、冷静而变得焦急不安时,突然一下子安静下来。刚进房门的一位白白胖胖的四十开外的妇女把目光一扫,摆手说:
“你们都给我回自己房间去,在这儿吵嚷什么。她的名字叫杨兰春,牌子已经挂出去了。”
“杨兰春?她不是上个月刚嫁出去吗?”胆大的张口发问。
“你们懂个屁!老杨兰春是嫁出去了,但她的“照会”没有缴销。许多老客都知道我们堂子里有个杨兰春,阿媛来顶替,省得一笔“照会”的花销,又可以招揽老客,这不是两全其美吗,哈哈!”这位厉害的中年妇女连骂带说,发出得意的笑声。
一会儿,事情安排妥帖。所有人都离开了。阿媛的随身阿姨——孟阿姨告诉她,这位有福相的中年妇人就是这个堂子的老鸨,她就是出了3百元大洋把阿媛抵押进来卖唱的“债权人”。
第二天阿媛——小杨兰春就开始了卖唱生涯。也许是老鸨的宣传绝招奏了效,头一天在小杨兰春名下,就出人意料地收到40张局票。何谓局票?就是客人们预订卖唱的“小先生”何时到何地相会的条子,唱一曲一元大洋。
于是,小杨兰春被梳洗打扮,在随身阿姨的陪伴下,坐崭新而阔气的专用黄包车,按照局票的时间顺序,从这个地方,又到另一个地方……这奇迹般的“开门红”,使小杨兰春身价倍增。堂子里有人称道,有人羡慕,有人嫉妒。而凶狠的老鸨,也由于这是一棵难得的摇钱树,经常是笑脸相待。但对于年仅13岁的小杨兰春自己,嫖客们的贪婪、卑劣、下流,尽管只是卖唱,也得当人面强颜欢笑,受尽凌辱;每天夜半12点以后,腰酸背疼,嗓子嘶哑,才能回到自己房间,倒在床上,好一阵痛定思痛的饮泣……第二天还得照常赶场……多少个噩梦般可怕的日日夜夜呵……更可悲的是小杨兰春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按契约,3年之内她不得探家,亲人也不得来妓院探望。即使她是最红也是最能替老鸨赚钱的一个,也不例外。小阿媛在头一个年关,提出回家半天看望父母的要求,眼泪哭了一缸,老鸨仍然一口拒绝。绫罗绸缎,包不住那颗受人摧残的心;车来车往,挡不住囚徒对自由的渴望……
年复一年,小杨兰春身价不减,但痛苦也像一座望不到顶的大山,越来越重地压着她那颗破碎的心。这座规模不小的头等妓院,从老鸨到“大先生”、“小先生”、账房、门卫、佣人,以及后台老板,小杨兰春差不多都熟了。但是,在她的心目中,唯一可以讲些心里话的亲近人,只有她随身的孟阿姨。
孟阿姨是个矮胖、圆脸、小眼睛的五十开外的妇人。从去小杨兰春家接她到妓院,每天从早到晚,形影不离。她的工作是照料小杨兰春的生活,从吃喝到梳洗打扮,但不负责监管,只要一离开妓院,就有专职监管的男跟班。
开始时,小杨兰春根本不理睬这位其貌不扬的老女人。慢慢地,她发现孟阿姨不仅对她和颜悦色,精心侍候,而且堂子里的姑娘们都称赞她是好人,心肠善。特别在小杨兰春背地失声痛哭时,她总是劝导说:“阿媛(她从不叫小杨兰春这个艺名),不要太伤心呵!一个人吃尽苦头,只要时来运转,总有熬出头的那一天。你还年轻,还是个小先生,啥时候遇上个好客人,把你赎出去,结婚成家,就会有好日子过了!”
更想不到的,是孟阿姨还识字,经常看书或听书。她不仅能有声有色地讲述《三国演义》、《西游记》、《薛丁山征西》、《罗通扫北》,还能有头有尾地讲述诸如苏小小、玉堂春、梁红玉等“青楼”出身的历史上有名气的女性的故事。她说话平和,娓娓动听,但在讲到梁红玉时,居然激动起来,提高了嗓音,说:“那梁红玉也是住过“青楼”的人,交了好运嫁了韩世忠,同丈夫一道抗金兵,后来生儿育女,还被封为“一品夫人”呢!一个人的命能料得到吗!”
阿媛人小有心眼,头几个月,总疑心是老鸨指使她装白脸充好人的,只当是听故事解闷,是真是假随她去。也许是日久见人心吧,朝夕相处,赤诚可见。特别是孟阿姨在妓院属佣人一等,老鸨只指望她们把大小摇钱树的生活料理好,别的事什么也不任用。小阿媛日子久了也看清了这一点,与孟阿姨慢慢亲近起来。她陆陆续续从孟阿姨那里,了解到这个魔窟的概貌。比如:为什么叫“长三”堂子?由于阔绰的客人们在这吃花酒、打牌,常常每人要付3份银子,再加上堂子里每年端午、中秋、过年3次结账,俗称“长三”,在当时上海属头等妓院。
啥叫“小先生”、“大先生”?原来“小先生”又叫“清倌人”,都是没有成人的十几岁小姑娘,只给客人们唱唱戏,侍候客人们吃吃花酒。只有“长三”这类的头等堂子才有“小先生”,其他等而下之的“么二”堂子、“咸肉庄”、“花烟间”就没有了。
最关紧要的,是卖唱不卖身,三年期满回家去。小阿媛忍气吞声,各种凌辱都忍受着,就盼着一天又一天打发日子,快点熬到期满的那一天。每到小阿媛向孟阿姨提出这个问题时,她就一反常态,和蔼可亲的笑容消失了,总是说:“你还小,讲了你也不明白,将来再说吧。”
一年之后,14岁的小阿媛出落得更水灵了。有一天,一位年过半百的阔佬在听小杨兰春唱戏时,忽然把老鸨叫来,问要多少身价,想买小杨兰春出去当丫头,实际是做小的。小阿媛闹开了,死活不干;一连3天不起床,不吃不喝。老鸨也舍不得这棵摇钱树呢,便谢绝了客人的要求。
事后,她悄悄对孟阿姨说:“苦日子三股熬过去一股,想把我卖到别的地方,大白天做梦。我是卖唱不卖身,期限3年。堂子里真敢这样做,就得吃官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