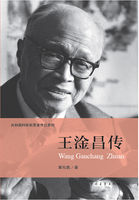当晚,我应约去黄维房间,他特地给我沏了一杯龙井茶,轻声细气地说起来。
原来,在黄埔军校创建初期,严重就是威望颇高的军事教官。他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拥护国共合作,参加黄埔军校的创建工作,除担任战术教官外,还担任学生总队长、训练部副主任(主任为邓演达——笔者注)。他从调任北伐军总司令部训练处处长,并受命组建补充师即第二十一师(独立师——笔者注)开始,就着力实施由黄埔军校确立的政治与军事相结合的原则。他精心选拔年轻有志有为的黄埔学生担任连排指挥官,并在短促的时间内对士兵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他要求每一个官兵都抱定“打倒帝国主义、除军阀”的政治宗旨,明确全体官兵都要做到“不怕死,不贪财”。他还第一个在军队生活中实施邓演达在黄埔军校所倡导的“人事公开”、“经济公开”、“意见公开”的“三大公开”的创议,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严重作为一师之长,他以身作则,严以律己,诚以待人,特别是他在生活上清廉得如一名士兵,使部下都诚服他治军严明,第二十一师从1926年秋天自广东挥师北伐,过江西,进浙江,到达上海、江苏,历时数月,沿途对城乡百姓不犯秋毫,处处受到欢迎。
黄维是带着深情且沉重的口吻回顾这半个世纪以前的往事的。二十一师自广东过江西全境,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但进入浙江,就与孙传芳军阀接火。江山、常山、龙游一线,北伐军顺利挺进。不料在严州(建德——笔者注)、富阳,孟昭月部设重防,摆开架势决战。严重命令由陈诚任团长的六十三团为主力进攻孟军。虽经激战,几度发动攻击,仍无进展,并有较大的伤亡。最后,二十一师还是师长严重亲自赶到火线,在前沿直接指挥下击败孟昭月部,打开通往沪杭大门,直下杭州。
这一硬仗使二十一师名声大振,严重的名字频频出现在报纸上,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通电嘉奖严重和二十一师,江浙父老推崇二十一师为北伐模范师。
黄维回忆说,这期间,他是初出黄埔校门的低级军官,在二十一师六十三团从排长升为连长、营长。严重师长在他的心目中,是长官、严师,是崇敬和学习的榜样。他万万没有料到,在北伐军势如破竹,二十一师顺利攻下杭州,由浙江向江苏推进,攻占吴江、同里,半夜进入苏州,截断沪宁线,使友军相继攻克沪宁时,突发上海“四一二”事变,国共合作破裂;他更想不到,他所崇敬的严重师长正在这时,向蒋介石提出辞呈,拂袖去庐山隐居十年,直至抗战爆发才第二次出山。
黄维说,严重辞职的根本原因是对国共破裂不满,他不想追随蒋介石,也不想投靠共产党,他对国家前途十分失望。他辞职的托辞是“身体欠康,心力不济,难以再担重任”。蒋介石先是不准,后来经严重推荐六十三团团长陈诚担任二十一师代师长后才同意。他先去杭州筹款为二十一师北伐在浙江牺牲的官兵建立了烈士墓,然后就只身到庐山山南太乙峰下的只有十多户村民的太乙村结茅屋而居,劳作之余便是研读《四书》,特别是《大学》,在精心研读后写出一篇篇独具心得的文章。他断绝了同国民党军政界人士的来往,偶有挚友和部属去看望他。
黄维长叹说,严师长真是个“怪人圣杰”呵!“九一八”事变后的一年盛夏,我刚升任为师长不久,应蒋介石之召上庐山参加军事会议。我利用会议的空隙,去太乙村看望老师长。我早就耳闻,如果有人乘车坐轿登门而为严重所知,必定会被他不留情面地教训一顿,因此我是步行去拜望的。当我推开那被称为“劬园”的半掩着的小门,严重并没有听见有人进来,他正对窗聚精会神地伏案读书。那是多么简陋的小屋!一张床,一张旧方桌,一张书桌,堆满了线装书。我还发现他的床头放有一叠报纸——据我所知,严重自隐居庐山之后,是不看报纸的。这一变化提醒我,他在关心国事了。我正想着,严重回头一望,我立即作了一个揖,大声说,“老师长,学生看望您来了!”“好好,你又登门了!”这是因为在他上庐山隐居之后,我是第二次登门了。他不等我坐定,劈头就问:“听说你现在也当师长了,不知贵师现驻防何处?同谁作战?”我对他消息如此灵通,颇为吃惊,当即回答,“军队就驻防在江西。多谢老师关心,学生才升任师长不久,力不胜任。”“不必客气了。”
严重单刀直入对我说:“东北三省都送给日本人了,蒋介石却把大军压在江西对付共产党。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现在的情况是外敌已经入侵,民族危亡在即,不先攘外又怎能安内,这不是本末倒置了吗?当军人虽说服从命令是天职,但也不能没有头脑呵!”我无言以对,就把话头转向询问他的生活和健康情况,他喟然回答:“还不至于饿死,身体也颇健旺,只是眼看着外敌入侵,中国人自己却内战不休,我虽身居深山,也坐不住啊!”接着,他向我讲开了他正在精心研读的《大学》中正心、修身、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说今日中国人同为孔孟之后人,对得住列祖列宗,保住我华夏江山,当是最起码的职责呀……我用心恭听。临别时,我看他生活这样清苦,心中斟酌再三,才取出随身一点点并非是事先准备的钱,力劝他收下,小补日用。但严重老师长连连摆手说:“不必,不必。你来看我这个没用的老头子,就不错了,现在我自食其力,还有一口饭吃;如果有一天真揭不开锅了,我再写信求你接济也不迟。”我无可奈何,只得收起钱,怏怏离去……
讲到这里,黄维便打住了,我看出他回忆这段往事,心绪颇为激动。相对沉默了一会儿,黄维又对我说:“严重的事就先讲到这里。国民党的失败,表现在军事上打败仗和经济上的大危机,而就其执政党的纪律和风气而言,则在于腐败蜕化之风的滋生蔓延而不可收拾!像严重这样的人品风骨的人太少了,国民党人在北伐时期呈现的浩然正气一步步消失,最终荡然无存!所以我开头说,北伐时期和抗战全面爆发之初再度出山的国民党将领严重的言行,作为中华民族借以生存、发展的道德传统在他身上的体现,是很值得我们后人研究的,无论是国民党人,还是共产党人,概不例外!”
批判梁漱溟,固执的黄维一言不发,个别谈时,他沉重而缓慢地开讲
黄维将军的秉性是有固执的一面。固执并非好品性,但表现在他身上,固执的另一面则透露正直、刚毅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他沉默寡言,知道言多必失的古训,也知道言者常常有“罪”的现状。但在他身上,最可贵的不在话多话少,也不在讲的是错是对,而在于直言,讲真话,不轻易苟同别人,随大流。作为军人,他的这一个性却是与学者型的梁漱溟相通的,他们也因此有着共同的给人印象颇深的性格特征——固执。
黄维与梁漱溟彼此结识,是在1978年2月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召开之时。在这次会议上他俩才同为全国政协常委,而且被编入同一个小组——政协直属组。
1978年2月,梁漱溟在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小组会上,又作了一番引起轩然大波的关于“人治法治”的发言,矛头直指毛泽东主席,说他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呼吁必须彻底否定“文革”,这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当时,再一次遭到批判是势所必然的。
对梁长达数月之久的批判,黄维是从头至尾都参加了,但他始终极少发言,特别是对梁漱溟的言论,一次也没有正面触及。组长动员他,他还是那几句老话:“文革”十年,我在狱中八年,不了解外情,无资格横加评论。”
他还补充说:“至于梁漱溟先生的言论,我作为一个学识浅薄的军人,听起来高深莫测,这批判又如何能批到点子上?希望各位组长容我旁听受教育。”
黄维的这种态度,在学习组二十多人的成员中,属极少数。组里的绝大多数人,对梁的种种言论,反对也罢,赞同也罢,最低限度也得讲几句表态的话——即便是违心之言,也得过这一关。
物以稀为贵。黄维就是黄维。他的保留态度引起高层人物的注意,他们指示可以个别找他谈谈,要耐心做工作,解除他思想顾虑,让他说心里话,以真正了解到他的思想认识和真实态度。谁去做这项工作呢?有关领导挑来选去,找到了笔者头上,理由是:你不是官,作为小组秘书,与全组人朝夕相处,再加上与黄维还算谈得来,不妨试试。我没有推辞,因为这类工作在我近20年的工作经历中已是家常便饭,我的责任是如实谈,如实反映,决不添油加醋,甚至极少作分析。
1978年4月间的一天,我和黄维开始了一个小时的令人难忘的对谈。我开门见山地说:
“黄老,全组都在批判梁漱溟,您至今一言不发,组长(请注意,组长也是政协常委或委员,并非是这场批判的真正决策者和领导者——笔者注)让我找您聊聊,您是否顾虑在会上谈不方便,希望您能在会下发表高见,有什么谈什么,由我负责转告组长。”
黄维淡然一笑,沉默了一会儿却反问我:“你也从来未在会上说一句话,你对梁漱溟先生的言论有何高见?你学习得比我好,能不能先说给我听听,开开窍?”
我颇感意外,但立刻回答说:
“您也知道,我是工作人员,小组秘书,是为委员们服务的。在学习会上,我的任务是记录,没有发言权,因此一言不发。至于对梁漱溟的言论有何看法,因为梁的言论是在政协会议上讲的,有权发言作评价的仍限于政协委员,现在是在学习小组,就限于参加这个小组的政协委员。我们机关干部没有开会讨论、批判,因为这不是我们的任务。当然,对梁这个人,大家是有看法的,他的顽固是上了经典着作的,作为党和国家的干部,是不可能会对他作出好的评价的——我当然也不例外。现在我的任务是受组长的委托,请您在会下发表高见,我负责向组长汇报,我可以保证如实反映,一字不差。”
黄维沉思了好一会儿,才慢悠悠地说:“你给我出了难题。我要是不说,你完不成任务,好像我也过不了这一关——会上不说,会下也得说,总之不表态不行,是不是?”
“您也给我出了难题……不表态不行,组长没有这么明确要求;组长让我来约您个别聊聊,都是为了避开会上公开说话的不便,谈谈自己的想法和看法,而这实际上是一种表态。我受组长之托,当然是能完成这项任务最好,但您若拒绝发表意见,我也无可奈何,如实向组长禀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