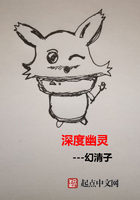“进来!”
大理寺的办事效率低,这是徐子彦早就知道的,但让他硬生生在外面站了半个多时辰,这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
徐容不是公私不分的人,况且,自己来大理寺是以圣上亲封的将仕郎的身份来的,虽说因为自己尚未及冠,领的是个虚职,到底也是从九品的官身,所为的又是江南道三司使贪墨军粮,资敌叛国的重罪,徐容没理由会在这种情况下给他使绊子。
有问题。
小厮见徐子彦双手都捧着文书,讨好地一笑,待他走进屋子,便伸手把门带上。
除了十五岁那年,被沈擎默撺掇着从花园围墙的狗洞里钻进来玩,这还是徐子彦第一次正式来大理寺,也是他第一次不是以儿子的身份站在徐容面前,这对他很重要。
徐容一身官服,手边摆着几摞案卷文书,几乎占了半个桌子,他手上还拿着几页纸,眉头紧锁,听见徐子彦进门的声音,手上一顿,抬起头看向徐子彦。
徐子彦说不清这是什么样的眼神,他自北原回来,一直随军驻扎在京郊,凯旋宴上,皇帝封赏的时候,他也没看到徐容的身影,他不确定,自己一时冲动跟着沈擎默跑去战场究竟是对是错,他只是觉得,如果有命回来,凭借军功,或许可以给自己和姨娘找条活路,如果埋骨北原,如果……那……倒也无妨,姨娘那里,沈擎默会帮他照顾好。
徐容其实在凯旋宴上就看见徐子彦了,但现在再见到这个他从未注意过的庶子,他只是觉得更加陌生。
“徐大人,”徐子彦手上文书还找不到地方搁置,走到徐容的桌前,将那一叠文书放在徐容的身前,退后了两步,向徐容行了揖礼,待抬起头的时候,他的眼中看不出一丝情绪。
一声“徐大人”把徐容的注意力拉回到面前的文书上。
“下官奉命提交江南道布政使洪全、江南道都指挥使冯继远、江南道建康路总管徐杨、江南道建康路司粮通判刘虢等私吞军粮、通敌叛国的罪证。”
徐子彦刚开口,徐容的头就开始疼了,江南道自古便是天下粮仓,正所谓“江南熟,天下足”(注:此处化用了南宋民谚“苏湖熟,天下足”,明清亦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尤其是江南道的淮扬路、建康路,商业发达,农耕兴盛,论其富足,几乎就是半个国库。
若不是早早地拿下了江南道,以南唐舒家军的能耐,再磨下去,恐怕南唐还有几分东山再起的胜算,江南一战,虽胜的侥幸,但也保住了江南的粮仓。
这次与粟末人战于北原,便是从建康路特调了一批军粮,供给前线。只是,没想到,这次出的岔子,简直是从古至今,闻所未闻——运军粮的车队居然绕开了骁果军的大部队,直接开进了粟末人的地盘。
彼时,沈擎默率军刚收复睢远、樊顺二城,连带了周边的整整三十二个县,粟末人败走的时候,非常阴险,不仅抢走了这几地的所有粮食,还顺手放了把火,一夜之间,百姓流离失所,死伤无数,建康路运粮的这个“失误”直接使得骁果军来到这片焦土上面临的第一件事就是断粮。
沈擎默不是第一次上战场,也不是第一次和粟末人打交道,粟末人会来这一手完全在他的意料之中,于是,大军刚出天津道,调粮的军文已经送到了江南道都督靳东旸的桌上,江南到燕南有运河相连,运粮船应当到安定城上岸换乘陆路,与燕南道真定路司粮通判何久交接,再由何久亲自押送到北原在睢远城与沈擎默的大军汇合。
时间极其宽裕,路程极其通畅,经手人极其少。
几乎是不可能出任何状况。
但这次,就是这样蹊跷。
徐容看了一眼自己左手旁的一本弹劾奏章,又若有所思地翻开了徐子彦带来的文书,北原粮车运进了敌营的事情传到大业城,陛下震怒异常,在大军刚启程回拔的时候,就派了监察院御史汤瑾、大理寺少卿季良友,前往彻查此事。
而沈擎默大约是对被人从身后捅一刀,还给他的敌人送了美酒佳肴的行为气疯了,派了亲卫宋远追上了汤瑾,美名其曰“护送”,究其原因,不过是怀疑他们官官相护,沆瀣一气罢了。
陛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有追究他插手这件事,默许了他们用军队驿站传递这个案子的调查进度,并严命大理寺卿徐容全面接手此案,亲自审理,一应渎职、通敌、贪腐的官员,全部从严从重处置。
但……
“这是……”徐容盯着那些字,不由得瞪大了眼睛,怎么会?他念道:“何久死了?”
徐子彦的眼神一黯,说道:“是,宋副将回报,确实是死了。”
何久死了。
不是死在运粮的路上,也不是死在粟末人的部落里。
而是死在了,青楼里。
徐容握了握拳,翻开了下一页,他一目数行,忽然停下,震惊地看了眼徐子彦,徐子彦的眼神告诉他,这恐怕是真的。
何久的尸体被发现的时候十分完好,如果可以忽略他本该有颗心脏的地方空空荡荡这点不完美,这具尸体,确实,十分完好。
完好到什么程度呢?
连表情都十分生动。
他的死因是被人活生生的取了心脏。
“谁干的?”徐容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问徐子彦。
“秋娘,”徐子彦冷笑了一声,“那座青楼的头牌,被何久常年包养,若不是人还在青楼,几乎可以说是何久的外室。”
“一个***杀了运粮的通判?”徐容现在自己也无法相信,怎么会那么巧?“人呢?为什么?”
“人已经被关在福州城,已经招了,按汤大人和季大人的意思,不日会押送大业城,交大理寺再审,据说是,情债。”徐子彦的嘴角挑起一道弧度,可徐容看不出他任何想笑的意思。
现在的这个情形,一点都不好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