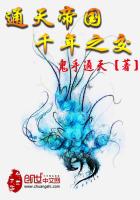张栻跟着两兄妹,举步来到塘畔,手抚雕花木栏,纵目观看,只见塘水十分清澈,水面荷叶青青,几枝莲茎,举苞待放;塘中还有不少鱼儿,在游来游去,分外悠闲自得。
水塘毗邻农田,其中的秧苗插下未久,尚有许多青皮泥蛙,在蹿来蹿去。
“嗯,适才那副下联的‘濯足灌缨’,明里是讲,在这塘畔,可以洗洗脚,洗洗帽子——”张栻正待继续给儿女们阐释,忽然看到胡大时从厢房后面,一手抚着后脑勺,没精打采地走过来,立马闭了嘴。
“大时哥哥,你怎、怎么啦,”张斓飞快地跑过去,拉起胡大时的手,轻轻摇晃着,“莫、莫非你爹爹,不在家么?”
“他,他!”胡大时支支吾吾地不肯明说。
“大时哥哥,”张焯有些诧异地问,“怎地院内若此清静,那些生员们呢?”
“春插休歇,很多都回家帮忙去啦!”胡大时解释道。
“哦,五峰先生的贵体,还有恙么?”张栻十分关切地询问,“若尚未痊愈,我们就改日再来吧!”
“我爹爹他,他的病,已然好了不少,”胡大时扭扭捏捏地,有些不愿吐露,“可他说,说……”
“大时哥哥,你爹他说、说啥子嘛?”张焯打破砂锅问到底。
“是呀,你明明白白地告知我爸,没事的!”张斓婉言相劝。
“他、他说,‘渠家好佛,宏见它说甚’……”胡大时面对新结识的小伙伴,终于一吐为快。
“啊——‘好佛’?”张栻一听,猛然想起上午,曾与张焯俩兄妹去过佛庙之事,登时满脸呈现羞愧之色,“张焯、斓儿,我们赶快打道,回、回潭州吧!”……
第三番前来碧泉书院,张栻算是真正的有备而至:首先,他做足了功课——费时近一个月,广泛搜集颜子的言行和史书中有关颜子的记载,写成《希颜录》上、下篇,以颜子自期,立志要作颜子那样的圣人,且早晚诵览,每日“三省”——他将《希颜录》随身而带,打算面呈五峰先生,祈请指正。
其次,吸取头两回的教训,既不坐轿,也不雇车,更不带人,租了两匹马,独自骑着前来,起早贪黑,仅用了两天多的时间,就赶到了紫云峰下,然后借宿在书堂附近的一个农户家里。
次日清晨,尽管有些腰酸背痛,张栻还是早早地就起了床,梳洗已毕,信步来到书院之外。
时近六月中旬,崎岖的山道之旁,那些水田中的禾苗,已经开始抽穗扬花。
院外的石牌坊前,以及香樟、古柏之下,有三五个早起的生员,正在诵读《论语》《孟子》《周易》等经卷。
“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朗朗的书声,传出老远。
“客官,请问您找谁?”张栻走到跟前,一位趴在石鼓上的小后生跳了下来,边问边用手头的经书,当成蒲扇轻轻晃着。
“我嘛,我找五峰先生,”张栻并不掩饰自己的来意,“是来拜师求学的。”
“您也是四川人吗,从哪儿来的?”小后生一听,立即改用家乡方言,热情地询问。
“哦,我老家是汉州绵竹的,”张栻能在此陌生之地,遇见老乡,真觉喜出望外,“我姓张,名栻,字敬夫,今年已满廿九。”
“那你、你是老兄了喔,”小后生滔滔不绝地介绍自己,口气也格外亲热,“我叫吴翌,老家是恭州的,今年十八岁,爸爸在福建泉州做布匹生意,得知五峰先生是福建崇安人,学富五车,特地把我送到这边来,拜他为师,求学近两年了。”
“哦,我随父而居,临安、连州都曾待过,仅永州,就住家一十三载,”张栻也坦言自个儿的经历,“前不久才迁住潭州的。”
“永州?据闻有位任过朝廷丞相的老乡,叫啥子张、张浚,字德远的,统兵抗金,居功至伟,因其得罪了奸相秦桧,也曾被贬居在那儿,”吴翌关切地询问,满脸崇敬之色,“老兄,您可曾见过?”
“那,那就是家、家父,”张栻见问,无法掩饰,只得坦诚相告,并一再叮嘱,“老弟,我若来这求学,你可千万别将我之家世,告知旁人!”
“难怪难怪,姓氏籍贯都相同,看我这猪脑壳,早就应该想到的,啪——”吴翌打了自己一个耳光,满口应承,“好的好的,绝不绝不。张兄,您头一回来吗?”
“不不,已经来过两次,”张栻如实回答,“据闻五峰先生,前向贵体欠安,一直未曾,得见其面。”
“啊,冇事冇事,先生已经起床,刚才我还见过他呢,”吴翌自告奋勇地说,“走,我带您进去!”
书堂大门虚掩着,吴翌兴冲冲地走在前头,推开便往里走;张栻不便多嘴,稍许,疑惑地跟随在后。
书堂内,左右各摆着两行长条木凳,中间是过道;过道尽头,横摆着一张八仙书案,一位胡须和鬓发花白的老者,正立在那儿,提笔习字。
老先生身着白色细布制做的圆领大袖“襕衫”,朝晖从书堂高处的圆窗斜射进来,映照在他的脸上,或许日常所见阳光甚少,抑或病后体虚,脸色有些苍白,颧骨高耸,眼窝深陷,两条蚯蚓般的青筋攀附在额角上。
他手中之笔尽管稍许有些颤抖,但其笔划仍有棱有角,功底未减。
“先、先生”吴翌连声呼唤,闯到书案之前,脚步方才停下,“五峰先生!”
“好你个吴翌,”胡宏眼皮未抬,手亦未停,“这大早的,不在外习诵,蹦来蹿去的,想干啥?”
“先生,有、有位新来的生员,想要拜见您!”吴翌束手而立,声音也小了不少。
“嗯哼,谁要见我,他不会自个儿来么?”胡宏将笔往砚旁的笔架上“噹”的一搁,身子往后面的木椅上一靠,正襟危坐,面露不悦之色。
“先生,来者是我,”张栻见状,从吴翌的身后斜跨一步,纳身便拜,“我姓张,名栻,字敬夫,以前曾有书信,向您求教过的!”
胡宏双手拢在小腹之前,沓拉眼皮,如同充耳未闻。
“先生,张栻今日乃三度前来,特为拜师求学,恳求接纳!”张栻跪伏于地,叩头祈请。
胡宏依然默不作声,仿若熟睡。
“先生,这位张兄,来意实诚,”吴翌立于一旁,见此情状,心中不忍,代为求告,“况、况且,其乃吾朝前之丞相张、张浚……”
“哎——老弟,”张栻连忙伸手,拉了一下他的衫角,接口掩饰,“先、先生,前相张浚,乃我父之世交,屡言先生,一身傲骨,不慕奢华,避居深山,潜心二程(程颢、程颐)之学,深研精传,为当世之大儒,堪称‘崖畔雪松,凛风而立’;故力荐愚生前来,觅师受教,万望先生容留!”
说完,继续诚心叩拜,甚而涕泪俱下。
“尔、尔且归罢,”胡宏良久乃言,“老夫今晨所书,‘忠、清’二字,且赠于尔,去后思之可矣!”
说罢,双手往后一背,起身便往后堂去了……
吴翌一听,心头似乎有着许多羞恼和怨怼,便要追上前与胡宏理论:“先生,您,您!”
“老弟老弟,别去别去,”张栻连忙拉住他的衣袖,甚为高兴地说,“愚兄这一趟前来,虽是拜师不成,可先生已经赠我两幅书法佳作,实在是好大的面子!”
他边说边去提起那尚未干透的宣纸,撮着嘴,小心地吹气。
“先生的秉性,正儿八经地有些怪异,”吴翌回头过来帮忙,有些不甘心地问道,“老兄,莫非你就打算返回潭州了吗?”
“五峰先生,不肯收受在下为学子,必有其道理,”张栻细心地卷着字幅,“愚兄迫不得已,只好先回潭州。”
吴翌有些依依不舍地问道:“那您,还会再来么?”
“肯定会的,但要等到先生真正答允的那一天才行。”张栻想了想,微微地点着头回答。
“既然如此嘛,”吴翌灵机一动,出主意说道,“呃,先生的幼子胡大时,空闲时常来缠着我,摆什么龙门阵;那我请他帮帮忙,抽空在先生面前,多替老兄美言几句!”
“胡大时?那娃娃很机灵;老兄上次来书院,也曾经见过的。”张栻笑了笑。
“说不定哪天,先生的心情好,他就会答应了,”吴翌满脸的阴云,方才一扫而净,“到时候,我再给老兄捎信!”
“好好,那咱们就一言为定!”张栻将两幅字卷好,小心翼翼地抱在胸前,“老弟,告辞!”
“莫着急嘛,眼下正好无事,我送您下山去吧!”吴翌跟在他的后面,走出书堂大门。
“我是租了两匹马,独自骑着前来的,还拴在近旁借宿的一个农户家里,”张栻感激地回答,“山道崎岖,就不辛苦你送行了!”
“好好,后会有期!”吴翌不得已停下脚步。
“后会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