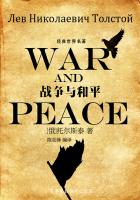静华的话,让王睿口吃起来,少年时候一紧张就说不出话的毛病又来了。他张着嘴,想说什么,憋了一分多钟,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脸变成了苍白的颜色,是他酒后的脸色。
两个人就那样在树下坐着,静华和王睿说话一向随意,这么多年来,王睿像个哥哥一样对自己很照顾,比自己的亲哥哥还要好,只是她一直心疼王睿三十六岁了,还一直单着,小月那些年没有踪迹。她也劝过他单方申请离婚,可是王睿都只是笑笑,答应着不见行动。现在小月回来了,她心里为王睿感到高兴,虽然小月带回来个女儿,这也没关系啊,他们应该还可以生一个自己的孩子的。思量了许多次,静华才开口了,谁知道他竟然这么紧张,静华倒怀疑自己是不是多嘴了。
王睿的脑海里浮现起曾经的往事,是他自己的回忆吧,或许静华早已经忘记了?
那还是在圆荷镇上静华母亲的商店里,她换她母亲回家吃饭,王睿在隔壁的睿鑫餐馆里,好像是为了买盒烟王睿出现在商店的柜台外面。
静华母亲接手这家商店才一个礼拜,静华也是第一次来换母亲吃饭,初中毕业的静华,小小稚嫩的样子,一下子就震撼了王睿的眼球,他完全忘记自己到来的目的,看着这个陌生的女孩呆住了。直到静华不耐烦地再三询问他要买什么的时候,他却逃也一般地回去自己的地盘,一只小鹿就在王睿的心里跳了一个下午。这还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这一跳,就是十几年。现在,静华说让他和小月生个孩子,王睿的心里有些酸疼,又好像是幸福的感觉。他知道这是静华关心他,才会这么说的。静华的心里一直是有自己的,这么多年的陪伴她不可能熟视无睹。他踌躇着,不知道该怎么说,很多美好的词语在脑海子大转。知了的叫声聒噪不堪,似乎是平添了暑气,王睿的额头冒出汗来,可是他并不觉得热。
静华!王睿开口说。
王睿郑重其事地叫自己的名字,表情凝重,静华觉得意外,就特意看了他一眼。王睿的眼睛忽然好像添了许多神采,亮晶晶地闪闪发光。静华潜意识里想要阻止王睿继续说下去,她模糊地感觉到王睿想说的话是什么。傻子都能看出来,王睿的眼睛此时就是一汪被爱情翻滚涌动的潭水,只等着喷薄而出了。
算了,你先不要说了,我去看看扬扬醒来没有?静华勉强找了个借口,想打断王睿的思路。
王睿霍地站起身来,挡在静华的面前,张开了手臂。
白杨树斑驳的日影落在他的脸上,王睿卯足了力气说:静华,我只想和你生个孩子!
这句话一出,两个人之间似乎就生出一堵墙来,静华脸色一变想要夺路而逃,王睿低吼着说:我等你等了十四年了!难道你不知道吗?
别,王睿,你别说出来,我们是好朋友,你像孩子的舅舅一样,比我亲哥哥对我还要好。我心里很感激你。王睿,求你,别说!静华的声音颤抖,她没想到他会真的说出来。虽然,她曾经感觉到他对自己不一般的感情,可是在他结婚后,她也出嫁了,好像就再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而且小月和他不是很好的一对吗?
我不管,你让我说完话,就算是死,我也要说!
静华无语。
你不知道吧?我根本就没碰过小月。就是为了你!我只想和你在一起!从我第一眼看见你开始!
静华震惊!
她喜欢我想嫁给我,用了卑劣的手段就嫁给了我。我心里只有你,我只想和你在一起!三年,我都没做出对不起你的事情来!你不要说话,让我说完,好吗?就在我为了逼着小月主动提出离婚而努力的时候,你却莫名其妙地宣布你要嫁给我的哥们苏畅了。我知道你喜欢的是伊远,可是你为什么要嫁给苏畅呢?我不敢问你。你们的婚礼上我对自己说死心吧!她现在是哥们的老婆了,不能再动邪念了,回家去和小月好好过做真正的夫妻,毕竟小月也饱受折磨,我对不起她。可是回到家里,却发现小月舍我而去。无奈,我只能放弃一切来到你身边,守候你!我担心你和苏畅不过是一时赌气,我见到了伊远,知道你去找他了,可能你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什么东西。我默默地看着你,你笑,我就高兴,你皱眉头,我就忐忑不安,想知道出什么事情了。方显的出生让我为你感到高兴,可是他一天天的长大了,我又发现了他是伊远的孩子。我就知道,早晚,苏畅会就此找你麻烦的。我这样毫无希望地爱着你,一直到你离开苏畅。我对自己说再不能错过你了,难道,我错了吗?小月回来了,我还是会和她离婚,我会安顿好她,我甚至还可以吧商店给她,足以养活她和孩子了。我对她没有感情,除了愧疚之情什么都没有。静华,嫁给我吧!
说着话的王睿哽咽起来,静华则呆若木鸡,不相信眼前的这个男人竟然为了自己等待到现在,感动,一刹那间,静华几乎脱口而出要说她愿意。可是,静华明白,不能,真的不能!苏畅是前车之鉴,自己再不能嫁给自己不爱的人。有了方显,生活就足够了!趁着王睿没有继续诉说的当儿,静华,迅速朝反方向跑去,绕过校园的操场,回到自己的宿舍里。方显在看书,被突然冲进门来的母亲吓了一跳。而大床上的扬扬也一骨碌爬起来,睡眼朦胧地看着母亲和哥哥,她有点难受没睡够,想哭,却发现没理由哭,因为母亲正走过来,抱起了她。扬扬就高兴起来,母亲的怀抱让她感到温暖如春。
伊远的日子味同嚼蜡不是一天两天了,他沉迷于创作中开始并没有什么察觉。每周之言放假回来画室看他,高高兴兴地和他一起过周末。有多久没看见依曼了?他不知道,也没有想起,现在难得的相安无事让他很放松。得空就带着女儿去画室后面的那条街上瞎溜达,当然是周末的下午居多,之后就送之言去寄宿学校读书。时光在叶生叶落之间平淡划过去,冬天到了,学校放寒假。之言干脆搬到画室里,和伊远挤在一起住,父女两疯起来常常用油彩把对方的衣服画的五颜六色,这种行为以前也有过,被依曼骂过许多次之后终于不敢再玩。画室在楼上,楼下的屋子安静得不寻常,偶尔,似乎依曼会回来住一晚,可是晚归早出的始终见不到她的身影。
眼见着大街小巷都穿上厚重的皮袄,还有时兴的羽绒服,各种色彩鲜艳地飘在街头巷尾。之言抱着壁炉不肯离开,吃着零食,看着电视,偶尔会踱着猫步出现在看着书或者画着画的伊远身边,又悄无声息地踱回自己的小躺椅上。
腊月二十这一天,之言趴在窗边,看外面下着鹅毛般的大雪,她有点后悔没有坚持陪父亲一起去置办年货。这十来年,这件事一直是依曼在做,伊远发现自己几乎不知道超市在什么地方。好容易找到离家不远新开的超市,人山人海地情景让他几乎晕过去。在超市门口定定神,他走了进去,马上就淹没在出入口密密麻麻的人潮中。
提着他所知道的该买的年货,在银台付过钱,看着大路上的雪已经淹没了脚,伊远放下东西,弯腰紧紧球鞋带。然后,第一次,他想起来想问问依曼人呢?她去哪里了?
左右开弓提着大包小包的伊远走回家,胳膊酸累,忽然提醒了他,依曼也是这样做的吗?那么她也会很累吧?
门口矗立着一根电线杆样的人,细高黑瘦的影子。伊远看去黑白对比倒也不错是一幅绝好的构图。
走到门口,站定了,伊远问:你是谁?
那个人看看他,说:我是姚宇,东城警察局的。对方说着,出示了一下工作证,伊远只看见一个瘦削的影子,他就收回去放回棉服的口袋里去。伊远心里奇怪,直接问:找我有什么事情?
你是伊远?依曼的丈夫?
是啊,她怎么了?不祥的预感在伊远的心里升起来,他掏出了门钥匙。
有些情况需要了解一下。对方很冷静的口吻。眼光却犀利无比,盯着伊远的一举一动。
伊远没有再说什么,打开门,让了姚宇进门,又关好了大门,在玄关换了棉拖鞋,屋里很冷,姚宇有些意外地问:怎么没有生炉子吗?
生了壁炉,在楼上,请跟我来。伊远将手里的东西胡乱放进厨房,带着姚宇上了楼,之言听见开门的声音正要下楼,看到还有一个陌生人,就趴在木质的楼梯扶手上不动了,看着父亲和那个人走上来,在她看来是一个更高瘦的人跟在后面,活像两课树,没有枝杈的。
原来,依曼失踪了,谁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姚宇是针对依曼失踪前涉及到的一个案子找来的。原本以为伊远会知道一些情况,可是伊远一问三不知,姚宇就很失望。伊远追问是什么样的案子,姚宇却不多说,只说想看看伊远的画。
伊远带着姚宇来到杂乱的画室,角落里的壁炉火已经奄奄一息,空气感觉有些湿冷,伊远不管姚宇转来转去地看那些半成的画,自己索性给壁炉里添上柴火,免得孩子冷。
过了会儿,姚宇走到壁炉前,站在伊远身边,也看着那渐渐旺起来的火焰,然后说:如果依曼给你打电话,请及时和我们联系。这是我的电话,他说着递过去一张纸,上面是一串数字。
难道依曼做错了什么事情吗?都不能告诉我吗?我怎么才能帮到她?伊远有些无奈地问他,眼睛看着骑在小凳上窝成一团的之言,尽力压低了声音。
现在还不能确定,可能与你无关。有件事情想问你,这幅画,姚宇指着角落窗下的衣服画,上面是整片的向日葵,大片的艳丽的黄色下流云般绿色的叶子只有一带宽而已。你只画了这一副吗?有没有类似的或者相同的?
伊远摇头:没有,我这幅画就这一幅。怎么了?
可是有人已经出了高价买了去,挂在自己的客厅里。
那怎么可能呢?伊远吃惊地说。
难道除了你,还有人画同样的画?姚宇反问。你有学生吗?
没有,我还不到能够收学生,我自己也就是普通的画家而已。
哦,看来我该走了。
等等,让我想想,你是说有人照我的画的样子,画出来画卖掉了。那么署名呢?是谁?
是你!
啊?不可能!
我亲眼看见的,不只一幅画。
伊远无语了,之言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他们身后,说:你见我妈妈了吗?
姚宇回过身,看着之言说:没有呢。叔叔该走了,祝你们新年快乐!
伊远送姚宇出了门,很客气地告别,关好房门之前他看了一眼头上的天,才不过下午的三四点钟,几乎要黑透了天空依然下着雪,路上几乎没有行人,亦或许是伊远没有看到有人经过。毕竟他们的这个独门小院,偏僻了些。
不怎么走动朋友的伊远,带着之言过了一个干巴巴的年,清水自然是没有回去,因为没有依曼,回去也不知道该如何交代眼下的情形。几个和伊远相熟的朋友也都回去了内地过年。父女两个就好像平时一样的懒散地过着每一天,除夕的夜里,家里的座机忽然响起来,之言高兴地扑过去要接电话,伊远却已经拿起话筒来了。
他喂了一声,对方没有说话,很遥远的一丝气息通过话筒传过来,伊远感觉到了,那是依曼的呼吸声,他紧张地问:是依曼吗?你在哪里?
对方没有回答,伊远继续追问,依旧没有声音,之言的耳朵贴在话筒外面,大大的眼睛里包着一汪泪水,颤颤巍巍地将落未落。
之言,你来说话,叫妈妈!伊远急急地说着,把听筒放到女儿的耳边。
妈妈!妈妈!之言大声喊道,终于哭了出来,伊远的眼睛也湿润起来,他偷偷抹去了眼角的泪,女儿的叫喊声让他的心被揉成了碎片。
到底,对方也没有说一句话,之言不停地叫着妈妈,说着妈妈我想你,你怎么还不回来。最后,话筒里也没有传出任何声音来。伊远不忍心,把耳朵贴过去,一阵忙音传来,对方早已经挂了电话,之言小,不知道,还一直不停地在呼唤母亲。伊远抢过话筒,挂掉电话,之言的拳头就雨点般落在伊远的胸前,伊远抱紧愤怒哭泣的女儿,紧紧地抱着她,直到她哭累了,哭声小了,变成啜泣,最后终于不哭了,在他的怀抱里抽泣着睡去,手指还紧紧地抓着他的衣袖。伊远的眼泪也流干了,他伸伸腿,轻轻地站起来,抱着女儿走进卧室里去。高大的背影在雪光中黑细瘦长,孤独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