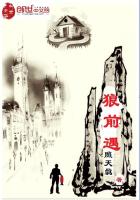“他来了,大哥。”彪形大汉看见田洁的眼神如同狼王窥视母鹿进圈,他准备拉开车门,兴奋地说:“我的食指有救了。”
中年人拉住彪形大汉的衣襟,示意了一个眼神:“等一等,你忘记了什么?”
“大哥不愧是大哥,还是您心思缜密,”彪形大汉“恍然大悟”地笑了笑,从我脚下的毛毯中抽出一把将近六十厘米的锋刃砍刀:“大哥,他要是不还钱,我就拿他的银色皇冠轿车抵债。”
中年人猛地朝彪形大汉头上拍了一下:“让你住手,这会儿别下车。”
“再不下车,他们就走了,大哥,你看田洁和那两个女的,要是大哥你顾忌,我就把那两个女的和田洁一块儿绑了。”彪形大汉把砍刀朝我挥了挥,摸了一下手臂的青筋肌肉。
“你真当SC外国语大学的校警明示牌是摆设?”中年人又拍了彪形大汉的脑袋一下:“你拍不醒还是健忘吗?忘记了五年前张虎在Ning夏Yin川打工的时候,暗恋工厂里一个X疆妹子,结果把人家给扛回了家,啥都没做。张虎的表哥和法院的副院长本来是亲家,结果张虎被判犯罪未遂,原本打算判两年缓三年,赔钱和内部协调解决,结果被判了七年半,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大哥?”彪形大汉摸着脑袋,晃了晃头。
“因为人家是少数名族啊,你真的忘了吗?”中年人继续说:“后来张虎因为表现良好,再加上副院长的一点关系,提前两年半出狱了。现在你还想在这个大学校门口面前绑人,而且是一个外国人,除非你想上头条?”
中年人继续嘱咐彪形大汉:“记住,咱们放炮,第一不放少数名族,第二不放外国人,第三,除非是同乡,否则必须硬压身份证原件和核对具体住址。”中年人说到这里,瞟了一眼我哀怨的眼神和窗外沉浸在“幸福”中的田洁。
娜莎耶夫和田洁短暂而轻微地拥抱了一下,他在娜莎耶夫的唇上狠狠地吻了一口,娜莎耶夫尴尬地抿嘴,看了眼身边的戴帽女,两人上了后座,车门关上了。
“那我们就干等?”彪形大汉一脸气愤,忽然睁大双眼,大喊:“他们跑了。”
我看着银色皇冠轿车朝下桥洞的方向渐行渐远,拐弯失去了踪影。
中年人捂住彪形大汉的嘴巴,露出一副恐惧的眼神:“别吱声,你想打草惊蛇吗?”
“大哥,你到底在害怕什么,赶紧跟踪,”彪形大汉绝望地看见消失地车影,一把拿开中年人的手,把砍刀立了起来,在车顶挂一道深痕,发出刺耳响声,把食指伸了出来:“现在我的食指是保不住了,要不然就你替我割了吧,大哥,你是不是因为前年我收款少了十八万,所以故意为难我啊?我从来没想过吞这笔钱,你不会是相信付傻子的话,不愿意相信我吧?”
中年人把目光转向我,看了很久,撇嘴一笑:“我有办法,开车吧。”
车窗两旁的绿茵从未彻底枯黄,就算是炙夏与寒冬,也不会枝头光秃,总有几片新绿挂上,茂盛如初。右边还是那个幽僻的西南ZF大学老校区,延伸进去是一片墨绿的湖畔,门口的车杆有一些老旧。弯弯曲曲的道路开往哪里?大会堂停车场旁一对情侣对着红色磁砖墙亲吻,虽然车行尽速,但我渴望时光慢一些。
“两位大哥,我给你们唱一首歌吧?”我傻傻地笑,放肆大声唱:“你算什么男人,算什么男人;眼睁睁看她走却不闻不问,是有多天真,就别再硬撑,期待你挽回你却拱手让人。”
“他是不是疯了,大哥?”彪形大汉看了我一眼,听我撕心裂肺地走调唱歌。
“真疯最好,如果是假疯,也会变成真疯的,”中年人眼睛透过后视镜凝视我:“小伙子,我们素未相识,听我一句劝,你没必要当替罪羔羊。”
“咱们放了他吧,大哥,我们的确是抓错人了,”彪形大汉意外替我求情:“就当作是一个教训,以后我会注意的。”
“第一个‘以后’是我替你买单,”中年人举起自己的断指,删了彪形大汉一耳光:“第二个‘以后’假设是你自己买单,可是付傻子的规矩是事不过三。断了的手指可以安装假肢,但是断了命谁来续?”
“嗐,想当初......”彪形大汉刚要感慨。
“想当初不入这一行,我们还在山里吃黑泥饼呢。”中年人打断,又回头看了我一眼:“小伙子,谁都有背黑锅的时候,这一次你替田洁还了钱,以后我们找机会帮你揍他怎么样?”
“我真的没有钱。”我叹了一口气,感觉自己浑身无力。
“那你的亲戚、朋友、家人呢,房子能不能卖了还债呢?”中年人苦口相劝:“既然我们相遇,鸡血和猪粪已经喷你家门口了,这也算是缘分,相识一场,互相帮个忙吧。”
“的确是一场臭气熏天的缘粪,”我恶狠狠地抬起头,愤怒喊道:“亲戚、朋友、家人不都是有福同享,有难独挡吗,房子卖了我住哪里,凭什么让我替一个非亲非故的人还债。”
“你的爸爸妈妈呢?”中年人的口气忽然变得温柔,眼神近乎哀求:“真的连五万块钱也拿不出来了吗,这样吧,三分息就免了,你只要替田洁还五万本金就可以了。”
哼了一声,我沉默地把头撇向窗外,心想是何等的缘粪把我和两个死缠烂打地高利贷收债人与无耻的田洁紧密缠绕在一起。我并不了解这一位苦心哀求的中年人和貌似憨厚的彪形大汉,万一他们知道了我母亲的联系方式,从替人还债变成了偷、骗、抢,那她的小心脏如何承受得住。我没有勇气卖房和向母亲开口借钱,哪怕勇气的赌注是自己的性命。兴许是转机,兴许转机的尽头是“永恒的天堂”在等待我的归回。想得很多很多,记忆又转到了从攀Z花开往ZQ的一辆火车上的硬座,我长嘘一口气,睡着了。
一阵烦闷的燥热和困难的呼吸唤醒了我,双手被紧紧后绑,火辣辣的膀臂如同千万蚂蚁在爬动,嘴巴被抹布塞满,头上扣紧,笼了一层厚厚的编织袋。
“醒了吗?”耳边传来中年人的声音。
我的嘴巴塞住充满机油味和腐臭味的抹布,只能勉强发出嗯嗯声,舌头几乎被堵进了喉道。我的脚在副驾驶靠背上猛踢。
“看来是醒了,小伙子,咱们就这么......定了。”中年人缓缓地说出“定了”的时候,我感到胸口发凉,他究竟想做什么?
颈部、腋窝和后脊冒出一阵阵冷汗,每一根神经都在颤抖,也许我的出生年月日会在右边加上一串数字和右括号了,头很沉,过了一会儿,我又不争气地睡着了。
“啪”耳边听到一声响炮,伴随一阵巨疼,我惊醒并被推倒在地上。
“付爷,人给带回来了。”耳边响起了中年人的声音。
“让我看一看。”一个苍老的声音伴随一阵碎碎脚步声。
“别,付爷,他被我们打得血糊糊的,辨认不出来了,”中年人说:“田洁一路上都在骂您,为了堵住他的嘴,我们狠狠把他揍了一顿。”
“钱呢,阿虎?只要还了钱,他骂了我祖宗都没关系。”苍老的脚步声越靠越近。
“他不肯还,付爷,要不然咱找块地,把他给灭了口,送肥料厂吧?”话音刚落,我脚下一个踉跄,胳膊被抓起来,往不知名的地方走。
“那外国媳妇呢?”苍老的声音继续追问。
中年人没有回答,继续拉拽我往前方走,我的内心感受到了死亡的陌路。
“等一下。”老年人在我的头上拍了拍,语重心长地说:“虽然不熟,但在胜利村,付爷百事通的名号不是瞎吹的。田洁哪,初生牛犊不怕虎,当初你把小娜这个外国人带回来时,我就想再看一看你,也替你的妈妈和逝去的爸爸开心,本以为你这次出去是风风光光把小娜娶回来,就留你一个手机号......”
“付爷,你咋哭了?”彪形大汉发出一阵疑问。
“算了,这钱咱们也不能要了,就当作是替田洁的妈妈的陪葬费吧。”老年人的话引得我心头咯噔一跳。这个老畜生,难道是为了逼田洁还钱,把他得妈妈给杀了?我内心不由翻江倒海。
“让我看一眼田老二的儿子吧,这一顿揍算是利息还清了。”“唰”我的头上扣紧的编织袋被刀切开,几根发须落下,两边坠落的编织袋如果花瓣开启,我这小脑袋的“花蕊”惊愕地瞪着这位熟悉地面孔。
“怎么是你?”老人一边问,一边把堵住我嘴巴的抹布抽出来,瞬间我的舌头抽筋地蜷缩在一起,疼得要命。
“你们居然骗我。”老人点了下头,身后出现了四个壮汉,手里拿出一把短枪。
“田洁的妈妈为什么死了?”我顺了舌头提出疑问,但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的这一位大爷正是第一次前往胜利村的公交枢纽转站口,政府大楼后街的杂货铺的泥茶水大爷。
“啪”“啪”两声枪响,打在了中年人和彪形大汉的左右两块地面。
“阿虎,欺骗付爷的下场,你是知道的吧?”一个文质彬彬的瘦弱男子从左侧衣服口袋拿出一把短手枪,指在中年人的头上。枪的表面看起来比抗日电影里的手枪还要老旧,黯然无光泽。
“对不起,付爷,我错了。”中年人和彪形大汉跪倒在地面,裤腿中间浸湿,流了一大片不明液体。
眼看弱男子的扳机要扣动,我“莫名其妙”地喊了一声:“等一下,不要杀人。”
“没关系,等下你也会去陪他们的。”弱男子悻悻朝我笑了笑。
“把枪放下,安陆。”付爷示意另一名高个子松绑,我紧张地站在众人中间,中年人和彪形大汉和另外三个人走向了右边。我和付爷站在一片空旷的荒地上,前方有一片小山坡,旁边隐约可以看见枢纽站的入口,政府大厅就像一个半弧形圆点凸起。弱男子疑惑地把枪回了衣服里的夹子,两个人把我望着。
付爷和弱男子带着我回到了杂货铺,人来人往,行色匆匆,各自奔波繁忙,中巴车和小型四人箱摩托交叉行过,阴霾的天空和我第一次来到这里一样。厚灰覆盖的陈旧店铺如此低调,怎么也不会和高利贷、杀人犯联系在一起。也许他没杀过人?
“大爷,您能告诉我,为什么田洁的妈妈死了吗?”我看了看自己柴骨般的手臂上勒出两道紫圈:“当然,谢谢你,如果不是你们,我肯定已经被杀了,感谢上帝。”
“感谢你的上帝,”付爷把手放在我的头上,我感到一阵温暖:“你有两条路可以选,第一,死在这里,永无别日;第二,成为我的手下,帮我收债。当然,两者我都会告诉你田洁妈妈的死因,只是不是现在。”
“付爷,我喊您一声付爷,我有一个妈妈需要照顾,我生在一个单亲家庭,不能没有妈妈,妈妈也不能没有我。”说了一句,我声泪俱下,像一个小孩子哭了起来。
“他从小就没有见过妈妈。”付爷示意我抬头看安陆的眼睛,我瞟了一眼,不敢继续看。
“如果你表现优异,兴许两、三年以后,你就可以回去看她了,如果你执意逃跑,那就送你们去你们的上帝那里吧。”
“毕竟恶人都去地狱了,不是吗?”安陆的眼神露出一丝不安,他摸了下胸口的配枪。
“我就是一个做外贸业务的医疗器械销售员,”我哀声地从椅子上瘫坐在地:“付爷,我不会开枪,也不会打人,更不会帮您收债,留在这里就是一个吃闲饭的人。”
“外贸,你会说英语?”付爷的眼神亮出一点闪光:“安陆,那边的业务开展得怎么样了?”
“的确少一个会说英语的人。”安陆拉起了我的右手,他的皮肤白皙,手温柔而湿润,像一个女孩子的手。
“你叫什么名字?”安陆拍拍我的肩膀:“快告诉我。”
“喊我小X就可以了。”我惯性地回答。
“小X,咱们村现在准备出口野橘和苹果到马来西亚,既然你做过出口外贸,那流程肯定是熟悉的。”付爷喜出望外
“这个没问题,”我开心地回答:“如果仅仅是处理外贸跟单,与意向性客户的促销与接洽,我是信心满满。”
“这可是你的本职工作,你要认真完成。”安陆把“本职”两个子说的很重
“至于你的副职当然就是协助安陆和马来西亚的外籍收债人沟通,如果你能转副为主,成为他们当中的一份子,就事半功倍了。”付爷补充道:“既然你是我的人了,那和其他刚来的兄弟一样,月工资一万三,每一笔你接洽的一百万以上的生意,放炮成功,六千六百元提成,以下五百元。年终双薪。”
“好的,付爷。”我一边应声,一边疑惑,一个穷乡僻壤地农村人居然懂得和外国人打交道和收取外汇币种,哪里来的门路和手段呢?
安陆站起身,突然在我身上一阵乱摸,让我都有了生理反应,他拿出我的手机,用力一掰“啪”手机断成两半。
我目瞪口呆地张开嘴巴,付爷笑了笑,掏出了一个白色的手机:“你们年轻人最喜欢的水果,以后你就用它吧。”
店铺外的车声和脚步声越来越少,不知哪里冒出了寒蝉的哀鸣,我叹了一口气,夜空下凝聚成了孤寂的雾气:“付爷,安陆大哥,以后我会好好和你们学习的。”
勉强挤出一个微笑,我的肚子咕咕作响。
“饭点到了,付爷,”安陆提醒一句:“今晚应该好好宴请一下我们的新伙伴,以及未来的优秀员工。”
“去找老板娘要饭票。”付爷撇嘴,脸上有一些不悦。安陆应声离开了杂货铺。付爷换了一身藏蓝色中山装,带了一副黑框小眼镜,头发梳成了翩分,我们两个也离开了。
一边跟在付爷身边,一边喃喃自言自语:“难道我也变成了一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了?”
我和付爷走到了办公大楼的右侧入口,大楼的背后是一座一层的房屋,外表的装潢十分老旧,里面却是金碧辉煌,连服务员也是男的各个高大威猛,女的青春靓丽,寒风下春暖诱人。
“请坐,小X。”付爷给我挪了一根凳子,厅内暖黄的灯光与热闹的饭局和窗外的凄冷形成鲜明对比。
“付爷,以后我就是你的员工了,请词就不必了。”我慌忙给付爷让道,请他先坐下。
“胜利村的人均年收入是334块钱,而田洁的五万块相当于自己的卖身契。”付爷缓缓坐下,主动提起了田洁。
“既然如此,你明明知道他还不起,为什么还要借贷给田洁,难道是因为他要成为村里第一个娶外国女人的人?”我好奇地接话。
付爷继续说:“是因为我听说过他的爸爸的过去,都说虎父无犬子,哪想到......”
“老公,新来了员工,为什么也不通知我一声。”安陆和一个衣着亮丽时尚的女子走进大厅,她的皮肤黄得发暗,体态匀称,烫了一头金色卷毛短发,粗黑的眉毛在眉笔的作用下像一只蜡笔小新,高挺的鼻梁,鼻孔就像准备入火车的大山洞,“霸气侧漏”,嘴巴好似挂着的两节肥香肠,但年龄和付爷相差起码四十岁。
“饭票带来了吗?老婆。”付爷一脸“奉承”堆笑,刚才威严的气势荡然无存。
“啪”女子从钱包里掏出两万块丢在桌子上,眼睛偷偷瞄了我一下:“今晚敞开肚子吃。”
“谢谢......老板娘。”我一边喊一边看付爷的表情,嘴角咧笑得尴尬。
“别喊我老板娘,喊我梓姐就行了。”女子一边捂住肥香肠嘴巴偷笑,一边摆手。
饭局变成了安陆、付爷和梓姐的比酒划拳,而我则默默地啃了一堆蟹黄和鸭腿,以填满我的肠胃对于再次来到这片荒凉贫穷之地的恐惧。
最终,付爷和梓姐躺在了酒桌上,说起醉话,而安陆仅仅是面露红润,轻松地将两人夹在双肩,示意我付款。
夜色星空下,付爷和梓姐乘着酒劲左音高歌一曲,我默默地和安陆同步,一步一步地走向前方。
“哎呀,我的脚。”身边传来一声抱怨,我左转头看到一个摔倒的女生,月光下,她的五官看起很美。
“安陆,是你吗?”女孩朝安陆喊了一声,安陆把头转了过去,朝我喊了一声:“小X,过来帮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