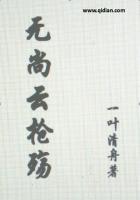离馆内初甄的日子越来越近,怜心和元香的合作也愈加契合。芳蓉凑过来围观以后哀嚎连连,只道自己是浪费时间,有元香在前面挡着还有什么胜算。
“唉……”怜心叹了一口气,从泛黄的铜镜中清晰地映出佳人蛾眉轻蹙的模样。
她的声音还是少女般的灵润,幽怨地叹了一声不但让人觉得哀愁,反而生出一种小姑娘家因没买着想吃的糖人而生气的可爱模样。
元香走过去替她拢了拢因为舞而略显凌乱的长发,头发略微泛黄,是她为了比赛故意饿着少吃饭的结果。元香怜惜她小小年纪却待自己这般狠,却因为知晓其中的缘故而说不出半句劝阻的话。
“怜心要是得了花魁会想做什么?”元香替她绾了个垂柳髻,一侧的头发盘得紧紧的,另一侧随意地披散下来,少女恬静烂漫的气质一下子显露出来。
怜心歪着脑袋想了想,道:“大概会穿着花魁的华服带着娘亲从来没有享受过的奢华祭品去拜祭她,然后用花魁的赏钱给乡里的娃们修个书院。”
怜心的娘辞世的时候恰逢她们娘俩最困顿潦倒的时候,死去三天尸体发臭了才被不堪冲天尸臭的邻居发现,小小的怜心就守在母亲冰凉的尸体旁边,别人问她什么她都不说话,大家都以为这个可怜的小姑娘傻了。乡里乡亲多是同样挣扎于穷苦生活底层的人们,不待怜心开口求便都你一文我一文地凑了钱给怜心她娘买副薄棺好入土为安。
事发的时候怜心虽然还小,但是乡里乡亲给予的恩情却永远不忘。
元香点了点头,打心底里对这个善良的小妹妹更加怜惜。
内部的初试在几天后举行了,评委团是以景戎为首,各个分科的夫子为辅。
比赛的当天为了保持神秘感,景戎特意又歇业了一天,馆内大大小小的杂役姑娘们也不管参不参加比赛的,都乐得清闲跑来凑热闹。
元香和怜心合作的一曲《浣衣殇》毫无悬念地拔得了头筹,曲终舞罢之时馆内无论评委、参赛的还是单纯凑热闹的都颇有默契地保持安静,半晌也没有人讲话,生怕嬉闹的人声会扰了这一抹情绪。
棋的首位被玉笑姑娘得了去,这位玉笑姑娘也有趣得很,虽然名字中含笑,平时也爱笑,却从不在下棋的时候露出半分笑意,惹得一群闲得重要部位疼的客人经常互相打赌,赌的是谁要是能在跟玉笑下棋的时候博了美人一笑便算赢。赌注从一壶好酒慢慢涨到一桌酒席,再慢慢上升到贵重的金石玉器,可惜玉笑从来也没在手谈过程中笑过,所以所有的赌注都分了三分给景戎做开赌局的报酬。总之客人们使了各种稀奇古怪的招数都没能成功。
玉笑绷着一张脸给景戎赚了满钵的金银,乐得那只狐狸露出一口银牙。
有一次分给景戎的赌注居然达到了千金,景戎跟玉笑打趣道,“你就笑一个圆了他们的心愿罢了,反正钱也赚够了。”
谁知玉笑用她那双杏核眼狠狠地白了老板一眼:“天下哪有伙计急着赚钱,老板觉得赚够了的。”
人家姑娘多聪明,求的就是源源不断、生生不息的来钱,你说钱来得多简单,就是绷住脸上那几条肌肉不往上扬而已,只要保持不笑,就算把一抹红唇憋成天包地也没人嫌她丑。
据说当时景戎被小姑娘训得满鼻子灰,回去以后把自己关在房里痛定思痛,深切反省自己那枚宝贵的奸商魂怎么就给大鱼大肉的滋润生活给挫没了。
诗词的首位自然是资质最老、悟性最高的素玉摘得。
画的首位被一个生面孔得了,听芳蓉介绍那名女子叫沉溪,因为觉着老待在伎馆里影响她的发挥,于是经常跟景戎打了声招呼背个行囊就出去写生,常常一去就是小半年,这么些年下来,幅员辽阔的国域都快被她踏遍了,直叫人羡慕她的洒脱。
有了沉溪的先例,伎馆里其他学画的姑娘也经常打着采风的幌子出去公款吃喝玩乐。景戎捶胸顿足啊,自家伎馆里的姑娘们一个赛一个精明,一个比一个悠闲,这样下去还怎么赚钱啊!
舞和琴的首位争夺比较特殊,因为元香和怜心分属琴、舞两类,两人合作得精妙却隐隐对比赛不公平,于是景戎做了主,让琴、舞两类再多选出两位得到参加花魁比赛的资格,芳蓉和凤舞分别获得。
琴棋书画舞,除了琴、舞各有两人参赛以外,其余都是一人。因着景戎手里还空了三个名额出来,于是便与夫子们商量着再从另三类中多选了一人出来,凑足十人之数备赛。
怜心舞技本不出众,此番初尝了得胜的甜头以后不敢懈怠,愈发努力地练习。常常练到连只需坐着抚琴的元香都受不了的时候才作罢。
景戎常常在开馆的时间摸鱼溜来探望这两个最有胜算的姑娘,每次来还不会空着手,变着花样带各种点心来慰劳辛苦的二位。
怜心苦着脸看着景戎带来的桂花糕,又哀怨地看了一眼天天大鱼大肉甜点不断但是从不发胖的元香。明明馋得要命却又想着不能为了满足一时口腹之欲而让好不容易瘦得恰到好处的身材功亏一篑。
“怜心,你现在的表情可像极了大饼。”大饼是原先的那个元香养着解闷的猫,这猫小的时候长得小巧可爱,还有一个很文艺很清新的乳名叫“玲珑”,后来因着元香迷恋景戎,狂追猛打不成之后把玲珑改名“景景”聊解单相思。岁月这把杀猫刀没有放过景景,还是血淋淋地把它给残害了,小时候那张美少年的脸一去不复返,特别是这一个多月,生生被景戎带来的甜点喂成了一只壮硕的大猫,于是它多了一个很通俗很形象的大名,叫“大饼(脸)”。
景戎举着半块碎了的桂花糕逗着怀里的猫儿,小肥猫伸爪子朝桂花糕够了够,谁知景戎成心逗它玩儿,一会儿把桂花糕举得低一些给了它希望,一会儿又在馋得口水滴答的猫咪伸爪子够的时候把那块都快被捏化了的桂花糕举得老高,如此折腾了几番,最后嘴一张,把那半块桂花糕扔进了自己嘴里,气得猫咪直哼唧,不住地用爪子挠他的衣袖。
元香望了望天,这只无良的公狐狸居然连小猫咪都要欺负。
怜心咬了咬下唇,狠心地别过头不去看那些长得晶莹剔透,个个仿如叫嚣着“快来吃我呀!!我很好吃的!!”的桂花糕。抹了把辛酸泪,心道自己连大饼都不如呢,大饼起码不怕胖……大饼再胖也有猫追……
大饼惹了祸端,不过却极冤。
那一日它照例跑去围观主人弹琴和怜心跳舞,本来在窗沿上趴得好好的,恰逢凤舞从旁边路过,大饼知道主人和怜心小妞不喜欢那个凶巴巴的女人,所以打了个哈欠转了个头继续闭目养神。谁知就在凤舞飘过的瞬间,它那颗年轻的猫心忽然大乱,鬼使神差般的跃下窗台在屋内到处乱窜。
非常不凑巧的是当时怜心正跳着整支曲子中最难的踮脚跃部分,大饼的忽然出现打乱了她的舞步,为了避让大饼,怜心往后一退,只听“咯噔”一声……
“大夫,我的脚三天之内能好吗?!”怜心几乎是带着哭腔拉扯着大夫的袖子问道。
老大夫捋了捋胡子,气咻咻地教训道:“伤筋动骨一百天,你的脚以前就扭着了,但你居然不注意休息,还继续这么大强度地练舞,这一次正好扭到了相同的地方,伤上加伤。我看你没个小半年是不能再跳舞了。”
怜心听了大夫的话,脸色瞬间变得煞白。豆大的眼泪盈满了眼眶,浓密的睫毛绝望地微微颤动。
元香不忍她这般伤心难过,便向景戎求助。
景戎深深地皱着眉,却也无能为力,他有万金难求的吊命仙丹却没有治疗小伤小病的速成药。
“罢了,怜心你就安心养伤吧。反正你还年轻,今年参加不了明年还有机会的。”景戎安慰道。
罪魁祸首大饼被元香捉来请罪,怜心虽心中有千万个伤心也无法对着一只肥硕的猫咪发作。冷静了许久便也想通了,有些事情大抵就是人算不如天算。
第二天一早,元香还未起床便听见屋外有激烈的争吵。
伎馆里的人们一向和平共处,偶有凤舞之类的泼辣霸道之人众人也是能躲则躲,躲不了就让着。总之是不会出现这么大声的喧闹的。
随手搭了一件外衫,元香起身出去瞧,看看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不得了的大事。
刚出楼门便看见素玉和凤舞在那里拉拉扯扯互相谩骂,两个人都吵得衣衫不整头发凌乱。不过说到互相谩骂其实也就是凤舞一个人在骂,素玉一向温婉,骂人方面的词汇量不够丰富,颠来倒去的就是骂凤舞“小贱人、小贱人”的,别的也翻不出花样来。
众人的争吵声终于是把天天都睡到日上三竿的景戎给吵醒了。
元香上前打听一番才知道,原来凤舞在怜心扭伤脚的当晚便去找了景戎,跳了完整的一曲《浣衣殇》要景戎答应让她跳这曲子比赛。
景戎答应没答应倒是不知道,只不过凤舞这一举动不知为何被泄露了出去,一传十、十传百,今天早上恰好传到了素玉耳朵里。昨日大饼忽然发难的时候凤舞正好从她们练习的房间路过,而得知怜心不能继续备赛的消息的当晚便去老板那里娴熟地跳了一整首《浣衣殇》,再加上之前怜心得罪过她,种种可疑的迹象都不得不让人往她要谋害怜心的方面想。
“你就是故意的!故意害得怜心不能跳舞想抢她的曲子!”素玉难得一见的愤怒,眼眶红红的,显然哭过,但是依然叉着腰指着凤舞的鼻子骂,气势上绝不输于她。
“哼!血口喷人也不是这么喷的!说我故意害怜心也得拿出证据!”凤舞的嘴角牵动了一抹莫名的笑,她很清楚素玉要是有一星半点的证据早就拿到老板那里去了,怎会自不量力地跟她叫骂。
“你!就是你干的!”素玉实际上比元香更疼怜心这个妹妹,见妹妹这么多日的努力就白白被人夺了去很是为她不平,发誓要让凤舞付出代价。
“大清早的都吵什么呢!”景戎披了件他一贯穿的墨色长袍,睡眼惺忪地摇着扇子出来了。一大清早被人扰了清梦的老板似乎有点起床气,脸上的表情很是不耐烦。
“老板!素玉大清早的来我屋子叫骂,非说是我害得怜心扭了脚失了选花魁的资格。昨天在场的还有元香,她亲眼看见是她养的那只该死的猫忽然发疯似的扑了怜心才让她扭着的,怎的平白无故地赖到我身上来了。”凤舞的表情充满讽刺。
“一定是你!肯定是你使了什么法子让猫忽然发疯的!”素玉拿不出任何证据却又不甘心地强辩着。
“哼!懒得跟你纠缠!”凤舞说罢便往楼里走。
素玉还想冲上去拦住她,却被景戎先拦了下来。
“既然你们都知道了,我也不瞒着。怜心不能参加比赛确实非常可惜,可元香也是同样练习了很久的,如果因为怜心的退出而放弃了这支曲子实在是可惜。现在并没有任何证据指出怜心扭了脚是有人故意陷害的,所以也就不存在凤舞谋害怜心一说。目前来说,凤舞的舞确实是跳得最好的,让她和元香合作相信一定能把《浣衣殇》演绎得同样优秀。”
“什么?!谁要和那个贱蹄子一起练舞!?”凤舞和元香几乎是同时脱口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