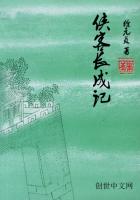孙广明上个月刚刚过完六十大寿。他在黄州府做了二十年的推官,断狱无数,只是可惜了他的好名字,他向来只知道唯“财”是用,案情断得明不明他可不管。数月前,黄州府尹调任,新来的府尹甚是严苛,他这糊涂推官实在干不下去了。这些年来他也贪得盆满钵满,正好趁机告老还乡。一路上,娇妻美妾在侧,坐着马车唱着歌,甚是舒坦。眼看到了武昌府,哪成想光天化日之下竟有强盗抢劫。
他大着胆子,撩开车帘,只见一个蒙面黑衣人拦在大路当中,手中挥着一把明晃晃的大刀,随行的车夫和管家孙福早就伏在地上抖成一团了。心里暗骂孙福无用,自己硬着头皮作了个揖,颤声道:“大王,啊不,好汉,老朽这厢有礼了。我们这一家老小都是善良百姓,路过宝地,没啥孝敬您的,哎,孙福,快给好汉献上十两银子,聊作茶资,聊作茶资……”
管家孙福忙从地上爬起,伸手到褡裢里去摸银子。这银子也会添乱,越是着急越不听话,连摸两个都是二十两的银锭。老爷的话他是不敢不听的,只好送回去接着摸,直到第三回才摸到一个十两的银锭,哆哆嗦嗦捧到黑衣人面前。孙广明在旁一个劲地咳嗽,一口老血差点没喷出来。
黑衣人接过银子,哈哈哈大笑起来,直笑弯了腰。笑毕,沉声骂道:“老东西,别跟我打哈哈,把你车厢里那两口檀木箱子给我抬出来!”
孙广明一听,两眼一黑,乖乖,看来贼人早就打探明白自己的底细了,这可如何是好。
黑衣人见他不动弹,焦躁起来,纵身过来,手中大刀一挥,哗地将车轮砍为两半。车厢失衡,登时栽倒在路边。孙广明和两个小老婆哭爹喊娘地从车厢里爬出。黑衣人踹开厢门,车中果然有一大一小两个檀木箱子。
黑衣人大喜,将长刀插在地上,一手一个,抓起箱子便待要走。不曾想那大个箱子颇为沉重,一提之下竟未提动。他拔起刀,一刀将箱锁劈断,揭开箱盖一看,里面全是码得整整齐齐的金银元宝,足有数千两。
“老东西,你还真有货啊!你不是说要孝敬大爷吗,那我可就全收下了,哈哈哈——咦?阁下是?”黑衣人忽然发现,眼前不知何时站了一个赤露上身的魁梧汉子。“坏了,自己好不容易逮到条大鱼,真是得意忘形了,连这个庄稼汉走到身前来都不知道。”
“老人家积攒点家业不易,兄弟还是手下留情吧。”来人正是蒙川。他在树林里观望多时了,见黑衣人要携赃而去,便出面制止。
黑衣人听他语气,知道他不是寻常路人。“呵呵,阁下也要分一杯羹吗?那可得凭本事啊。”说罢,手中长刀呼呼作响,兜头盖脑向蒙川砍去,车夫们见状,吓得四散奔逃,孙广明腿都吓软了,瘫倒在地。
蒙川岿然不动,待刀锋及面,倏地后退半尺,掌力凌空击出,长刀登时被逼成曲尺,反向刺去。
黑衣人见状不妙,连忙撤手,一个铁板桥,堪堪避过。再起身时,蒙川已欺到身前,两指如剑,对其咽喉虚点一记。
蒙川见此人虽是拦路抢劫,却并未动手伤人,还算守江湖规矩,因此未对其下重手。
一招过后,高下立判。黑衣人知道自己不是蒙川对手,也不再逞强,拱手道:“兄台果然好手段,小弟佩服、佩服。大家都是闯江湖的,有财一起发。呶,这大箱的金银归你,小弟只拿这小箱的,如何?”说罢,也不管蒙川可否,提起箱子,拔腿便奔。别看他武功平平,身材纤瘦,可跑起来却迅捷异常。
蒙川追出两步便即停下,一来他有要事在身,耽搁不起,二来这黑衣人倒也不算过分,只抢走少许钱财。他哪里知道,那小箱里装的都是珠玉翡翠、字画古玩,远比一箱金银贵重得多。黑衣人是个惯犯,眼光可比蒙川尖多了。
管家孙福和三妻四妾躲到路边草丛中不肯出来,只剩下孙广明仍趴在地上瑟瑟发抖,蒙川过去将其扶起,安抚道:“老丈贵姓?府上何处啊?”
孙广明听了蒙川和黑衣人交谈,只当他也是强盗,见他打听自己的姓氏住所,以为蒙川盯上了他这只肥羊,日后还要动手,哪敢说实话:“老朽无名之辈,无名之辈……”
蒙川见他怕得厉害,不好再问什么,指路给他:“沿着官道,西行五六里便是府衙,老丈快去报官吧。”
孙广明只道他说的是反话,哪敢应声,喏喏道:“不敢,好汉,不敢……”
“那这箱金银如何,总不能明晃晃地摆在这大路上,可要我帮忙抬走?”蒙川本是好意,料他这把老骨头定是搬不动数百斤重的箱子,想要施以援手。可孙广明却会错了意:“好汉只管拿走,权当老朽孝敬好汉的,应该的,应该的……”
蒙川急道:“这些钱财,我怎会要?”
孙广明一把鼻涕一把泪,磕头如捣蒜:“好汉,求你行行好,拿着这些金银走吧,这已是我全部家底了,真没有了,再要就剩下我这条老命了,唉,呜呜……”他是认准了破财免灾这条理,任凭蒙川怎么解释,一概不信,就是苦苦哀求。
蒙川本是狭义之举,硬被人当成强盗之行,不禁有气,索性心一横,真的去箱子里捡起金银来。一边拿一边宽慰自己,人家富贵之家也不缺这点银两,看看,光老婆就娶了五六个,自己远去京城,没有旅资可不行。原本只想拿个三五十两,总觉不够,最后捡了十个二十两的银锭,十个十两的金锭,用管家撇下的褡裢装好,缠在腰间,道一声谢,径自离去。
孙广明待蒙川走远,才颤颤巍巍爬起来,一边感慨老天垂怜,劫后余生,一边咒骂蒙川假仁假义,虚伪做作,连声催孙福快马加鞭赶去城里报官。官府见既无人员死伤,孙广明又不是什么显要人物,也懒得深究,不过是讯问一番,图了画像,敷衍了事。
蒙川并未急于上路,而是返回武昌城里。先到香水行痛痛快快洗了个热水澡,然后去净发社理发净面,又到街上寻了间布铺,从头到脚置办了套衣物。一切收拾妥当后,顿觉神清气爽,心情大好,俨然一钟鼎之家的俊朗小生,再也不是街边游荡的邋遢汉子。不得不说,手中有银子就是好!
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从武昌府到京城,怎么走都没有乘船快。蒙川到码头寻了条顺路的货船,给了船老大二两银子,上船便走。
当晚,货船宿在黄州,第二天正午到了蕲州,酉时刚过,已到了九江府。
九江府号称“三江之口、七省通衢”,乃是天下眉目之地,南来北往的货物、商旅均在此汇集。货船到了这里,要停靠一晚,卸下蜀地的柑橘、井盐,装上本地的稻米、瓷器,到了下游再贩掉,回程时装上苏浙一带轻便的丝绸、茶叶,如此往复,实为辛苦,一趟下来也不过赚个一二十两银子。因而,船老大也愿意在途中顺路载客。
诘旦,船工们用过早饭,正要起航,岸上忽然有人喊道要搭船。此时船已离开码头一丈多远,那人也不待船老大答允,直接跳上船来。
船老大正要发怒,那人随手抛过来一个五两的银锭。看那人模样,身材不甚高大,一身青布衫,头上束个四方巾,瓜子面庞,白白净净,两只眼珠滴溜溜乌黑漆亮,看似是个年轻书生,不像歹人。再问那人要到何处,答说要到京城探亲。船老大见顺路,给的银钱又多,立时就转怒为喜了。
年轻人上船后,同船上众人打了遍招呼,自称姓齐。船工们都是粗人,好不容易来个斯文人,蒙川不禁多看了几眼。这一看不要紧,蒙川忽然觉得这年轻人有些古怪,但哪里古怪却又说不出。
那人见蒙川一直望着他,微微皱眉,走过来问道:“怎么?兄台有何见教?”
蒙川自觉失态,忙拱手致歉:“不敢!只是齐老弟风姿俊雅,让我想起一个故人而已。”
年轻人并不相信:“哦,敢问兄台的故人姓甚名谁,仙乡何处?”
蒙川笑了笑:“不瞒老弟,我还真不知道这个故人叫什么。不过,前日午后,我们刚刚在武昌府东门外见过,他走得急,并未留姓名。”
此言一出,姓齐的年轻人矍然色变。他盯着蒙川从头到脚看了一遍,恍然大悟:“嘿,还当真是旧相识!”
原来这人正是在武昌城外拦路抢劫的蒙面人。蒙川起初见他身形、口音便有些怀疑,只是不敢相信当日的悍匪竟会这般风度翩翩、儒雅文静,出言一试,果然不错。
年轻人重新施礼:“小弟齐襄。日前匆匆一别,还未请教兄台高姓大名?”
蒙川听他言谈不似一般强人,回礼道:“在下蒙川。上次出手阻拦,搅了老弟的财运,还请见谅。”
齐襄忙道:“蒙大哥哪里的话,江湖上讨生活,各凭本事嘛。以大哥的本领,在绿林道上自然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蒙川正色道:“齐老弟错解了,兄弟我不是吃这口饭的。某虽不肖,但恃强凌弱、鱼肉无辜的事还是不做的。我瞧你相貌堂堂,衣冠楚楚,想来家境殷实,衣食无忧,何不好好读书,考取功名,何苦做此营生?”
齐襄闻言脸上有些挂不住,讪讪地道:“嘿嘿,我这个人好动不好静,读书是不可能的了。自幼家父就逼我读书,可连书都是他偷来的,又能教到我什么好处。蒙大哥我听你满口仁义道德,定是书香名门之后,不知学问如何,如今在哪里高就呢?”
“这……”蒙川一时语塞,无言以对。也是,自己刚刚蹲了五年大牢,哪有资格教导别人呢。
齐襄人虽年轻,做事却颇老练。不到半日,便和船上众人混得烂熟。每到码头,必下船买来酒菜供大伙享用。蒙川初时还对他处处设防,渐渐发现其并无歹意,慢慢也对他有了好感。闲来无事,二人也切磋些拳脚、棍棒,闲聊些江湖逸事。齐襄书没读过几卷,知道的东西却不少,沿途千余里,各处市镇风土人情、物产名胜、奇闻怪论,信手拈来,如数家珍。蒙川只恨不能将其引荐给紫虚子,不然听他二人当面谈侃,绝对是件趣事。
一路上,晓行夜宿,顺风顺水,到了第三天黄昏,船已行到太平府,离京城只剩半日行程。齐襄忽然起意,要在此游玩几日,买来好酒与众人作别。
酒到酣处,齐襄同蒙川道:“蒙大哥,这长江水道我来往不下几十回,唯属此次最为快活。你我当真算得上是一见如故,他日有缘,必能再见!”
蒙川见他说得真切,也不禁动情:“不错,老弟。这些年来,我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冤屈,这几日纵横江湖之上,与烟霞为伴,与波涛共舞,实为平生之乐事。今日一别,不知何时再会,有道是‘遥知湖上一樽酒,能忆天涯万里人’。”
两人立在船头,纵声长啸。齐襄酒量不及蒙川,脚下已是踉跄。蒙川忙向前扶住,着手处只觉绵软异常,齐襄轻轻将他推开,回首谢过。踊身一跃,上到岸上,不多时就消失在夕阳下。
日色渐暝,蒙川仍怔怔地立在船上。嗐,自己真是蠢笨如牛,在牢城和一群粗野汉子们摸爬滚打了五年,如今一个妙龄女子在自己面前都分辨不出,还和人家称兄道弟,这对眼珠算是白长了。我说这小兄弟怎么长得这么俊俏,夜里休息也不和他人杂处,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