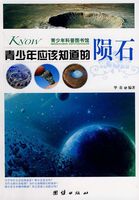范文艺的父亲是丛林游击战的老手,最擅长在原始森林中使用马蜂窝、毒蛇、麻醉吹管等原生态必杀器,这些个传家宝是一件不拉的传给了范文艺。
范文艺发现黎阍单身前往海滩走去,天赐良机呀,他悄悄的尾随上去;范文艺迅速从灌木林里穿到黎阍前面设伏,抄起吹管瞄准了黎阍的后颈脖,“嗖”的一声击中目标;黎阍踉跄两步身子一软就歪了下去,就听到潘码风的声音:“小黎姐,你怎么了?”吓的范文艺脖子一缩,趴在灌木林里大气不出。
潘码风快步奔至黎阍身边,一看脖子后面,就知道是中了麻醉针射击,他迅速拔下针头,马上给黎阍打了一针纳洛酮解毒。心里就犯疑,这东西听说在丛林游击战的时候有人使用,怎么鸿庥岛有它的踪迹。他迅速观察四周情况,心里升腾起团团迷雾,觉得还是尽快离开灌木林为好,于是,他迅速架起黎阍向灌木林外走去。
回到医务室不一会儿,黎阍就悠悠的醒过来,潘码风立即把刚才发生的情况告诉她:“小黎姐,你被人麻醉暗算了!”
黎阍焦急问道:“我吃亏没有?”潘码风一时无语,等了一下才明白黎阍话语里的意思,忙答道:“没有,我及时赶到救下了你。”女人啊就是女人,小命不要紧,身子清白才要紧。
黎阍赶紧追问:“有谁知道我们去海滩一事?”潘码风想都没想“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气的黎阍就想骂人:“算什么事?”又问潘码风:“小兄弟,要不要报告那个鸿庥岛岛主?”黎阍对范文艺素来没有好言语。
潘码风脸上就有些尴尬的神情“还是不要惊动太多人为好。”黎阍想想也不无道理,也就没有再吱声。
潘码风是鸿庥岛上呆了好多个年头的军人,比较熟悉了解鸿庥岛的人情世故,鸿庥岛多年没有听说有人使用麻醉吹管;所以,他在心里一直觉得“犯瘟疫”的可能性比较大;他和黎阍没有私仇,但他又极端好色,故而使用了即能够达到他个人目的,却又不必杀人的麻醉吹管,对黎阍实施攻击。幸亏,自己是先行到达等待黎阍,否则,结局可想而知。
范文艺色欲熏心铤而走险,差一点得手,让潘码风坏了好事。他就在心里恨得牙根痒痒的,琢磨着,还是弄个法子把潘码风赶走才行啊!
范文艺是瞌睡就遇上有人送枕头。当天晚上,刮起了一阵南海盛行的西南季风,而且来得突然,风的阵性大;把一艘马来西亚渔船刮上了鸿庥岛,鸿庥岛如临大敌,立即进入临战状态,由于风雨交加,一直挨到天大亮,风雨稍停顿一下后才摸上渔船,把渔船上的渔民赶下来一问,才闹明白是被大风刮过来的。范文艺气的七窍生烟,他妈的,几个渔民一艘渔船,就搞得鸿庥岛一夜鸡犬不宁,他当场把昨天晚上的执勤人员骂了个狗血淋头,并且立即安排将所有俘虏人员关押起来,扣押渔船,同时上报陆上的旅部机关。
这时,他的心腹,曾经盯梢黎阍的阮中尉,就趁机给范文艺献上一个锦囊妙计,“范上尉,国难家仇您没忘吧?”“切齿不忘!”范文艺血红了眼睛。
阮中尉继续献言道:“范上尉,您没来鸿庥岛之前,曾经也发生过像昨晚一样的情况,一群人一艘船被风刮上了鸿庥岛,不过那是一群海盗和一艘海盗船;只因为他们是专门抢劫中国渔船的,所以,就放了他们一马;当时就留下话来,如若有事当相互协作帮忙。”范文艺血红的眼睛依然盯着阮中尉。“今天,我们何不利用马来西亚渔船,冒充遭遇台风求助,混上离鸿庥岛最近的南薰礁,报仇雪恨。”范文艺两眼依旧血红,并且发出了残忍的邪光:“马来西亚渔船、海盗、南薰礁、国仇家恨,老子豁出去啦!”
阮中尉依然喋喋不休:“海盗船我已经联系好,他们马上赶过来;我们必须向他们提供中国制式武器,以杜绝后患,事成后,南薰礁上的物资全部归海盗;如果您同意,今天晚上就行动!”阮中尉随即请示“谁负责行动指挥?”范文艺面无表情地木讷吐出:“潘码风。”阮中尉不解的疑问“潘码风?他只是个军医?”
范文艺根本不尿阮中尉的疑问:“潘码风在野外救助训练大队学习过马来语,而且他还精通中国粤语,他去,是不二人选;就这么定了。”说完,随即扬长而去,撂下一脸茫然的阮中尉。。。
范文艺早就想拔掉潘码风这个眼中钉、肉中刺,今天是老天爷送来了机会,他会轻易放弃,不,决对不可能。
阮中尉其人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军国主义分子。偷袭南薰礁驻军,既可以讨好巴结上司,又可以血洗赤瓜礁海战之辱;此次,虽然是他出馊主意地,但是派潘码风去实施攻击,令他心里很不爽。他决定要亲自去敲打敲打潘码风,毕竟,好歹也算是两国交锋,万万不可轻敌大意。
听到阮中尉传达的军事行动命令,潘码风周身冰凉,他知道,“犯瘟疫”对小黎姐动歪脑筋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他是利用手中职权把自己支开,即报复自己,又孤立小黎姐。作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二话没说立即进行出发前的准备。并且故意装作有意无意的说道:“南薰礁的对手比较难对付,不知岛上有麻醉吹管吗?”
阮中尉不知是计,马上回应说:“范上尉调到鸿庥岛时,带上岛五支侦查分队使用的麻醉吹管,你可以统统带上。”潘码风闻言心里就明白了,欲祸害小黎姐的人是“范文艺”无疑;潘码风不露声色,淡定从容的回答:“谢谢您,阮中尉。”并且,相约晚上在海滩码头见面。
送走了阮中尉,潘码风就一直在琢磨该怎样把事情的原委告诉小黎姐。。。
黎阍见潘码风神情不定,欲言又止的,就温和的问道:“兄弟,你好像有心事,舍不舍得跟姐姐分享?”潘码风心底担心黎阍再次着“犯瘟疫”毒手,遂直言不讳“小黎姐,麻醉毒针是犯瘟疫下的手,”“你怎么知道?”潘码风就把自己接到行动命令、自己故意讨要麻醉吹管的事情告诉了黎阍。黎阍顿时气的半晌没有吱声,好半天才从牙缝里吐出来一句话:老娘要整死他!
半夜里,南海又刮起了西南季风,虽然没有头天晚上风高浪急,但也不适合出海航行。“犯瘟疫”严词拒绝了阮中尉延迟行动的建议,以天气固然恶劣,但是敌人往往麻痹大意为理由,命令按照行动计划执行。“犯瘟疫”是巴不得潘码风翻船出事,反正,船上都是海盗,管他个奶奶地!
马来西亚渔船颤抖着离开了鸿庥岛海滩码头,在南海西南季风刮起的晚上,被牵牛鼻子的缰绳用力拉着一般,极不愿意的向着苍茫笼罩的黑夜驶去。
潘码风亲自坐镇在渔船驾驶楼上,作为小渔村长大的汉子,他熟络的知道浪中行船的技巧。一个裹着蒙面头巾的海盗走过来,悄无声息地就靠在他的臂膀上,这让他心里老大的不自在,“唉。。。唉,晕船了!这才离开码头呢,有这么不靠谱的吗?”身边的几个海盗“嘿嘿”的笑出声来,潘码风心生疑窦,瞧了瞧几个笑的怪怪的海盗,再仔细一看裹着头巾的海盗咋就像是个女的,“我的天,小黎姐!”潘码风心头一惊“还真是小黎姐!”顿时就有了想死的心,没出息的自己把姐姐带进火坑啦——
黎阍扬起漂亮的脸蛋,嗔道:“不欢迎啊!”
潘码风一颗心碎得是捧都捧不起来,那里还说得出话来;她是什么时候混上渔船的,自己怎么就没有清场啊!唉,反省都没有用了。此时此刻,潘码风只有把万千不快统统压下心底,温柔有加的对黎阍说:“你帮忙看看有没有晕船的,给他们发发晕船药。”话一出口,又悔死了:世上那有做海盗的会晕船地?
这时,海盗的大哥就站出来打圆场,他摸着一脸的毛脸胡子,“我是阮赐水,是船上老大,岛上家门兄弟阮中尉说今天由你起事,船上兄弟唯你马首是瞻;这老妹子说是你家姐,是你起事的护身符,所以,船上兄弟没敢挡你好事,请潘老大海涵。”
潘码风知道开弓没有回头箭,既来之则安之,遂故意大大咧咧的“嘿嘿”笑道:“谢谢各位大哥的抬爱,兄弟我这厢有礼啦!”
阮赐水笑的一嘴脸的胡子都在颤抖,他的一船人五凑六合的,菲律宾的、越南的、文莱的、马来西亚的、新加坡的、印度尼西亚的、泰国的、柬埔寨的、缅甸的、斯里兰卡的,他把今天来了的,今天人不在场的说出来一大串,不知是故意炫耀实力,还是要震慑一下来自XX海军的潘码风。不管他说的是天花乱坠,还是故弄玄虚,潘码风心里就只装得下小黎姐;所以,他和阮赐水只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应景。不过,从阮赐水透露出来的信息可以知道,他的人马基本上是南海区域各国政府通缉的人犯,都是有案底的人。
不知不觉,马来西亚渔船离南薰礁越来越近了。
暗夜中的南薰礁就像匍匐在海水下的一只怪兽。南薰礁的气候是南沙群岛最恶劣的,因为礁堡紧挨着深海区,其南边方向不远就是一条漫长的大海槽,风高浪急,令人恐惧。毕竟是和正规军交手,海盗们都胆战心惊的蛰伏在船舱中,全没了来时路上的喧嚣,就连惯匪阮赐水也紧张的只晓得“咕噜咕噜”的吸水烟,半晌没有下文。
黎阍失踪,范文艺猜都不想猜,肯定是潘码风那小子给弄上了马来西亚渔船,在他的心底:黎阍就是一只煮熟的鸭子,现在好了,煮熟的鸭子飞了。他咆哮如雷,他将阮中尉骂的狗血淋头,要不是为报国仇家恨,他妈的,他范文艺依着个人的小性子,早命令炮兵把马来西亚渔船轰沉了。
阮中尉不慌不忙,“等潘码风抓人回来,再以违反军纪军规擅自行动处理黎阍不迟,”“他回不来了!”范文艺呼呼冷笑,从牙缝里挤出一段令阮中尉骨头缝隙都发寒的话:“你命令潘码风抓舌头,要活的;我命令,阮赐水那帮混蛋见人就杀,格杀勿论,不要活口!”
阮中尉不无担心的,“可给旅部的行动报告是抓舌头要情报。”“就说是潘码风违抗命令,滥杀无辜,伙同马来西亚海盗拐带缴获的军用物资逃跑。”
范文艺又发出一阵令人发怔的呼呼冷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