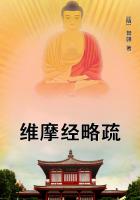且说胡夫人打马回了包子铺,那是六神无主,不知所以,生意亦没有心情做了。扈福所说的五千个大洋她可到哪里去弄?她把炕头上的那架红木柜倒了个底朝天,又把家里值钱的物件变卖个干净,亦不过是凑了一半的大洋,剩下的便再也无处去淘换了。
扈挺在家里盼着胡夫人的再次造访,再来时,那可是白花花的银元啊!过了两日还不见胡夫人的动静,扈挺心里不免敲起了鼓。这日,扈挺在家里坐等,听见梆梆的敲门声,扈挺站了起来,对着院子里的扈福说:“福伯,快去开门,想那胡夫人来了!”
扈福应喏一声,迅速走到门口打开院门,却见门外站着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头戴一盏小毡帽,肩膀上搭着一个灰色的褡裢,正专注地看着扈福。扈福问了一句:“这位兄弟,你有什么事吗?”
那人不搭话,却张大着嘴巴啊啊啊地叫个不停,双手还不断比划着。
扈福看了一阵子,懂了!此人是个哑巴。
院子里的扈挺等了一阵子不见扈福进来,便亦来到了院门口,见扈福正和一个男人聊着天,并不是胡夫人,他亦随即走了过来,站在了哑巴的身侧。哑巴自顾比划着,手舞足蹈,却把扈挺主仆二人看得一脸的懵,哑巴比划了好长一段时间,见二人仍然不明白自己的意思,脸上不免有了几分着急的表情,他用右手做了一个写字的动作,又指了指扈挺家的院子。
这次扈挺明白了,哑巴是想让自己取纸笔来,想把表达的意思写出来。扈挺笑笑,对着扈福说:“你且去取纸笔来,看看他想干什么!”扈福应喏一声,转身进了院子,一会儿又出来了,手里拿了一本裱纸本,一个墨水瓶,还有一支醮墨式的派克笔。
哑巴把纸笔接在手里,在纸上写了一行字:胡清家怎么走?
扈福到现在才明白,哑巴是来问路的。他沉吟了一会儿,从哑巴手里接过纸笔,亦跟着写了一句:哪有什么胡清?
哑巴接过纸本看了看,眉头紧锁,琢磨了一会儿,随即又写了一行字:是我写错了,扈卿家?
哑巴写完字,却一转身,把纸笔递给了身边的扈挺。扈挺接过纸笔看了看,随即亦不加思索地写了一句:顺着此路一直北去,左拐第一家便到。
哑巴看着纸本,感激地朝着扈挺二人连连点头,将写了字的那张纸顺手撕了下来,折叠起来放进口袋,又频频鞠躬致谢,匆匆向北而去了。扈挺二人便返身进了院子,扈福随后又把院门关闭,插上了门闩。
扈挺向屋里走去,刚走了几步,却猛地顿住了身子,立在那里沉吟半晌,突然转身对着身后的扈福说:“坏事了,快去追上那个哑巴,把写了字的纸张讨要回来……”
“怎么了?少爷”扈福懵懵地问道。
“无须多问,快去!”扈挺突然声音提高了八度,焦急地喊着。
扈福见少爷拿了急,便不再多问,转身跑向门口,拉开院门追了出来,街上空荡荡的,哪里还有什么人影?扈福便跑去了扈卿家询问,问刚才有没有一个哑巴造访,扈卿亦是懵神,说并未有客人来访。
到了这个时候,扈福的心里亦多少有了些明白,他在哑巴拿走的那张纸上写了“胡清”两个字,而自己在几天前也写了“杀人者胡清风”的字样,亦是他亲手塞进了毛淤青家的大门。那个哑巴来头不小,看来他是故意把“扈卿”写成“胡清”,有意来套自己字迹的。
扈福思索着,蔫蔫地回了家,等在院子里的扈挺着急地问:“追到他了没有?”
扈福摇摇头,一脸的沮丧。
扈挺问:“你写给毛淤青的那封信,是你的亲笔?”
扈福点了点头。
“会是谁呢?”扈挺喃喃地说了一句。
扈福思索了一会儿,突然抬起头看着扈挺:“是不是那个张泽?”
扈挺愣了一会儿神,随后微微点了一下头,朝着扈福语气坚定地说了一句:“不管他,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走一步看一步!”说着,转身进了屋。
却说那个哑巴,慢悠悠地向北走了两步,见扈挺二人进了院子关了院门,转身向南跑去,跑到巷口往西一拐,那里早等了一个人,正是张泽。张泽问:“怎么样?拿到了吗?”
哑巴点点头,开口说了话:“张科长,一切顺利!”
两人随即翻身上马,扬鞭催马向西奔去,转眼就没了踪影。
原来,胸怀正义的张泽总是怀疑扈挺二人,他不相信软弱的胡清风会是枪杀两人的杀人凶手,再说,说他杀了维州县县长周府安亦实在是有些牵强,他跟周县长无怨无仇,没有作案动机。张泽揣着满腹狐疑去了关押胡清风的牢房,对胡清风说明了来意,并保证给他洗冤雪耻,胡清风便对他道出了实情,把从陌生人手里买枪、扈挺收枪还枪的来龙去脉说了个清楚。张泽听了,更增加了对扈挺的怀疑,他苦思冥想,该如何入手这桩凶杀案,从哪里寻找突破口,思来想去,他想到了递到毛淤青家的那封书信,是谁给毛家递了这封书信呢?是谁这么决绝的认定胡清风是凶手呢?又是谁想把胡清风置于死地呢?
张泽打马回了警务处,到了自己的公务室,从档案柜里拿出了那封从毛淤青家取到的书信,又拿出了刚才讨得的那张裱纸,将两张纸上的字迹仔细地做着比较,他发现扈福写的那句“哪有什么胡清”跟毛淤青家得到的那封信上的字迹一模一样,特别是两张纸上都写的“胡清”二字,简直像是从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从笔墨字迹的粗细推断,张泽甚至可以肯定,连写字的笔都是同一支,都是那只醮墨式的派克笔。如此,一切似乎都明朗了,写给毛淤青那封信的人就是扈挺的老管家扈福,张泽联系着这一系列发生的事情,现在他几乎可以肯定是扈挺借枪杀人,栽赃陷害。可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的作案动机是什么呢?只有一点可以解释,就是扈挺看上了胡清风家的钱财以及他红火的包子铺生意。
张泽正琢磨着,门一响,进来了一个人,张泽忙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说:“曾处长!”
原来进来的这位正是警务处的处长曾悼。
曾悼朝着张泽笑笑,压压手示意他坐下,随即也在一把椅子上坐定。
曾悼笑着说:“怎么?这几天没去陪陪秋云?”
“处长,这几天忙于公务,好几天没去找她了!”张泽笑着说。
曾悼呵呵一笑,说:“你不去陪她,我这个当爹的可就难受了,整天埋怨我给你安排的事务繁重,还说我是有意拆散你们,给我扣了个这么大的帽子,我哪敢呢?”
张泽也笑着说:“呵呵,秋云就是刁蛮!”
曾悼接过了话茬,微微一笑:“是啊!这个丫头被我从小惯坏了,就是爱耍小姐脾气。不过,你还要多体谅她才是啊!”
“是,当然,我也爱秋云啊!处长放心,今天我就过去找她!”张泽说着,端了一杯茶水递到曾悼的手上。曾悼喝了一口茶,问:“你刚才在忙什么呢?”
“喔!我在研究毛三的那桩案子。”
曾悼语气有些疑惑:“毛三的案子?他的案子不是已经结了吗?刘巡长早已向我做了结案汇报,杀人者胡清风不是都承认了吗?”
张泽看着曾悼,说:“我觉得这里面有冤情!”
“有冤情?那个胡清风杀人,人证物证俱全,会有什么冤情?”
“那么我说有人借枪杀人栽赃陷害,处长会相信吗?”
曾悼笑着说:“我的好女婿,你在编故事吧?好了好了,别这么劳累了,还是多回家陪陪秋云吧!”说着,抬起了身子转身欲离去。没想到张泽几个快步挡在了曾悼的前面,表情严肃地说:“处长,我说的是实情!”
曾悼看着神情冷峻的张泽,问:“什么实情?说来听听!”
“我觉得杀毛三的另有其人,绝不是胡清风!”
“奥?那你说是谁杀死的毛三呢?”
“是谁我还不确定,不过我怀疑是扈家村的保长扈挺!”张泽语气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扈挺?”曾悼念叨了一遍名字,陷入了沉思,过了好一阵子又问:“你是说上次杀死毛六的那个人?”
“正是!”
曾悼看着面前的张泽,心里暗暗琢磨着:这个毛头小子,涉世未深,又岂能懂得官场的这汪浊水有多么深呢?那扈挺可是扈信的叔伯兄弟,而扈信又是约长,县长大人的执笔文书,那可是裴县长面前的大红人哪!可以说是神通广大,手眼遮天。况且那扈信的岳丈又是本县司法部部长柳义生。想办扈挺的罪岂是那么容易的?即使警务处抓了他,案子到了司法部,只要柳义生一句话,还不是照样放人?上次办毛六的案子,自己亦是收了其父毛淤夫的重金,本来想办扈挺个死罪,那亦是扈信出面横加阻拦,连人都没抓回来,就迫不得已收了手,那桩案子直到如今还在吊着,亦是不了了之了。
想到这里,曾悼亦沉下了脸,冲着张泽说:“不该你多管的你就不要管,这桩案子由刘普惠负责,没你什么事!”说着,抬起手拨拉开挡在门口的张泽,一闪身出去了。张泽立在那里懵懵的,他没有追出去,他从曾悼的表情上看得出,曾处长是真生了气了。
扈家官庄,扈挺大院。胡夫人终于是来了,她打开了放在桌子上的那个花包袱,里面露出了一大堆的大洋,白花花的一片,像个小山一般堆积在那里。胡夫人看着椅子上坐着的扈挺,说:“扈保长,这是三千个大洋,加上上次拿来的五百大洋,我亦只能凑这么多了!”
扈挺呷了一口茶水,没说话。还是一旁的扈信开了口:“胡夫人,这可不行,我们去县城给你办事,总不能让我们****心再搭上钱吧?”
“这哪能呢?”胡夫人连连摆手,“可是,我已经变卖了家里所有值钱的物件,首饰,亦只是凑了这么多,这几天又琢磨着把包子铺兑换出去,只是还没找到合适的人家……”胡夫人说完,又抹起了眼泪。
扈挺扈福二人相视一望,扈挺朝着扈福挤了挤眼睛,扈福会意地点点头,又慢悠悠地开了口:“胡夫人想把同福包子铺兑换多少大洋啊?”
“一千大洋,亦不晓得有没有人愿意要”胡夫人流着泪说。
扈福腔调有些阴阳怪气:“那同福包子铺日进斗金,兑出去了岂不可惜?这样吧,你且一千大洋留给我们吧,致于救人需要的大洋,先由我们给你垫上!”
那胡夫人听了,噗通一声跪在地上就磕起了头,口中连说感谢。
扈福上前一步扶起了她,说:“胡夫人先别急着谢,就是加上了包子铺兑换的大洋,亦不够五千大洋啊”
胡夫人又皱起了眉头:“这可如何是好?”
扈福掐指算了算,说:“如此来算,还差五百个大洋,不如这样,咱们明日就把同福开张,胡夫人从明天开始可以去包子铺打工,赚取薪水以偿还这五百大洋,什么时候还清了什么时候算完,我家少爷明天就带着五千大洋奔赴县城,去救你的丈夫,如何?”
那胡夫人从扈挺家一踏出来,就觉得“浑身轻松”了,转眼之间,自己所有的家财就都成了扈挺的,自己老板的身份亦变成了打工。如今,她已经是身无分文了,她甚至琢磨着该如何支付陈大爷那里租来的这趟车马费。
第二天一大早,扈挺主仆二人分头行事,扈福去了口埠大集,张罗着开张同福包子铺;而扈挺则骑马直奔县城而去。
到了益都,扈挺径直去了县府大院,他晓得扈信在县府做公,那里有他的一栋专职大院,以前的时候他去过无数次,所以对于路径亦是颇为熟悉。扈挺在县府衙门口拴了马,徒步向里走去,走到独栋大院门口,被一个长官伸手拦下,扈挺抬头一看,却是扈信的警卫副官江古。
“这不是神枪手江古吗?怎么?江副官不认识我啦?”
“吆!原来是扈二老爷啊!快请进。”江古慌忙陪着笑脸把扈挺让进了院子。扈挺进屋落座,把背在肩上的一个帆布褡裢取了下来,放到了桌子上,抬头问江古:“江副官。我大哥呢?”
江古一边忙着斟茶,一边回应:“喔!约长一大早就去了裴县长那里,或是有什么紧要的事出去了!”
“看我来得也是不巧啊!”扈挺纳纳地应了一句。
江古说:“扈二老爷这次来有事?”
“是啊!我是为了毛三的案子来的!”
江古说:“那事我也听说过,杀人犯胡清风已然定罪入案,只等着明年开春开刀问斩了,听说还是警务处的刘普惠办的案子,怎么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没有没有!”扈挺连忙摆了摆手,“江副官听说过警务处新来的张泽吗?”
江古呷着茶,说:“听说过,小伙子是军校的高材生,上学的时候就识得了曾悼的千金曾秋云,两人感情深厚,亦正是因此,他军校毕业之后,被曾悼要到了本县,给了他一个稽查科科长的要职!”江古说着,脸侧向扈挺:“二爷最好别招惹他,他的岳父曾悼亦手握实权,是为老爷的座上宾,那亦是呼风唤雨的人物!”
扈挺连连点头。
两人正说着话,门口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今天这约长衙门怎么这么清闲啊?”
两人循声向门口望去,但见从门外踏进来了一只绣花大脚,鞋面上一朵拳头般大的绸缎牡丹滴溜乱颤,随之闪进来一个横宽女人;见那女人,粗脖子上架着一颗肥脑袋,浓密的黑发朝天扎了一个大发簪,却似一朵被霜冻打萎的萝卜花,无力地蓬松在那里,萝卜花上插满了明晃晃的金银首饰;一张圆圆的肥脸浓妆艳抹,却遮不住满脸的皱纹;小眼睛,宽鼻梁,一对厚厚的嘴唇翻楞着,直压得下颚底下的那堆肥肉颤巍巍地乱抖。那女人立在门口,掐着腰,好似门神一般。身后还跟着两个丫鬟。
江古一看,连忙紧跑两步过去打招呼:“扈夫人,您怎么来了?”
扈挺一看,也认识,慌忙站起身紧走两步过去施礼:“大嫂安好啊!”
此人正是扈信的大太太柳氏。
扈太太搭眼瞅了一眼扈挺,说:“扈挺兄弟来了,怎么不到家里坐?”
扈挺赶忙陪着笑脸说:“大嫂,兄弟也是刚到一会儿,屁股还没坐热呢!”
扈太太又转脸瞅着江古:“江副官,你家老爷呢?”
“一大早就被县长喊去,或是有什么紧要的事商量去了!”江古说。
江古话音刚落,没想到扈太太阴阳怪气地说了一句:“被裴县长喊去了?别是又回扈家去看那个小狐狸精去了吧?”说到这里,她又转眼看着扈挺,“你来说,兄弟!”
扈挺连忙摇头:“嫂子。我真不晓得啊,真不晓得!”
扈太太斜眼瞅着扈挺,说:“不晓得?一个村住着,你会不晓得那个冯灯花?我可是听说那个冯灯花还给你大哥刚刚生了一对双胞胎小子呢?难道这个也不晓得?”
那扈挺一时语塞,摇头不是,点头亦不是,只在那里憋红了脸,茫茫然不知所以。
扈太太看着扈挺一副窘态,昂头哈哈一笑,说:“兄弟莫窘,亦勿瞒我,你大哥的事我是尽然知晓得,只是不跟他一般见识罢了!”
“嫂子大度啊!”扈挺慌忙弓腰施礼,答了这句话也是不太着调。
那扈太太大大咧咧地往椅子上一坐,那胖屁股震得椅子都嘎吱一声响,江古忙端了一杯茶递到她的手里,她接了过来呷了一口,看着扈挺慢慢悠悠地开了口:“要不说这事儿还不来气,你那个小嫂子冯灯花本来是我的贴身丫鬟,也不晓得你大哥是什么时候勾搭上的,竟然偷偷弄回了老家,瞒着我纳了妾,还给他生了两个娃,说起这事我就气不打一处来,等我回了老家一定好好收拾一下那个小狐狸精!”扈夫人说着,猛地喝光了茶水,咕咚一声咽了下去,将茶碗重重地拍在桌子上,那茶碗盖儿因了惯性,在碗口嘎啦啦地转了几圈才停了下来。
扈太太亦是个直性子,话说出来气也消了不少,她看着扈挺问:“扈兄弟这次来找你大哥有什么事吗?”
扈挺赶忙作答:“兄弟是来感谢大哥的,日前有人冤枉我杀了口埠镇上的毛六,若不是大哥压着,想我早已身陷囹圄了!”
扈夫人笑着说:“兄弟真会说话,冤枉你?我听你大哥说那事可是你亲口承认的,若不是我父亲出面说情,怕是你的案子早就压到司法部了!”
扈挺又慌忙起身朝着扈夫人施礼答谢。
这个当隙,门口的警卫高喊了一声:“约长到…”扈挺和江古慌忙起身去门外迎接去了。只留下扈太太不慌不忙地端起了茶碗!
扈信踏进院门口,看见了扈挺,笑着问了一句:“兄弟怎么来了?”还没等扈挺回答,江古却俯身上前,将嘴贴到扈信的耳朵说了句悄悄话,扈信瞪着眼看着江古,随即说了句:“她来做甚?”转身就欲往院外走,却听得背后一声大喊:“你给我站住!”扈信听了那声,好像被蜂子蛰了一口,双腿微颤,蓦地立住了身子,慢腾腾地转过身来,呲牙咧嘴,脸上一副难堪的表情,嬉皮笑脸地说:“夫人啥时候来了?”随即侧脸瞪了一眼江古:“夫人来了,怎么不早说?”
“你少跟我装模作样,见了我就奔逃?还能盼着我来?”扈夫人冷冷地说。
扈信一边向着屋里走着,一边问堵在门口的扈太太:“夫人今天怎么突然来了这里,不知有什么紧要的事啊?”
“这个且要问你,你自己说说,有几日没回家了?”
扈信嬉笑着说:“这些日子公务繁忙,所以少了回家,今晚一定回去……”扈信说着,已然走到屋门口,见扈太太掐腰开腿,犹如门神一般,她那魁肥的身子把本来不宽的屋门堵了个严实,扈信几次想拨开扈夫人进屋,都被她健壮的体肉给弹了回来,扈信脸上便有些懊恼,说:“夫人这是干吗?有什么事回去说,这是我办公务的所在,你在这里闹成何体统?”随即朝着她身后的两个丫鬟喊了一声:“快陪太太回去!”
一个丫鬟机灵,嘴巴贴着扈太太的耳根咕哝了一番。那扈太太便移步走出了屋门口,对着扈信说:“我且听你的,今晚你须得回家!”
“回家,回家,我的好太太”扈挺忙着陪笑脸。那扈太太便领着两个丫鬟,扭扭夸夸地走了。
扈信看着三个人的背影一直走出院门口,不仅摇摇头,轻轻叹了一口气,瞅了一眼扈挺,说:“唉!你这个嫂子啊,连个丫鬟都比不了”他随即一拍扈挺的肩膀,“走,兄弟,进屋叙话”
两人进屋入座,江副官看了茶,扈信就迫不及待地问扈挺:“你那二嫂可好,还有我的大金大银,为兄亦好长时间没回扈家了”提到老家的事,扈信的脸上又重新荡漾起了笑容,特别是提到家里的那对双胞胎娃子,那更是语气欢畅,眼放光芒。
“不瞒大哥,兄弟最近亦是瞎忙,所以没去大哥家走动,想是亦没什么事吧?”
扈信说:“兄弟这次来是留住啊,还是当日回去?”
“当日回去,这次找大哥有事请托,说完了事就回去”
“行,一会儿我跟你一块儿回去!”
“你跟我回去?你刚才不是答应了大嫂今晚回家吗?怎么能跟我一起回扈家?”
“且不用管她,那个肥膘子,我烦她!”扈信说着,侧脸看着扈挺,“对了!你这次来有什么事吗?”
扈挺便对扈信说起了胡清风案子的事,话还没说完,却被扈信从中打断:“你是不是收了人家的银两?”
“是!”扈挺应喏一声,把那个随身带来的帆布褡裢往扈信面前一推,“兄弟岂敢独吞,这不是亦给你带来了吗?”
扈信低头瞅瞅那个鼓鼓囊囊的褡裢,笑着说:“收人钱财替人消灾?”
“不是!”扈挺定定地说。
他这句话让扈信有些丈二和尚摸不著头脑,遂身子往前探探,疑惑地问:“那你是何意?”
扈挺眨眨狡黠的眼睛,说:“警务处有个叫张泽的,此人甚是可恶,正揪住此案不放,只想大哥从中通融,督促警务处尽快了结此案,亦尽快治了那个胡清风的罪!”
“奥?张泽?可是曾悼处长的女婿?”扈信问了一句。
旁侧恭立的江古应道:“正是他”
扈信盯着扈挺,声音变得严厉起来:“你得罪他了?”
扈挺连忙摆手:“没有没有……”
扈信死死盯住扈挺的表情神态,瞅了好一阵子,说:“兄弟别是又做了什么错事吧?”
扈挺被扈信瞅的心里发慌,语气有些支支吾吾:“没有,没有……”
扈信看着扈挺一副坐立不安的样子。亦不再追问,他站起了身子,对着江古一摆手:“已近午时了,去吃饭吧!”一行人遂出了大院,去了临近的一家酒楼。
且说三人在酒楼喝酒聊天,一直到日头偏西,都喝得醉醺醺地出了酒楼,回了县府大院,扈信便吩咐江古牵来了自己的马匹,与扈挺都上了马,两人催马往扈家赶去。赶到扈家的时候,已经是夕阳欲坠了。
扈信家在村子的最西南角,一座气派的古朴大院,大院紧贴着村南的那条东西土路,而这条土路,又是连接村子与外面的唯一出路,所以扈挺回家亦是必路过扈信的家门口。扈挺紧催马步,先前赶到院门,抬起手来咚咚敲起了大门,一会儿锁子打开了木门,先看见了扈挺,说:“二老爷来了,里面请!”扈挺指指身后,说:“你家大老爷回来了,他喝多了酒,快随我一起把他搀扶进去。”
锁子忙跑了出来,搀住在马上摇摇晃晃的扈信,与扈挺合力把他扶下了马,进了院子。
门口的台阶上站着那个二少奶奶冯灯花,她看见老爷回来了,亦忙推开了屋门,三人随即进了屋,冯灯花也跟着进来,返身将屋门关上。
扈信脱了鞋子上了热炕头,冯灯花给他盖上了一条棉被,扈挺便告辞出门,牵着门外的马匹自顾回家去了。
却说二少奶奶坐在炕头,轻轻地揉搓着扈信的额头,娇嗔地埋怨着:“老爷明知不胜酒力,干吗喝这么多的酒?还骑马赶了这么多的路程,岂不叫奴家担心啊!”
那扈信却咯咯地笑出声来:“灯花!我的小心肝儿,我没事,只是刚才觉得有些头晕,如今好些了!”
冯灯花娇媚一笑,柔酥酥地说:“老爷走了这些时日,亦不挂念奴家,是不是把我们娘们儿都忘记了?”
“夫人这是说哪里话,你们娘仨可都是我的命根子,对了,我的那两个娃儿呢?”
冯灯花说:“金儿银儿反蹬了一天,都很疲惫,如今都已经睡去了!”
那冯夫人本来坐在炕头,一只手支着炕沿,身子半是倾斜着跟扈信说着话,却不料躺在炕上的扈信一把揽住她的粉项,轻轻往身前一拉,怪笑着说了一句:“我的宝贝儿,可想煞老爷了!”那冯灯花亦顺势往炕上一倒,娇滴滴轻应了一句:“老爷,你真坏!”两人的脸便贴在了一起,冯灯花刚要伸出朱唇去接扈信那张高高鼓出来的嘴巴,却被一阵浓烈的酒味儿呛得咳嗽起来,还带着一阵子急促的干呕,冯灯花慌忙起了身子,伸出一只手捂住了嘴,轻轻咳了那么几声。
“怎么了,夫人?”扈信扬着脑袋,瞅着立在炕头前的冯灯花问。
“没怎么,你酒味太浓,奴家可是受不了!”
“唉!有些扫兴”扈信悠悠地说了一句。
“老爷猴急什么,你若想那事,可在家里多住些时日,奴家保证好好伺候!”
“老爷哪有那等清闲啊!明日一早须得回去,公务缠身啊!”
两人正说着悄悄话,门外传来一声咳嗽。冯灯花听出了声音是锁子,遂朝着外面喊了一声:“什么事啊?”
“少奶奶,老太请老爷过去叙话!”
冯灯花遂看着扈信,说:“你娘教你过去呢,赶快穿了衣服起来吧”
扈信不敢怠慢,迅速穿戴了整齐,出了侧门,向东厢房而去。推开门,见老太正坐在一把太师椅上喝茶,旁侧有个丫鬟伺候着。扈信赶忙走过去请安:“娘,你身体可安好?”
老太颤悠悠地说:“好!我儿原来回来,都是先到这里给老身请安,这次怎么钻进了偏房,紧着不出来了?”
扈信紧着回道:“娘休怪,这次儿子喝醉了酒,只是觉得头晕,在那屋倒了那么一会儿!”
老太一手端起茶碗,一手捏住盖把儿,缓缓在碗口上拨了拨,又朝着茶碗轻轻吹了几口气,说:“你这次回来,你那扈太太晓得吗?”
“晓得,儿子是经过了她的同意,才回来看望的!”扈信说。
“你休得骗我,凭你那大太太的脾气,她会让你回来看望那个女人?”老太瞅着低头不语的扈信,又说:“我不是阻碍你什么,且说这个冯灯花给我们扈家填了两个大胖小子,这就是大功一件,这个儿媳妇老娘亦是认了,只是你那个扈太太可不是善茬,你若得罪了她,你那岳丈柳义生亦饶不了你!”
“娘莫多虑,儿子晓得该怎么做!”扈信幽幽地说。
“如此甚好,你既然做了此事,就得有本事处理好它,再说了,自古男人三妻四妾亦是再平常不过的事,能否让你的家眷和睦相处,就凭你的本事了!”
老太慢慢悠悠的一席话,说的扈信连连应喏,他给母亲请了安,便退出了东厢房。扈信是出了名的孝子,这是众人皆知的事情。
锁子等在门口,领着扈信去了膳房用饭,吃罢了晚饭,下人们收拾了碗筷,都各自回屋睡了。
扈信搂着冯灯花倒在炕头上,说着悄悄话,旁侧甜甜地睡着两个娃儿,传来了轻微的鼾声。炕台上的一盏双头灯跳跃着两朵豆大的灯火,窜着两缕细长的黑烟,灯烟离灯头一尺又交合在了一起,汇成一缕较粗的烟柱,缓缓悠悠地飘向屋顶!炕头南侧的一扇大窗户,明月映着白色的窗纸,透进来一丝微弱的亮光,扈信紧紧地抱着小娇妻,呼吸有些急促,他大进大出地呼吸流动了屋里本来停滞的空气,空气略微一动,那缕灯烟便晃动起来,幻化成了柔动的丝雾,都四散开去了。
“噗”扈信抬起了头,吹灭了那盏双头灯。屋里开始骚动起来,过了一会儿,黑暗里传来隐约的男人呼呼地喘息声,还伴着女人轻柔地呻吟声……
突然,屋外有急促地狗吠声,屋里的那些声音亦随之停了下来,扈信停止了运动,抬起头听了听窗外的动静,那刚才还狂吠的声音已然没了声息,扈信就琢磨着可能是哪个走路的人惊扰了院子里的那几只大犬。他嘟囔了一句:“没事,过路的!”接着,屋里又传出了“啪啪”的声音,啪啪了没几下,那屋外的狗却又叫了起来,一只叫得厉害,又引得其余的狗也汪汪大叫,院子里顿时感觉像炸开了锅。狗叫声中,还夹杂着咚咚地敲门声。
锁子迅速穿好了衣服,快速向着院门走去,走到门口,把嘴贴在门内,喊了一句:“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