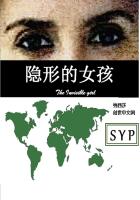邓芈无不讥讽地说:“听说新嫂子进宫,小妹过来向王兄倒喜呀。”
楚文王:“道什么喜呀,出去!”
邓芈透过文王向息妫说道:“嫂子,你就认命吧,谁让你那不中用的息侯来招惹我的王兄呢,这是他自作自受,当年,他舅舅借道给他,结果,回来就把他舅舅给灭了,比起他舅舅来,他息侯也不亏了,嫂子,你就认命吧。”
楚文王怒吼:“出去!来人,把她给我拖出去!”
邓芈高喊着:“你别哭丧着一张脸,你让谁看呢,我要是你,我一头撞死在这根柱子上……哈哈……”
楚文王大吼:“拖出去,传旨宫门,没有本王的旨意,谁也不许放她进宫!”
邓芈被拖了出去。邓芈手里的金钗掉在了地上,寺人从地上捡了起来……
听说女儿被送回了公主府,太后邓晏当天晚上便去看望女儿,女儿伏跪在母后的面前,不服气地听着母后训斥。
邓晏说:“你公公的死,也不能全怪在你王兄身上,周王东迁,礼乐具毁,作为一国君候不修武备,仗着有楚国的庇护,只知寻欢作乐,如此下去,它能长得了吗?有多少列侯枕戈达旦常备不懈尚且不保,如此一只头羊领着一群绵羊,他拿什么立国?就算你王兄不取,你敢保他人不取吗?你起来吧。你王兄不许你进宫,这一阵子,你就好好在府里呆着,想娘的时候,让寺人进宫传个话儿去,为娘来看你。”
再说扁鹊,自从息国被楚国闪电般地灭掉之后,他再次上山来见空山道人,山下百姓听说扁鹊来了,纷纷扶老携幼,络绎不绝来到山上请扁鹊治病。空山道人成了扁鹊的助手,四个小童们抓药送药忙个不停,空山道人不时地嘱咐病人几句,这副药加三片生姜,那一副加两颗红枣。
这时一位病人匆匆挤了进来,他挤到扁鹊面前,爬下就磕响头,他一边磕头一边说:“谢谢神医,谢谢神医,谢谢神医……”。
扁鹊将他拉了起来:“吃了没有?”
病人说:“吃了,今天午时不到,竟打下半碗虫来,现在肚子也扁了,你看是不是好多了?”。
扁鹊不觉皱了皱眉头,他用手在那人的肚子上摸了摸,片刻又问:“全吃吗?”那人摇了摇头:“没有,吃了一半,你说的白信,其实就是砒霜呀,三两砒霜,药房掌柜都不敢给抓,我说这方子是扁鹊神医开的,人家方才给我抓了,他交待我说先少吃点儿,我想也是,就吃了一半,今天下了大半一碗的虫子。要不,我再把下面的一半儿也吃了?”
扁鹊急忙摇摇头:“不用了,我让你米面不沾,子时吃药,那个时辰你肚子里的虫子也饿了一天,此时皆张着嘴等着你的食物,可是你只吃了一半,今天再吃,没有死的虫子它岂会再吃,不要说一半儿,就是再吃一点儿也得先把你自己给毒死。如今你这病已是无药可医,你现在回去,把该要的帐要要,把该做的事做做,三个月之后,你哪都不要去,就守着你的爹娘媳妇。”
那人闻言,只吓得脸色苍白,他一下跪在地上,求神医救命。
扁鹊摇了摇头,那人见再说无宜,也只能哭着走了。
小庵直到掌灯时分才送走了最后一个病人。
空山道人说:“此时月亮正好,何不架个案子,带些酒菜上去,咱俩喝上一杯?”
扁鹊说:“正想如此。”
他们迎月而坐,把酒临风,举目望去,山如峦斗,水如回肠,千水万壑注入一江。
自从扁鹊上山,睢阳子便一直想和扁鹊单独谈谈,先前见病人甚多,后来又见师傅和扁鹊上山赏月,他便一个人守在山下等着他们下山。息国破城,妫生死不知,睢阳子着了魔一样寝食难安。自从睢阳子想明白之后,决心留在山上,他就一直努力忘掉妫儿,可是,谈何容易,白天与师傅师弟们在一起,还不觉得怎么,到了晚上,当自己面对自己的时候,这种思念就象虫子一样无时无刻不在嚼食着他的内心,使他多次萌生再次下山的冲动,可就算自己下山又能如何呢?就像师傅所说,此时下山,你只能是害了妫儿,最终把自己也搭进去。为了让自己能够安心留下,师傅还和自己畅谈了一次,他告诉自己为什么站在山顶瞒目皆路,一但下去就会进入迷宫,问题到底出自哪里?
师傅给睢阳子做了精辟的解释,原来他把阴阳学说进行了实际运用,万物万事,皆逃不出阴阳两字,前面是阳,那后面就一定是阴,上面是阳,那下面就一定是阴,一个人要想确定自己的位置,不但要时时刻刻弄明白前阳后阴,还要时时刻刻知道上阳****,前、后、上、下彼此观照,你才能准确地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这些道理,谁都明白,可到了实际运用往往是顾此失彼,只把一对儿阴阳作为参照而忽略其它,如果有人把前阳稍作修改,你就会进入一个往复遁环的怪圈,骗术往往很简单。所谓兵者,诡道也,即是这个道理,这也是你师傅不让你接近我的原因。
扁鹊和空山道人依山而望,扁鹊问空山道人:“以你的判断,楚国下一步又会向哪国下刀?”
空山道人望着明月:“这次楚国能放回献舞,说明这个文王开始向中原靠拢,向仁爱靠拢,息国被灭,楚国已经推到了中原的边缘,接下来,楚国会进入一个漫长的准备期,否则即便进入中原,他也会很快地败回来。到目前为止,大大小小十多个邦国都被楚去国设县,县在楚语中叫“悬”,楚王不像中原那样将这些邦国分封给臣下,而是悬在自己手里,虽说这些邦国没有了兵马,但要让这些邦国民心稳定,安居乐业,恐怕也非一日之功。”
扁鹊点点头。
空山道人说:“越人兄,咱们还是回去吧,如果你再不回去,只怕我那徒儿又要一夜不眠了。”
扁鹊会心地笑了。
扁鹊回到自己的房间,刚坐下来,便听到外面有轻轻的叩门儿声,扁鹊将门拉开,果见睢阳子站在门外,扁鹊急忙将他请进屋里,两个人刚刚坐定,睢阳子便开口了:“先生周游列国,可有妫儿的消息?”
扁鹊道:“息国被灭,我听说妫儿被楚王虏到了楚国,这也只是风言,再过几日,我准备过江看看,如果有妫儿的下落,我也会及时传到山上。”
睢阳子伏地致谢。
也不知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一天,一群宫女、寺人被赶进了楚宫,钗环也在他们中间,他们既害怕又小心地往前走着,他们打量着这个陌生的地方,这个和中原宫庭完全不样的的地方,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将会是什么,他们也不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发生,他们只知道,死神如同恶梦一样,伴随着他们,他们只知道,一个将军把他们从楚宫拉到了这里,在门外将他们赶下了马车,交给了这里的宰伯……
宰伯把他们带到一个小院里,宰伯面无表情,从他脸上你很难看到接下来的吉凶,不知过了多久,有人抬着食物进来,每人一份地分给他们,接下来,便是一个个澡盆抬了进来,一桶桶热水倒了进去,那些寺人被带走了,院子里留下的全是女人,一个粗壮的老女人指着他们,要他们脱了衣服,跳进水盆里洗澡,接下来是一些宫娥将她们脱下来的又脏又臭,甚至里边还有不少如跳騷、虱子一类小动物的衣服抱了出去,堆到墙外,一把火扔了上去,便噼里啪拉地响个不停……,接下来,又抱来了新的衣服,这些衣服多是丝织绸缎,与息国纯棉大不相同,这些衣服穿在身上,有着说不出的舒服,特别是被风一吹,竟“哗哗”作响。眨眼之间,她们也和眼前的这些宫女们一模一样了,甚至比她们的衣服还要好一些,她们又被赶了出去,同那些息国来的寺人合在一起,说是息国的寺人或宫女,仔细看时,却不难认出,他们大多来自陈国,应是陈国息妫的媵寺媵女,他们看起来比原先精神了不少,他们被赶进了一个大院子,钗环手上还是挂着那个小包裹,她不时地打量着这个陌生的地方,一切都和中原不一样,一切都是凤的图案,不管是圆形,方形、或者不规则形状的器皿,上面的图形嵌饰,几乎都是一色青铜片的凤鸟造形,迎面的虎座凤架悬鼓,两旁各站着夸张的巨形凤鸟上。
宰伯让众人一律站在阶下,他喊了一句:“娘娘……X县的媵寺媵女带到。”
只见妫从里面跑了出来,她一下子将钗环抱住:“姑姑……”。
此时这些人才算见到了亲人,无论是寺人还是宫女,她们哭成了一片……
钗环惊喜地将妫搂住,哭泣着:“我只说这一辈子再也见不着妫儿了,没想到……真没想到……咱息国没了,一切都没了……”
息妫:“姑姑……”伏在钗环怀里大哭起来。
宰伯走过来,小声劝道:“娘娘,凤体要紧呢,身体是爹娘给的,别哭坏了她,娘娘,在这里,就得学会自己个儿心痛自己个儿,不管怎么说,亲人来了,今后的时日还长着呢。”
息妫止住了哭声……
宰伯又说道:“王上有旨,从今往后,你们这些从陈国跟着娘娘的下人就在兰台服侍了,姑姑是老人,这些人你最熟悉,谁的心粗,谁的心细、那个勤快,那个手笨儿,你就看着铺排,缺什么少什么,尽管问奴才来要,娘娘,他们赶了几天的道儿了,今天刚刚进宫,也够劳乏的了,先让他们歇歇,从明天起,兰台的人就全部撤换了。这位姑姑,你是娘娘身边的人,你的房间在寝宫外,伺候起来也方便不是,没事的时候也好陪娘娘说说话,有什么事儿,你再叫我。”
钗环躬身点头。
宰伯:“娘娘,如果没什么事儿,奴才先告退了,亲人相见也有好多话要说,有奴才在旁,也多有不便。”
妫点了点头,宰伯转身走了。
钗环对那些下人说:“以往在息宫怎么做,到了这里还是一样怎么,你们先休息去吧。”
妫拉着钗环进了兰台。
有了这些老人,一切也就跟息国没有什么区别了,第二天,那些在兰台伺候的人真的就一个也不见了。
楚文王在净心房招见钗环,钗环大礼参拜,文王让宰伯赐给钗环一张席片,钗环以头触地:“奴婢不敢。”
宰伯说:“王上让你坐,你坐下就是了。”
钗环这才谢座儿,她小心翼翼地坐在席片上,却仍然是两手支地,垂首而坐,随时准备磕头……
楚文王说话了:“你用不着害怕,抬起头来。”
钗环的头垂得更低了:“奴婢不敢。”
楚文王说:“今天招你来,只是想听听,你们为何会生活在那里,你的妫儿为何又会出现在息宫,那个小伙子哪去了?”
于是,钗环便将妫生下来被庄公遗弃,自己带着妫流落在外,陈后又如何找到他们,结果,被庄公发现,陈后又如何被卫队误杀,自己带着妫又如何逃到曲水桃林,又如何遇上睢阳子,在即将大婚时,睢阳子又如何被歹人所杀,最后又如何回到宫中说了一遍。听到痛心处,楚文王竟也落下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