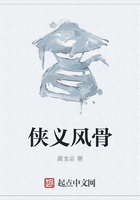娅凝、艳华上一次面对面地聊天,是在娅凝大学毕业那年的夏天。
一天天接近去单位报到的日子,娅凝靠从图书馆借的几本推理小说来打发内心的不安,以抗拒这个现实。
对于将转变成社会人娅凝心烦意乱。老是陷入杂想,高速旋转的社会会像搅拌器一样将她这颗封闭着不够成熟的心绞碎。因为仅是填写履历、合同等程序,就令她生厌了。她小心掩藏着自己的不适应性。
艳华家没有电话,她会突然登门。那天,娅凝看完一本结局马虎深感受骗的小说,心中蒙上了无法排遣空虚。当听到艳华在外面叫门,她欢喜地从床上跳起。由于分隔两地上学一年见不上几次面,娅凝不再像中学时躲着艳华了。
把艳华迎进家,她从厨房端来洗好的一篓脆桃,放在写字桌的玻璃板上。表现出罕有的待客之道。
一旦苦闷,娅凝就变得需要艳华了。
盛夏的泡桐擦着玻璃窗沉甸甸地盛开,挤挤挨挨的。
娅凝背靠墙壁,拱腿坐在床上,她的手腕无力地搭在双膝,在朋友面前舒展着病歪歪的样子。无精打采加上过分消瘦,令娅凝一直给人先天不足弱不禁风的印象,其实她的身体在成年以后健康多了,但她甘愿继续囚禁在这种顽固的形象里。艳华见了说:“真不敢相信,你就要工作了,娅凝,你身体吃得消吗?”她听了淡淡一笑。
艳华拿起一只桃子咬了一口。
脆桃表皮的水珠沾上了她的嘴唇,倏尔被湿润的舌尖舔掉了。她咬桃子发出清脆的实实在在的声响,让娅凝很受安慰。艳华咀嚼得非常精细,她吃东西时心满意足的笑容真是一道风景。
两人交谈中,小卧室没有插销的房门动不动就滑开,娅凝不厌其烦地走下床把它关上,最后她想了个办法,干脆用木椅顶住。这么做是防止母亲、祖母偷听。艳华素来知晓娅凝对家人的排斥,却不知她会在家人面前表现出对自己的排斥。她让出了所坐的靠背木椅去挡住门。然后在床沿坐下了,从她的角度看着娅凝,跟探病似的。
房间里洋溢起了艳华欢乐的声音,娅凝有种感觉,笑声对于沉闷的家庭来说,就像蝇拍打在了苍蝇身上。母亲和祖母一定在外面厌烦着呢。
为了打扰她的笑声,娅凝向艳华倾吐了心里的烦躁,听说工作压力大啊什么的,办理人事关系时,老员工就吓唬过她了……谁知,对于朋友身在福中不知福、把未发生的事想象成灾难的本领,艳华抱以大笑。她完全不能理解,娅凝为何委屈地看待降临在自己身上的幸事?说很害怕在银行这种森严的机构工作。
“我多么羡慕你能进银行啊!”艳华衷心为娅凝高兴。把朋友的顺遂视为自身的幸运,基于艳华对两人友谊百分之一百的确信。
而在娅凝听来,艳华的羡慕是廉价的。她对使用在自己身上的“羡慕”向来视而不见。
她发牢骚并非向艳华寻求解决之道。尽管艳华的生存技能强大,但她没有高超的智慧来宽解娅凝。
娅凝需要念叨。由于艳华不是一个懂得“附和”的朋友,娅凝还得小心措辞。
在娅凝的四周环绕着消极的迷雾,艳华总以为能像踩灭一只烟头那样,轻易地驱散朋友的萎靡。但与此相反,娅凝营建起来的消极的坚壁首先阻挡的就是艳华。比起家人,艳华的积极完全是入侵的异类。娅凝善于沉默,并不意味被说服,那是近乎于逆反、嘲弄的沉默。
聊着天,艳华时不时地翘起脚尖,她脚上穿着一双打工赚来的黑色低帮牛皮鞋。
圆滑的鞋尖凝聚着一抹窗外的光亮。炎夏里即使稍嫌捂脚也穿来给娅凝欣赏了。娅凝对他人的穿戴着装一直缺乏评断之心,见她始终不问,艳华主动说这是才买的鞋子。听到价格,娅凝咋舌,她当时还不能理解质地材料什么的。一味的奇怪,向来节省的艳华怎么突然变得奢侈?
被清苦家庭节俭作风浸润的艳华,上身穿着母亲浅黄色的确凉衬衫,下身绛紫色半截布裙是拿祖母压箱底的衣料在裁缝店缝制的。而这双鞋却花去她暑假打工的全部收入。娅凝礼貌性地夸赞了那双鞋。艳华双手搂着小腿美滋滋地抬起来。为责任感附加了说明,“学期挣的钱全给弟弟交学费了,暑假里挣得我想怎么支配就怎么支配了。”
她说得很逍遥,不容别人品味其中的苦涩。那一刻,娅凝看到某种悲剧性的东西像细细的黑线为艳华勾着边。
过了很多年,娅凝才明白那双鞋的意义。与自己相反,“奉献精神”是艳华生活的支点。艳华渴望踏入社会工作,改变家中的境遇。而凭劳动挣得的鞋子,是宣告向明朗的未来迈步,那是一份自我鼓励。
艳华服从志愿进了一个并不擅长和爱好的专业,为了把文凭上的“专”改成“本”,要比娅凝晚一年毕业。她提及此,认为比复读来得好。两人谈到小镇曾经发生的事件,一个男生考了两年落榜后,从工字楼楼顶纵身一跳,摔在了早市的菜筐里。至今仍令艳华唏嘘不已。
“比起考不上大学,是不是自杀更让父母痛苦?”娅凝问艳华。
艳华讶异地瞪着眼睛,说:“当然。”那神情是在困惑这么显而易见的问题根本用不着问。
“然而,只要他活着,他的父母就没有这样的觉悟。”娅凝说。
在娅凝看来,那个男生只能选择自杀。既然他从娘胎里出来,就被赋予了考大学的重任,那么他吃的每顿饭,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是奔向这个目标来。他那血肉之躯的存在也是为了考大学。目标落空,因为目标而建立的人生只能自行解散。
娅凝又说,镇民们在议论此事时,常会叹息考不上大学的下场多可怜。很少有人批判把考大学当成唯一目标是错误的,因为这样会教坏家里正在用功的孩子。
所以,在这位男生身上根本没有真正的同情。
娅凝对事物独特冷酷的感受往往让艳华既想笑又觉得着迷,她感到思虑深沉的娅凝总希图自己的见解鞭辟入里,语出惊人,从而不停地剖析难题,自寻烦恼。
娅凝也在暗暗琢磨,她和艳华的人生目标是什么?自杀怎样才会在她们身上形成?
她脱口而出,说不能忍受不自由。
被娅凝前面那番理论弄得云里雾里的艳华,这下抓到了娅凝的话柄,她高扬起嗓门,“政治课早就讲过了,没有绝对的自由。”
其实娅凝追求的是补偿性的自由。但她没跟艳华解释,在为生活打拼的艳华面前,那样未免显得贪得无厌。所以,娅凝豁达地让朋友否定了自己。
她望着朋友那张圆圆的像猫似的脸,因为桃子的香甜而泛滥出幸福之笑。心想,艳华和自己有多么的不同呢?在专科学校里,艳华竞争到了学生会主席,她对此职位的风光有着深刻的执念,一定是中学里美丽的学生会主席赋予了艳华幻想,加之长期的卑微感促使人迷恋权力。想来艳华从小到大严肃的一面都是模仿权力。为了保住这个位置,她每天自习到凌晨,保持成绩名列前茅。同时,她还得旁听其他感兴趣的专业课,为求职多开拓门路。
两个人的轨迹竟是大相径庭。艳华经历的周折,娅凝绝不会染指。
当日影移到床面上,娅凝随手拉起窗帘。一束光从窗帘边缘透射向床沿,把坐在那儿的艳华,从额头到肩膀斜切出了明晃晃的白亮断面。在艳华洋溢笑容的表情里,很容易让人忽略她唇色暗淡,脸色枯黄,由每天两份工给累出来的疲惫。这些憔悴的细节悉数显现在了娅凝的眼中。对人向来失察的娅凝从未讲过“你脸色不好”类似的话。但刹那间,艳华自足的样子颇令娅凝不安。
艳华需要有人为她分忧,娅凝注定只是一个袖手旁观的朋友。她为自己一直对艳华不够真心而产生了片刻的负疚。
没什么好抱怨的了。娅凝忽而想起女孩子间最热衷的话题。前年暑假,艳华跟娅凝汇报她谈了男朋友,并把英俊男友的照片给娅凝看。去年暑假,艳华打工没时间回小镇。
娅凝于是问艳华恋爱的事。
被询问的艳华冷淡地说,他去年和别人好上了。她已度过了和男友分手的痛苦期,目前不着急谈恋爱了。就这么轻描淡写地简要地说了说。
娅凝早该猜到是这回事。因为谈了一个多小时,艳华都没有提及男友。娅凝不可能追问其中的细节,也找不到现成的话安慰艳华。她以同样冷淡的反应。“哦——”了一声。两人抱有相反的爱情观。对娅凝来说,可供追忆的恋爱才是永恒的。
落寞的神情没有在艳华脸上停留,转瞬她又翘起了锃亮的鞋尖,露出一口白牙仰头自我开解地笑着,区区的挫折在她那里就是过眼云烟。她兴致勃勃地为娅凝、为自己描绘未来,笃定她们会一起在市区落地生根,住进一座楼里,各自的孩子也会成为好朋友。
…………然后,她恍然想起了。
“娅凝,你看,我都忘了问你了,你谈男朋友了吗?”
“算,也不算吧。”
“这是什么意思?”
于是,娅凝用一种随便的态度说起了她和大学恋人的关系。这样的关系甚至为她所炫耀。
听到娅凝和他去了小旅馆,艳华慌忙地跑到门边,把木椅顶了顶门,又小心地揭开一下挡在门玻璃上的帘子,望望大人们在做什么。这副谨小慎微的样子令人怜悯。
她被吓坏了。明知没结果还要向男方献身,一定是娅凝疯了。艳华一边批评娅凝在铤而走险,一边叮咛娅凝千万别让父母知道。
忧心如焚的语气让娅凝颇为满意。正是厌倦艳华对未来的憧憬,才故意挑衅了她的价值观。
如果说舍友的气愤起码还会让娅凝有一丝感动,那么艳华口口声声的“被玩弄”,则像亲人的唠叨那般令她不痛快。“被玩弄”,是娅凝唾弃的落后的性观念。艳华一直谨守着自己的贞操,很难说这不是男友背叛她的原因。
娅凝不反驳艳华,默默看着她行使理所当然的“亲密”。她出外夏令营,即使家中拮据,也从景区买来纪念品送给娅凝;她擅作主张为娅凝过生日,从母亲的摊位上偷了一只发卡给娅凝,娅凝不愿过生日只顾在写字台前低头写作业,艳华自己动手,去厨房里盛了些剩饭吃。她非要拿自己当亲人吗?
这会儿,她完全不知道自己苦口婆心的规劝,于娅凝像滴进水里的油。
娅凝瞧不上艳华的追求。瞧不上那双鞋,瞧不上她打工赚钱,瞧不上她当学生会主席。更瞧不上她对老师以及任何权力的惟命是从。娅凝淡漠的心,阻挡艳华随随便便闯入,这位康庄大道上的朋友,总是让娅凝格外地加固起萎靡的壁垒。她越是表现得顺从,暗自就越是远离朋友的劝导。
那一次的聊天依然是愉快地结束了。娅凝向艳华保证,她以后绝不会再谈类似荒唐的恋爱。她在作这番保证时,简直变得跟艳华的弟弟一样驯服了。艳华舒了口气,想必是当学生会主席期间,有不少与人做思想沟通的实例,她那肉乎乎的手娴熟地握住了娅凝的手,似乎在把优良的品性传给娅凝。本来这种形式化的煽情举动很令娅凝不屑,但是她又着实感受到了两只手的温差,突然袭来的温暖,就好像寒冷的时候抱着了绒被。把夏天变成了冬天。
…………
七年后的这个下午,娅凝经过艳华家门前,朝那蓝色铁门锁住的二层小楼望了一眼。曾经的保证现在看来是更加可笑了。
她从单位提早回家为了和陶煜约会,他的膝盖伤已无大碍。这注定更加荒唐。
除非七年间艳华的观念变化了,不然以后把这事告诉她,不敢想象她的反应。但预料中的谴责也构成了小小的动力。娅凝现在就像个孩子似的,不知在跟什么作对。或者说,娅凝一直心存反抗之心,然而终究反抗不了其他,只能跟朋友逆反了。有一天她会跟艳华解释,她所作所为正是补偿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