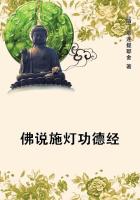“你给我吃吧!”我几乎脱口而出,说完就被自己吓了一跳。那个女的也吓了一跳,她圆睁着眼睛看着我问:“你真的要吃吗?”我扑过去,三两下就把盘里的面条扫光了,旁边的男的看呆了,他把自己盘里的土豆都给了我。他们看着我把盘子都舔了一圈后,关切地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不想解释,就抿了抿嘴撒了个谎,说自己进山没带够钱。我的惨样打动了这对来自广州的夫妇,他们给我煮茶喝,还塞了我一堆牛肉干,我推脱,他们就说:“我们带了太多食物,就当帮我们减负吧!”
我的同胞们真是太善良了,我的眼里闪着泪花千恩万谢地离去。我提着牛肉干上楼,房间里传出长谷夫妇的声音,我刚推开门,他们就说:“璐璐你去哪了?我们给你留了面条和麦片,快吃吧。”
我站在门口沉默了一会儿,拎起手里的袋子说:“这里有牛肉干,一起吃吧。”
燃烧的雪山
快走到乔姆隆的一段,山坡上长着漫山遍野的大麻,乔姆隆是一个大村庄,非常漂亮,可以饱览鱼尾峰的壮景。马队叮叮当当地从石板路上经过,路的两旁点缀着鲜花。这里似乎是一个补给站,物价几乎和山下无差,小店里可以买到20卢比的饼干,我看到直升机在这里起飞,螺旋桨带起一阵狂风在深绿的山谷中盘旋而去。可惜为了赶路,我们并没有在这里停留,而是一路冲到德奥拉里。
到了德奥拉里,雪山就近在眼前了,在山路上一路摸爬滚打,我的衣服已经脏得没法穿了。我把裤子和袜子洗掉,裹着我仅有的薄外套,冻得直搓手。我洗好衣服回来,院子里坐了两个中国人,我打了个招呼,尴尬地笑着说:“好冷啊。”他们问:“你没带够衣服吗?”我指了指挂在绳子上的湿衬衫,说:“都在这了。”女的听了马上起身进屋找了件黑色的抓绒套头衫,说:“穿上吧,送你了。”我谢过这个漂亮又热情的姑娘,她叫叶蕾,和她的男朋友一起徒步,他们还帮我修理松动的登山杖,我脑海中闪过一个主意,说:“晚上你来叫我一起吃饭吧。”
夜幕降临,我冷静地看着长谷开始架锅,桌上雷打不动地摆着一碟土豆,叶蕾如约来敲门,我莞尔一笑对西马说:“朋友请我去吃饭哦。”他们憨厚地说去吧。我和叶携手离去,这个主意真是太好了,既不伤害长谷一行的感情,又能饱食一顿,中国人的智慧是无穷的。
第二天一大早,出门的时候天还是麻黑的,地上结着霜,呼出的每口气都化为白雾在眼前飘,我的手冻僵了,因为低温,手一捏登山杖,皮肤就有被粘住的感觉,泉水也要在嘴里含一会儿才能咽下去。今天我们要上到安纳普尔那峰的大本营,中午在山路上照例只喝到了一点面条汤,但是对终点的期待压过了饥饿感。我健步如飞,这里的草木开始荒芜,雪山越来越近,山脚下忽然出现无数只咩咩叫着的羊,它们挤成一团,堵在山路上不肯往前走,我不得不用登山杖拍它们的屁股,好让它们挪一挪。看来我是很有做牧羊人的天赋的,我带领队伍昂首从羊群中挤过。
终于到了大本营,这里开了两间旅馆,我们选了最高处的一家。几个老外坐在外面的一块空地上,居高临下地看着我们气喘吁吁地爬上来,他们喝着啤酒嚼着薯片,一个女的居然只穿了件背心。再往前更是一惊,几个人赤膊围在水龙头前冲澡,一对情侣互拥着对着雪山亲吻,他们足足吻了一个小时,当我收拾好东西从房间里出来,他们还在那吻得如痴如醉。
大本营被雪山四面环绕,看到了无敌的山景,雪山近在咫尺,似乎伸手就可以触摸得到,偶有几只老鹰飞翔而过,雪山在太阳光线的变幻中变幻,起初我还试图用相机捕捉,最后直接放弃了,因为在阳光的刺射下、在雾气中,每一秒都是不同的景象。
太阳落下,雪山在落日的照耀下,看起来像燃烧起来了一样,整座雪山都变成了金色!夜幕降临,一轮圆月在雪山旁升起,星星在苍穹闪耀,环绕着雪山,这是像梦境一般的景色,像无法描述的仙境,我被深深地震撼了,几乎说不出话来。
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千辛万苦吃着面条汤爬上来,是值得的。我看着自己手里的登山杖,身上的衣服和脚上的鞋子,全是陌生人的礼物;我对徒步一无所知,却跟随着长谷一家来到这里。如果没有这些陌生人的帮助,我就不可能来到雪山跟前,我感到自己如此幸运。
然而,睡在雪山上的滋味却不太好受。夜里,我蜷缩在床上,穿着叶蕾给的黑色抓绒衣,仍然冻得瑟瑟发抖。我呼吸沉重,头痛欲裂,还想呕吐,挨到早上,我总觉得都是因为我太饿了,就支撑着走到餐室点了杯姜茶,喝完后情况并没有好转,我站起来,结果差点晕倒在地板上。我去找长谷,因为大本营的山景太美了,我们本来决定再住一晚,长谷说:“你高原反应了,必须马上下山。”我不想因为自己的情况打乱他们的计划,决定独自下山,长谷却坚持大家全部下山,“如果你晕倒在路上了怎么办?”
长谷夫妇正帮我收拾行李,外面却传来了吵架声,是西马在嚷嚷,他的衣服上沾满了污垢,大声责问着旅馆里的一个帮工,说着说着,他咚的一声一拳砸在了那个尼泊尔人的胸口,那个尼泊尔人哇地叫着跳了起来,冲进厨房拿出一根棍子要打西马,几个人使劲拦住他。我马上问Ella怎么回事,原来是旅馆的院子里有一个失修的粪坑,上面只是草草用塑料板遮盖了一下,西马一脚踩上去,塑料板就裂了,他整个人掉进了粪坑里!他爬出来,追着旅馆的人要一个说法,结果旅馆的人连一句道歉也没有,只是冷冷地说:“你下山去。”西马彻底愤怒了,他追着那个帮工跑,他们在院子里咆哮,一个喊着日语,一个喊着尼泊尔语,梅子和Ella都过去拦西马,一向内敛的长谷夫妇都出动了,叫嚷声惊动了整个大本营,所有游客和向导都围了过来,一场混战眼看就要开始。
这时旅馆的老板出来了,他手里端了杯热茶,悠哉地站在一边,好像他的院子里在演话剧。西马一心要揍那个帮工,他打不过西马,突然用英语叫道:“他们欺负尼泊尔人!”然后又哇啦哇啦嚷了一堆尼泊尔语,不知道从哪里就跑过来几个尼泊尔青年,手里举着大石头,凶狠地盯着我们。长谷终于愤怒了,他冲着旅馆的老板叫:“我要把这一切都发到网上去!”那个老板嘴角一咧,做了个请便的手势。
我的高反都被吓跑了,过去拉Ella说我们快下山去。她只是冷静地瞪了我一眼,梅子和长谷的妻子拦在西马的前面,结果被踢了好几脚,长谷一看老婆被打,扑上去就给了那个帮工的脸一拳,“啪!”一块石头砸在了西马的腿上。几个西方游客和尼泊尔向导拼命地拦他们,眼看拦不住了,他们对着西马叫“快下山!快下山!”西马知道形势不利,“我下山!但是我要在这里洗干净我的衣服!”他站起来,走到水龙头前用冰水冲澡,他的鞋子里灌满了粪便,已经没法穿了,他就穿着拖鞋,我们一行人从大本营往下撤,走出去了很远,我回头望,高地上站着几个黑影,好像在盯着我们。
在路上,Ella对我说:“璐璐,你一直说我们日本人太内向,不会说‘不’,不知道怎么拒绝别人,今天你看到了吧?”
我们从大本营一直下到多旺,当我们第二天走到乔姆隆的时候,听说那几个尼泊尔人还在搜寻着西马,有人在路上拦住西马说在找一个在大本营跟别人打架的韩国人——他们把国籍搞错了,西马当然说不知道。我们在山路上走了4天(当然仍然是吃着泡面),终于出山,回到了博卡拉。
一回到博卡拉我就跑进餐馆猛吃了一顿,见识了山上的物价后我觉得什么都好便宜,领教了挨饿的滋味后我觉得什么食物都很可口,我虽然走成了半残,但是胃口依旧很好。
下山后的隔天晚上,我和长谷一家约好吃告别饭,不料在店里碰见了京苏,她也刚刚从山上下来,只不过她走的是大环线。她见到我显然很激动,眼睛里居然泛起了泪花,她拉着我的手说:“一起回加德满都吧。”我被她的友情感动了,跟长谷一行道别后,我在博卡拉又休整了几天,和京苏一起回到了加德满都。
从加德满都到樟木只要四个小时,我已经离家半年了,似乎从这里回国再合适不过了,我就这个问题自我抗争了好几天。我出发的时候以为按照我的预算,走到尼泊尔就应该回去了,没想到我一路省吃俭用,特别是我在印度的超低开支,留给了我一个惊喜:我还有两万多块钱,也就是说,我比我原先预计的节省了一半。
这些钱能让我走到哪里呢?我心中并没有谱,我上网查资料,又翻开世界地图仔细看,慢慢地,我有了一个模糊的想法,它听起来很遥远:我想去埃及。
我照着地图去找埃及大使馆,地图都是一些没有人性的家伙印的,我千辛万苦摸过去却扑了空,地址是错误的,大使馆早就搬家了。我折回旅馆找到大使馆的电话打过去,对方说:“你可以在这里申请,但是不确定有没有签证给你,要等开罗的批文。”我问他多久,他说:“最少10天。”
放下电话我就打消了从尼泊尔去埃及的主意,签证要等10天,还不确定有没有,这种风险我不愿意冒。我查了尼泊尔飞埃及的机票售价,并不便宜。我左算右算,算出回到印度,再从印度飞埃及是最划算的路线。此时我在尼泊尔已经待了近两个月,我已经可以重新申请印度签证了。我和京苏一起去泰梅尔区的印度领事馆申请签证,护照都交上去了才告诉我,“因为过节请你10天后再来领签证。”
我和京苏呆滞地在加德满都吃吃喝喝又等了10天,搭了趟廉价航班从加德满都飞到了新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