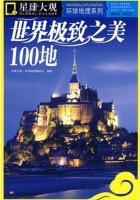“你不认识我了吗?我是西马啊,之前我们在加尔各答见过。”我还是想不起来,加尔各答的日本人实在太多了。但是这些都不重要,我问西马是否也要去徒步,他说是的,他也没有雇挑夫和向导,我马上就问能否跟他一起走,因为我不认路,他笑着说当然可以。我以为西马也是一个人,结果他打了个呼哨,从角落里钻出来一堆日本人。这是个大家庭,西马和他的朋友梅子以及日裔澳大利亚女孩Ella,还有一对姓长谷的日本夫妇,长谷的老婆是个日裔巴西人,还有他们九岁的女儿理子。
我看到这么多人不禁吓了一跳,长谷似乎是这个团队里的头儿,他跟我介绍说他们准备一路在山里自己搭灶做饭,预计走8?10天,问我愿不愿意加入,如果加入的话就把食宿费交给他,我问他多少钱,抿着嘴等他报一个天文数字,结果他说:“3000尼币就够了。”我惊诧,3000尼币怎么会够呢?我查过很多前人的攻略,走一趟ABC,食宿费至少要花到10000尼币,我虽然心存疑虑,但是这种省钱的好事我是不会错过的。于是我们一群人浩浩荡荡组成了一个国际纵队,朝山里进发了。
七个人,两包泡面
我们从纳亚普沿着一条田间小路进山,起初的时候地势平坦,景色也平平,一个村口的开阔地上用几根长竹竿搭了个三角形的支架,挂下两根麻绳绑着一个板凳,便成了一个秋千,这就是村里小孩的全部娱乐了。我进边上的一家小店想要买瓶水,结果他开价50尼币,同样的水在泰梅尔区只要10尼币。
长谷一行看着我要去买水都很诧异,我便忍住不买,跟着他们继续走,到了一户农舍,他们拧开农舍前的水龙头就喝,我也学他们的样子去灌了一壶水,灌完举起瓶子一看,水里漂浮着很多不明黑色杂质,西马看我不太敢喝的样子就过来安慰我:“这是经过大山过滤的水,比你在店里买的还要好!”
“之前我走喜马拉雅徒步线时候也是一直喝这种水,完全没有拉过肚子。”长谷说。他们柔弱的日本人喝了都没事,那我自然就更不用怕了。
山里人的智慧是无穷的,他们在岩石的夹缝里插一片竹叶,涓涓细流就从竹叶上往下滴,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水龙头,尼泊尔的瓶装水喝起来都有点酸涩,这里的山水喝起来却甘甜清洌,从此,我过上了喝山水的日子。我们无止尽地在山路上穿行,经过一片又一片的村庄,还曾数次迷路,幸亏西马会说尼泊尔语,在田间劳作的农民总是很乐于给我们指明方向。
一直走到中午,我们在一处溪边停下来搭灶做饭。长谷是个瘦高个儿,他把包卸下来,掏出瓦斯炉,架起碗大的小锅开始煮泡面。长谷夫妇在一边忙活,Ella躲到树丛后上厕所,结果被蚂蟥吓得跑了回来。我跟理子玩,理子虽然才9岁,却已经走过喜马拉雅徒步线,她生得手长腿长,走路的时候一直冲在最前面。
我突然觉得这种家庭野餐似的场面非常和谐,便掏出了包里的7个煮鸡蛋跟大家分享,这是我在进山前煮的,准备带在路上吃。长谷煮好了一包方便面,小锅在七个人中传递,我发扬中国人的谦让精神,我要维护中国人的形象,不能让人家觉得我很贪吃,我心想。于是到我的时候我似乎只是舔了舔锅边就把它递给了旁边的梅子,这只是我的虚晃一招,先让别人吃饱,那剩下来的食物就都是我的了。果然第二锅泡面就来了,这次我吸溜了几口面条,然后我又开始了镇定的等待,等着第三锅食物轮过来。我等啊等,一直等到长谷夫妇开始往包里塞炉灶,我才醒悟过来,这就没有了?七个人就吃两包泡面吗?我寻找着梅子和西马的眼神,想看看他们是否也跟我一样惊讶,结果他们都看起来一脸平静。长谷来吆喝大家继续上路,他们在前面有说有笑,我疑惑地跟在后面,这怎么可能吃得饱呢?哦,我知道了,晚上一定有大餐等着我。
我很快就饿了,梅子和Ella走得很慢,我们几乎每走一个小时都要歇一歇,长谷就会给大家发一块饼干或者一颗糖果,含一块糖果在嘴里,饥饿的感觉就不会那么强烈。走过一条铁索桥,进入闷热的森林,路也变得不再好走,我在碎石子路上滑倒了数次,因为下起了雨,一些路就成了烂泥堆,还有几处滑坡,我又饿又累,浑身疼痛。在出发之前,每个人都跟我形容走ABC跟去隔壁老王家一样简单,此时我在心里把他们挨个骂了个遍。到了下午5点,我们到了托尔卡,这时我们已经在山路上整整步行了9个小时。
托尔卡的旅馆开在山顶的一块平地上,站在山顶上俯视底下的梯田和消失成了一个黑点的农舍,别有一种成就感,旅馆的院子里居然还栽了几株大麻,Ella一看到就扑了上去,巴不得挂到大麻树上。这些山间旅馆都有自己的规矩,他们的房费低廉,有时候甚至不用付,但是你必须要在里面点餐,因为他们主要靠卖吃的来赚钱,山里无交通,食物的运输都是靠挑夫,自然就比外面卖得要贵,比如泰梅尔区一份60尼币的手抓饭,到了托尔卡就卖到了280尼币。我本着对这些规矩的了解,就认定晚上一定能吃到大餐,再不济,也总能吃饱吧,我心想。
西马来叫我,长谷把炉灶支在房间里,推开门一股暖气涌来,我期待着大餐,结果看到长谷仍在痴情地煮着他的泡面,桌上摆了一碟煮土豆,我数了数,一共是8个土豆,每个土豆差不多只有鸡蛋那么大。
“好贵啊,这8个土豆就要180尼币呢。”梅子一边剥着土豆一边说。“这……就是你们点的吗?”“是啊,不点餐的话就不给住,就只好点了个土豆。”我的心都碎了。
第二天清晨6点半,吃过长谷煮的红茶和几片奶酪我们就出发了。这天的路全是上坡,我的左膝开始疼。
长谷是个非常负责任的人,他背着30公斤的包,永远走在最后,他要确保没有一个人走失。中午我们在瀑布边的一块阴凉地上架锅煮饭,照例是七个人两包泡面,还有一点咸麦片。我总是感到饿,开始怀疑自己的胃是不是比别人的要大,当我感到饿的时候,就喝几口泉水,我饥肠辘辘,身体却有一种像被清洗过的舒畅。天又下起了雨,我们经过一处塌方,看起来像是发生了山体滑坡,还有落石不停掉下,原本的路面只剩下了一掌宽,一不小心滑倒就会直接掉入山涧。山里的太阳起得早,刚过8点,阳光就很炙热了。在太阳底下徒步是最折磨人的事,尤其是艰难地往上攀登的过程,走几步衣服就被汗水濡得可以拧出水来,太阳烤得人头顶都开始冒烟,下午2点,我们的体力都已耗尽,就在基努停下休息了。基努有一个温泉,时候还太早,精力旺盛的长谷夫妇和西马出门去泡温泉,我觉得我熬不到吃晚饭的时刻了,趁他们出门,赶紧跑到旅馆厨房说给我来点吃的,我不想让长谷夫妇他们看到我偷偷点东西吃,他们一路上对我非常照顾,如果给他们看到我在偷偷吃东西,那意思似乎就是他们做得不够好。
老板端来一小碗清水面条,160尼币,面条清晰可数,看起来还不够我塞牙缝的。隔壁桌的一对西方情侣,两人点了一碟炒面,然后把桌上的一整瓶番茄酱都倒在了面里,原来他们主要是吃番茄酱来了。我正感叹着他们好聪明,Ella不知道从哪里过来了,我心中一惊,用颤抖的声音问她要不要也吃点面,她婉言谢绝,说要等长谷他们回来开晚饭。她的语气让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没有什么组织观念的人,我们结队进山,长谷和西马替大家负重,几乎所有的食物都由他们背着,我却偷偷躲起来吃东西。我感到十分羞愧,同时暗自决定下次吃东西一定要更加隐蔽才行。
进山后的第三天,并不算辛苦。前一天好不容易爬上基努,早上看到一路垂直下降的石阶有点崩溃,我头一次发现原来下山比上山更困难,因为掌握不好节奏,膝盖越发疼痛。我们一路下降到竹林,这是谷底的一块平地,毫无视野,雾气弥漫,阴暗潮湿,不知道为什么人们会选择在此停留,当我们到达的时候竹林的旅馆竟然几乎快满了。
我们在竹林住到了一路上住过的最烂的店,房间没有被褥,被子居然要收100尼币,长谷自然是不会给钱的,提议说大家忍耐一晚。山间的夜晚非常寒冷,我没有厚衣物,只有一条薄薄的抓绒睡袋,不知道晚上要怎么过。洗澡也变成了难题,热水是要收费的,而且还定时,100尼币洗10分钟,我虽然理解山里物资运输困难,但对这种钻钱眼的行为非常反感,我的心情变得很差。我想我心情差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饿。既然今晚注定挨冻,那么我就一定要补充点热量。我在院子里等着长谷他们上楼,一直等到了天黑。
他们一走,我马上一个箭步冲进了旅馆的餐室,餐室里烧着火炭,暖和极了,几个人正围在桌边吃饭,一个女的娇声用中文说:“我饱了,吃不下了。”她推开她面前的一盘炒面,盘子里起码还剩下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