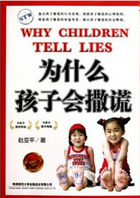“砰砰砰”大力的敲门声将我从熟睡中惊醒,愣了半晌才反应过来有人敲门。
“予婳,予婳!”
是颜钰的声音。
我急急应了一声,怕他一个冲动直接把门砸开了。
翻身下床,动作利落无比,然因心急没能注意到自己体力的变化。
“来了来了,大早上的做什么扰人清梦。”我一面抱怨一面开门。
颜钰兴奋的开口,“予婳,有事干了!万家家仆万一失踪后被人发现尸身悬挂在城门上,万二疯了,整日里说着胡话,衙门束手无策来找咱们帮忙。”
这都什么跟什么乱七八糟的,万一万二又是什么?但有一点我是听懂了,又死人了,而颜钰很兴奋。
“你这么兴奋做什么?死人了你就这么高兴?还有衙门的人是怎么找上来的?”
“你哪来这么多问题!一句话,帮还是不帮。”
这死孩子还吃准了我不会拒绝的心理,有心拒绝,好奇却占了上风。最后还是咬牙切齿的点头同意了。
“给我一炷香功夫,还有叫上晔清,至于尉迟,你去问他,他若爱去便去,不去就随他。一炷香后大门汇合。”
丢下这么句话,我“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颜钰摸摸鼻子,转身去喊人。
一炷香功夫我收拾妥当,准时来到大门口,看见晔清,颜钰,尉迟已在门口等着我了。晔清双手负后,眼含笑意,尉迟和颜钰瞪着眼互相对峙着。得,不用想,这两人准时又斗了起来。
“衙门那都打点好了?”
“早就准备好了,咱现在是挂名捕快了。”
“哟,身份都整好了,颜钰,你这效率还挺高啊。”
“哪里哪里。”
“那什么尸体搬下来了?”
“早搬下来了。”
我跨出门槛向外走去,边走边问,“这事知道的人多么?”
“不多,”颜钰亦步亦趋跟在我身后,“发现的早,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衙门一早就给人弄下来了。”
“那咱先去城门瞧瞧。还有你早上说的什么万一万二乱七八糟的,再给我讲一遍。”
于是在去城门的路上,颜钰把来龙去脉给我讲了一遍。
“这么说,这万银也是个有意思的,给家仆取名竟按数字来,若是排位百后的怎么办?难不成叫万一百零一、万一百零二?”
“嘿!我也这么想的,说不定还真是这样。”
尉迟听了,对此嗤之以鼻,照例先冷哼一声,“不过普通人家,哪用得上一百多号家仆,你们多虑了吧。”
颜钰不悦了,“你不了解情况就不要瞎说,那万银财大气粗家财万贯,雇用个百来号人再正常不过,这可不是你这种没见过世面的人能理解的。”
“哼。”尉迟扭头不与颜钰争辩。
我则早拽了晔清先行一步。
几句话间,就来到了城门前。
这城墙高约四丈,城门高不到两丈,约莫一丈多些。城门上方约一丈半的高度插了一柄利剑,在阳光下闪着刺眼的光。想来这万一便是被挂在这剑上。
也就是说这柄建距地面约三丈,距城墙最上端约一丈。这个高度对我来说是没什么问题,然对普通人来说就有些难度了,更何况不仅要将剑插-入城墙上,还要带个人上去。
我对颜钰道,“能叫城门守将下来么,我想问几句话。”
颜钰点头,“没问题。”
事到此,颜钰神秘的来头我约莫能猜到些,却一直没有询问。他既不愿说,我自没有勉强的理儿,况我吃他的喝他的,该守的底线还是不能碰的。
颜钰不知给那守将看了什么腰牌,那守将瞬间恭敬起来,对颜钰点头哈腰,差点就要跪下了。
在我看不见的角度,晔清隐在袖内的手翻了个结,莹白光点在指尖隐隐跃动,随后指尖一弹,光点向我飞来没入我的体中。
“这位就是县令特聘的协助破案的高人。”颜钰指了指我对那守将道。
“久仰公子大名。”守将朝我抱拳。
我纳闷极了,颜钰压根连“高人”的大名都没说,哪来的久仰,况我为这身绿衣特意梳了个时下女子流行的发髻,怎么我就成公子了?
我狐疑看向颜钰,他一副见鬼的神色看着我,再看晔清,一如往常的淡定,而尉迟虽没颜钰那般夸张,眼却也直了。
如今时间紧迫,我着实没有时间去弄清究竟,只能先顺着那守将的话应下来。我也朝他抱了抱拳,“叨扰守将还望见谅。”
“无妨,公子直问便是。”那守将是个彪形大汉,嗓门极大。此刻大手一挥,很是豪迈。
“这万一的尸身是今日才发现的?”
“是,今日寅时一刻开城门时发现的,兄弟们见状就直接去报了官,送到衙门去了。”
“尸身不是被剑刺在城墙上的?”
“不是,尸身的腰上系了条短绳,绳子的另一端挂在了剑上。”
“昨夜晚间没有什么异动?”我指指上方,“没有什么可疑的人上城墙?”
“没有,”守将答的很肯定,“若有人想城墙一定得先从下面上去,昨夜我一直在城下当值,并没有什么可疑之人上城墙,若是有人没经过我直接上了城墙,上面的兄弟也一定会发现的。”
没有可疑之人,城上城下均无异动,那么万一是怎么被挂上去的?除非他们里应外合联合,合力将万一挂上,但这又说不通,一群守城的有必要与一个小小家仆过不去么?再说若要杀人都恨不得将尸体藏得越隐蔽越好,这凶手怎么偏反其道而行?若凶手是昨夜在城墙上守城的人,的确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但却很多问题都无法解释。
凶手应该不是他们,然该问的问题还是要问的。我遂问道,“你的那些兄弟都是可靠之人?”
都说武将心思直,这话用在这位守将身上是一点不假,“我这群兄弟都是跟我一起出生入死过的,绝对都是可靠之人。”
先不论这话的真实程度,起码这守将对自家的兄弟态度是一目了然。
“你们是怎么把万一弄下来的?”
那守将不好意思的搓了搓手,“说来惭愧,这人就被挂在这剑上,可公子您也看到了,这剑的位置挂的忒刁钻,我等兄弟一群人都无法跃此高度,只能从城上吊两根绳子,下到那剑的位置,将那尸体给拉上去。”
“那剑为何还在上面?”
这大汉饶是脸皮再厚也红了脸,支支吾吾,“那剑实在是插-得太紧了,我等实在是无法将其拔出。”尸体不是被剑刺在墙上,而是腰上系了绳子挂在剑上。怎么这凶手好像知晓若是用了第一种方法,这群人断然无法将尸身拿下一般。
“这长寿县里的人有人能将剑拔下么?”
“据我所知应该没有,长寿县里大部分人都没怎么练过武,能拿得出台面身手的人,基本都在这了。”
我了然点头,唤道,“颜钰。”
颜钰与我默契对视,走至城门下,一跃而上,身形敏捷如猎豹,在快到达那剑的所在位置时,迅速伸手,一把握上,轻巧一抽,那剑瞬时就被抽了出来。
颜钰轻轻落地,连衣角都整整齐齐,好似他方才不是在飞檐走壁拔剑,而是轻松的弯腰捡拾地上的东西。
拔剑需要多大的功力,这守将再清楚不过了,自己手下身手最好的兄弟也只能堪堪跃到那个高度,若再伸手拔剑,那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了。
而这瘦弱的青年,只轻轻一跃,伸了伸手便轻松取了下来,且脸色正常,果真不容小觑,因此对颜钰是愈发恭敬了起来。而能令身手如此厉害的人臣服之人,想必更是有过人之处,因此这守将连带着对予婳也愈发的小心起来。
我接过颜钰手中的剑细细观看。
果真是把好剑,剑身在阳光下闪着寒光,剑身锃亮,伸指弹之铮铮作响,且一滴血迹都没有,可偏这干净的不能再干净的剑身却泛着寒气,一股浓重的血腥味在空气中蔓延,诉说着它的嗜血。
“那尸身可有异常之处?”
守将沉吟片刻,“说实话,我行兵多年也很少见到过这么惨的死状。那尸身上血腥味极重,身上的衣服都被血染透了,胸前好像破了个窟窿,我怕破坏了证据就没有掀开看。且神色可怖,眼睛鼓出,好似受到了极大的惊吓,他的十指被连根切断,只留下一个光秃秃的手掌。”
那守将说完忍不住搓了搓胳膊,神色不忍,看来那尸身的样子的确震惊到他了。
该问的也问差不多了,我准备告辞。
“如此多谢了,若有异常还望及时通知我等。”
他一抱拳,“公子放心,若有情况在下一定及时相告。”
这人为何总叫我“公子”?难不成因为我总扮男人真变成男人了?
我们一行四人离开城门准备去下一个地点。
我问晔清,“方才那守将为何一直称我‘公子’?”
晔清闻言笑而不语,十足的神秘。
我只好又问了一遍颜钰。
颜钰抱着肚子笑弯了腰,“你真不晓得原因?你自己低头瞧瞧你自己!”
我狐疑看向尉迟,希望他能直接告诉我,他却别扭的转过了头,从鼻腔挤出了一个哼声,听着竟带着丝不好意思。
无奈我低头瞧自己,不看则已,一看吓人。
我腰间原本缀着一圈流苏,行走款款随风摆动,如今却是不见了,不仅如此,我这身女款绿衣也变成了绿色长衫,完全就是男子的行头。
我大惊,伸手摸了摸我的腰间,咦,流苏明明还在,这衣衫也分明还是我早间出门穿的那件绿衣。
我目光狐疑的在晔清,颜钰还有尉迟身上逡巡,有些不敢确定。
所以,我这是被下障眼法了?还是比我自己下的障眼法还厉害高明的那种?我自己下的障眼法只是针对别人,而这个却是将我自己也骗了过去。
是谁,尉迟,颜钰或是晔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