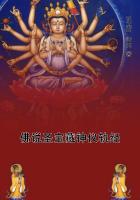那一天发生的每一件事,林薇都记得很清楚。
傍晚五点五十分,她从学校回到家,邻居家的女主人掀开门帘,探出半个身子来对她说:“刚刚林凛的班主任打电话过来,问他病好了没有,明天会不会去学校,好像有个什么测验。”
“他哪有什么病?”林薇脱口而出。
大学一早要晨跑,去一次敲一个章,一学期坚持下来就有加分。所以,她总是很早出门赶过去,就为了能多拿几百块奖学金。这几天也是一样的,她早上出门的时候,林凛还刚刚起来,像平常一样刷牙洗脸吃早饭,然后换衣服理书包,一切正常,并没有什么不对。
“那我就不知道了,”邻居家的女人看了她一眼,讪讪地道,“反正他们老师这么说的,我白天上班也不在家,没看见林凛。”
林薇有点尴尬,赶紧道了谢,进屋去看,林凛果然还没回来。家里就这么巴掌大一块地方,走的时候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她愣在那里,心里还在想,这小子跑哪里去了,等他回来了,一定要他好看。她去楼下厨房淘米,插上电饭锅烧饭,又炒了个菜,一边做一边等,但却没有等到林凛,一直都没有。
那时已经是初秋,天黑得早了些。钟敲过七点,林薇坐不住了,推了自行车出门去找。先在弄堂里转了一圈,然后又到平时常去的饮食店看了看,都没有。她有些急了,在路边找了个电话亭打给何齐。听筒里的“嘟嘟”声响起来,她的心倒放下一些,想林凛大多是跟何齐在一起。这些天何齐突然不去接他了,他表面上没有什么,心里还是难过的,她不可能看不出。
但那“嘟嘟”声一直就这么响下去,没有人接听。林薇挂掉电话,硬币退出来,再打一遍,还是这样。她又急又气,骑车回去,咚咚咚跑到楼上,邻居又探头出来看,房门仍旧关着,林凛还是没回来。天完全黑下来,窗外的路灯亮了,她慌了神,想到报警,转身从屋里出来,才刚下楼,就看到一楼的公共厨房里站着两个警察。
后来,她在王俊从法院复印出来的案卷上看到过这一连串的时间——
200×年,9月20日,下午5点15分,凶案发生。
5点20分,嫌疑人何齐、胡凯被抓捕,嫌疑人林凛(未成年)驾驶嫌疑人何齐提供的车辆逃逸。
5点35分,嫌疑人林凛逃逸途中遇车祸,在警方控制下入院抢救。
7点50分,嫌疑人林凛的亲属林薇被带回分局协助调查。
当夜,林薇在公安局接受问询,因为她的身份到底是嫌疑人还是嫌疑人家属尚未有定论,几个办案的警察对她的态度也不大好拿捏。没人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事,她被带到一个小房间,里面摆着一张桌子几把折椅,墙上没有挂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标语,也没写“禁止刑讯逼供”,看样子应该不是审讯室。从晚上到半夜,前前后后来了几拨人,反复问她相同的问题:
“林凛是你什么人?”
“你认不认识何齐?”
“什么时候,在哪里认识的?”
“他跟你什么关系?”
“胡凯呢?跟你什么关系?”
“听没听他们提过沈继刚这个名字?”
……
林薇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坏了的发条玩具,机械地重复着那些答案。至于她为什么会在这里?警察为什么要问她这些?所有问题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她不允许自己去想,但即使不想,却也有着极坏的预感。
每隔一阵,她就问一遍:“我弟弟林凛在哪儿?他现在怎么样?”
警察们表情淡漠,并不回答。
就这样,直至凌晨,最后一拨问话的人走了。又过了一会儿,一个女警走进来,在她面前的桌子上放了一碗温吞吞的方便面。从午饭到现在十几个钟头,她什么都没吃,水也不曾喝过一口,奇怪的是一点都不觉得饿。她坐在那里没动,女警也不强迫她吃,放下面就准备走,不知是真的同情她,还是审讯策略,离开之前又转回来,对她说:“你弟弟在区中心医院,手术做完了,还没醒。”
林薇迷茫地抬起头,医院?手术?她不懂。
“你知道什么都说清楚了,就能出去看他了。”女警继续说下去。
“我知道的都说了。”林薇回答,喉咙发出的声音有点陌生,好像根本就不是自己的。
“你这又是何苦呢?”女警叹了口气,“你弟弟未成年,而且根本不认识被害人,现在弄成这样,是为了什么?你顾着你男朋友,也得替他想想。”
许久,林薇才弄懂这话里的意思,整个人却还是麻木的,她很难接受这个现实,林凛出事是因为何齐。
女警等了一会儿,见她始终没有反应,终于还是打开门走了,之后很久都没有人再进来。问询室里没窗,也没挂钟,她只能大概估计着过去多少了时间。二十四个小时,她心里想,他们可以留她二十四个小时,如果超过了,那么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赖志成是在半夜里被一通电话叫起来的。过去的大半年里,这种事情已经发生了多次,好在他年纪大了,睡得也不沉,并没有觉得多痛苦。次数多了,再在静夜里听到那一阵阵催魂的铃声,竟然连心慌的感觉都没有了。
但这一次却是两样的,电话那一头不是何齐,也不像光善堂那帮小的管他叫“阿Sir”,反倒例行公事的喊了声“赖先生”——是上海那边的张律师,到底是职业素质,几句话就把事情说清楚了。
赖志成听得坐起来,后来干脆就下了床,开口道:“先把人保出来吧。”
那边答说:“被害人送医之后宣告死亡,重大刑事案,四十八小时都没到,要取保候审恐怕有难度。”
“有难度?去找领事馆,找侨办,务必给我把人先弄出来!”他提高了声音。
“只是何先生,对不对?”那边又问。
“是,只是何齐。”赖Sir回答,待电话挂断又拨了另一个号码,叫车过来,直奔机场。
民航包机在上海降落已是次日天明,太阳从近海的滩涂上升起来,机场跑道上晨风凛冽。赖志成从舷梯上下来,上海这边的律师及一干人等已经在下面候着了。
“怎么样?”赖Sir问。
张律师答:“领馆方面还在交涉,警察局死抠着规定不放人,估计不满四十八小时出不来。”
“人见到没有?”
“在审讯室见过一眼,没单独见,也没说上话。”
“怎么样?”
“情绪不太稳定,看见我就叫,要我去医院看那个孩子。警察就借这个机会把我带出去了,否则倒还能多知道一点情况。”
“就是那个行凶的孩子?”赖志成问。
“是,” 张律师点头,“车祸的时候,人撞在方向盘上,脾脏破裂。”
“现在怎么样?”
“手术已经做完了,但情况好像不大好,我在医院留了人,一有什么就打电话过来。”
“雨林道的人撤了没有?”
“没有,还是老样子,二十四小时盯着呢。”张律师答。
“有什么动静没有?”
“好像也派了人去医院和警察局打听消息,再多就不知道了。”
赖志成点点头,道:“尽快把何齐保出来吧。”
言下之意已经很清楚了,就怕何齐这种状态下面乱说话,特别是万一那个孩子再有什么事的话。警察局那边搞刑事审讯的都是多年的老江湖,是绝对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
赖志成坐上车往市区去,一路都闭着眼睛靠在座椅靠背上,看着像在睡觉,其实却不是。他莫名忆起多年前的一个场景,那是在英国,当年的何齐大约只有十四五岁,在学校里打一场曲棍球比赛。他离得很远,但脚底下是一个山坡,有点居高临下的意思,也能清楚地看见赛场上那场冲突。何齐被对方球员围堵,人家用球棍使绊,那一跤摔得不轻。队友们围上去就要开打,何齐也是气急,却还是把球棍扔了才冲上去。何齐,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可以说是看着何齐长大的,何齐会做什么,不会做什么,他不可能不知道。
他禁不住又想到另一个人。多年前的那一天,他并不是独自站在那个山坡上,陈康峪也在,还有陈效。
陈效,他在齿间轻念。
几个月之前,他们在法庭上又见过一面。律师不客气的发问,但陈效没有流露丝毫惧色,倒像是在观察坐在原告席和旁听席上的每一个人,看到他的样子,赖志成突然感到一丝不安。或许自己错了,赖Sir这样想。
一审判决下来,香港那边临时召集了所有董事开会。有人在会上叫嚣,一个上海公司算什么?明年就把子公司变分公司,看他还能怎么折腾!还有人在说,他陈效不是不要现钱要股份吗,不出三年,让他身无分文地滚蛋!
赖志成一向是极安静的人,那个时候,也没出出声,但心里未必不这么认为。
可是如果,只是说如果,陈效能在这件事里面折腾出什么花样来,那么倒真的是不容小觑了。
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前后三部车子驶出雨林道别墅,一辆往东,两辆往西,开出一段路,那两辆往西的也在一个路口分道扬镳。
王俊坐在其中一辆上,正打电话给陈效:“事情到了这份上,你现在出面,既没必要,也不合适。”
陈效在另一辆车上轻笑,王俊听他不说话,知道再多说也没用,他决定要做的事情,又有谁能拦得了呢?
跟进来的时候一样,林薇出警察局也出得十分突然。
给她送过饭之后,又过了几个小时,问询室的门开了,外面是一条走廊。有一面全是窗,午后的阳光照进来,让她睁不开眼睛,也看不清门外站的人是谁。
后来回想起那个时刻,林薇自己也觉得奇怪,竟然没有一丝的侥幸,以为事情已经结束了,第一反应便是林凛。林凛出事了。
“有车送你去医院,……你要是想自己过去也行……”说话的还是那个女警,语气似乎比半夜里要好一些,那意思就是她可以走了。
林薇知道自己没猜错,一下子站起来朝外走,脚却好像踩上棉花上,还没迈出几步,就差一点摔下去。女警去拉她,她一点力气都没有,碰到人家的手,才知道自己不停地在发抖。
刑警队的车子一路鸣笛开到医院,下了车一群人直接拥着她去外科病房,因是警方控制的嫌疑人,专门留了一个房间出来,门口站着两个值班警察。
跟林薇同车来的警察走上去问:“说什么没有?”
其中一个值班的摇摇头,回答:“手术做到半夜,完了之后就一直没醒过来,刚才突然就不行了,没抢救过来。”
林薇就是这么听到林凛的死讯的,轻描淡写一句话,其中就算有惋惜,也不是为了死去的那个人的。
她觉得意识一点点在抽离,任由别人叫她去做这个那个,而后又有一个医生出来跟她讲话,车祸?脾脏破裂?修补术后再次出血?每一个字她都听见了,却好像不能理解似的。
直到一个警察开了病房的门,让她进去,在她身后说:“十分钟,然后法医会过来。”
她看到病房里的推床,上面躺着一个人,身上盖着医院略显陈旧的白布。她蛮横地推开警察的手,没有一点感谢的意思,自己也觉得奇怪,仅在那一瞬,她突然想起一个不相干的人,以及他曾经对她说过的话,
“做坏人才难。”他这样对她说。
而她觉得愤怒,她并没有做过什么坏事,结果却是这样的。
十分钟,只有十分钟。她关上门,把布掀起来,伸手轻拂他的额发,一点一点看他的身体,脸上、腿上的瘀青,和腹部已经缝合的伤口。然后重新盖上布,站在床尾的角落,死一样的静。
不知道过了多久,一老一少两个护士进来收拾抢救车。
年轻的问:“怎么回事啊?”
老的答:“车祸,小孩儿才十几岁。”
“真作孽。”年轻的感叹。
老的鼻子出气:“楼下太平间躺着的那个呢?估计本来也没想要人家的命,捅的是屁股,谁知道那么巧,一刀扎在股动脉上,人送到医院心跳血压都没了。”
年轻的骇笑:“这手势,倒是做外科医生的材料。”
“你是见得少,”老的也叹气,“在医院待久了就知道了,越是年纪小的,越是狠。”
林薇在旁边听着,那两个人从进来到出去都没看见她,好像她也只剩一副魂灵。直到这个时候,她还是不敢相信,林凛杀了人,然后出车祸死了,成了一具苍白冰冷的尸体,躺在她面前的推床上。
这许多年,她一直有这样的怀疑,自己身上多少会一些地方像林燕青,每次做错事,总是反躬自省。最早的一次甚至可以追溯到小学一年级,当时的同桌最喜欢在她面前炫耀各种好看的文具,因为她除了老师给的绿色中华铅笔,什么都没有。一天放学,她留下来做值日生,发现同桌的卡通铅笔掉在地上,她没有出声,捡起来藏在袖子里,带出校门走了很远的路扔掉了。那件事,她记了很久,倒不是因为内疚,而是她暗自害怕,有一天那一半来自于母亲的基因会突然爆发出来,让她做出叫自己都骇然的坏事。
她一直以为是自己,却从没想过会是林凛。
她从没有想到过会是林凛。
林凛比她小五岁,在记忆的最远处,他只是一个软软的婴儿,经常哭得惊天动地满脸通红,老房子隔音差,有时候邻居会敲着墙壁骂,林燕青自然不会去管,难得清醒的时候便会出去勾搭男人,否则不是眼神呆滞地躺在床上,就是发疯一样到处找,至于找什么,那时尚且年幼的她还不怎么明白。她只好去哄他,有时候哄得好,有时候不行。傍晚,总是在傍晚,天渐渐黑下来,他莫名其妙地大哭,好像世界末日将临。她给他唱歌,抱着他轻轻地拍,恨起来也会打他,惹他哭得更凶。等他大一点,她会抱他出去玩,那时她自己也不过六七岁,邻居看到他们,就会说她像个小妈妈。
的确,林凛更像是她的孩子,而不是林燕青的。
但现在,他死了,躺在白布下面,单薄瘦弱,如一张青白色的纸。
十分钟,法医就来了。林薇走出病房,警察在外面等她,应该又有新的问题要问,但她一步踏出去,就整个人倒下去了。她觉得自己像是掉进了一个深洞,时间似乎失去了意义,往下再往下,很久很久,直到一双手托住她。
她隐约知道自己被抱到一张床上,不省人事,沉沉睡去,很快开始做梦。
好像又回到夏天,刮台风,家里的屋顶漏了,雨后初霁,何齐找了人来帮他们修房子。午后,他吻在她唇上,她闻到他身上的温暖清爽的味道。
我爱你,他对她说。
我不会原谅你,她却这样回答。
她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在做梦,却流连在里面,不舍得醒过来。直到有一只手放在她肩上,将她强拉回现实。她睁开眼睛,看到面前站着一个人,很久,她才认出来他是谁。
陈效坐在床边的椅子上,看着她说:“节哀。”
他声音沉静,就像他这个人,猜不透背后是什么意思。她又闭上眼睛,手机械性地拧着床边护栏上的插销,一圈又一圈。他什么会在这里出现?又和这里发生一切有什么关系?她全不关心,只想着一个人,林凛。一件事情,林凛死了。
“你知道何齐为什么来上海?”隔了一会儿,他又问,手搁在她肩上,不轻不重,只有些微的暖意隔着衣服透进来。
她摇头,然后才想起来,轻声道:“为了打官司。”
“是,”他点头,“遗产官司,我是原告,他是被告,你弟弟杀掉的是我这方面的证人。”
真是讽刺,直到这个时候,才知道何齐这么说是认真的。她睁开眼睛,突然把护栏上的插销拔出来,朝陈效扔过去。
他躲开了,抓住她的手,她背过身试图挣脱,歇斯底里地喊起来:“随便你们争什么,跟林凛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是他?干吗拖上他!”
他从身后抱住她,她动弹不得,低下头就去咬他的手,牙齿深陷进皮肉,几乎立刻就尝到血的味道。他却没有叫,只是一下把手抽回来。她以为他会放开自己,却没想到他整个人压下来,把她面朝下按倒在床上。她再没有力气挣扎。
病房的门是反锁着的,大约是动静太大,外头有人敲门,他回头比了一个手势,敲门声总算没了,但还是有人扒着门上的小窗口往里张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