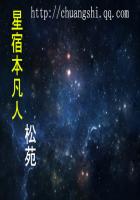“姐姐!”想得入神了,一声呼喊蓦地将她从自己的思绪中拽了回来。她讷讷问:“怎么了?”
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早就走歪路了。
岑九无语地一掌拍在自己的额头上:“走这边!”
司路默默地将她前进的道路更改为正确的,跟在岑九身后。这回脑海是一片澄明,她开始打量四周,明明灰暗的地下宫,在蜿蜒的回廊里却丝毫感觉不到黑暗。那光亮分明是夜明珠,她四下扫了扫,却没有发现夜明珠在哪里。
岑九走在前面,拐过最后一个弯,穿过月亮门,是一片漂亮的院子。司路一动不动地看着天空,原来,已经晚上了。那里,赫然挂着个月亮。花草树木,皆在这片院子里。空气非常棒,这片院子盛着一林子梅花,时节未到,想必盛放花朵之际,定美得不可方物。这院中还有几棵桔子盆栽,橙色的果子零零散散挂在上面,倒也别有一番风味。一条小溪不知从哪淌来竟穿过了这片院子。院中还有一座小小的拱桥,一派小桥流水的景象,勾起司路心中丝丝情谊来。
岑九走到院中央的房门前,敲了敲,道:“主子。”
里屋传来一声“嗯”,岑九得令,将司路推入门内,再退了出来,独自一人按来时路,退回了地央宫中。
房间非常大,不同司路住的那个小寝居,这里更宽敞,设备更齐全,并且,设计更美观。因为是建在地面上,所以所用之材皆是上等的红木。木门和纱窗也不是简单的雕纹,所成之物,皆栩栩如生。屏风两侧是甚司路也没去细看,宿印怀一人正坐在一盘棋局前,若有所思地捏着手里的黑棋。
“坐,与我对一局。”司路缓缓坐下,软垫也挺舒服。
此局虽已开始,但却被下成平局,她此时入局,竟也毫无不公平之言。
执一白子,观一棋局,司路稳当落子。宿印怀嘴角浅浅一笑,落定一黑子围了司路的棋。前者也毫不示弱,一子破了他一局。安静的院子里,除了二人落子的声音,就是呼吸声了。二者皆陷入棋局的思索里,一番明里暗里的较劲打得不可开交。一个时辰过去了,最后一子落定之后,落了个平局。宿印怀抬眼,眸中是难掩的欣赏,他果然没有看错人。
打得一番酣畅淋漓,宿印怀难得也高兴。将棋局放置身后,底下的茶杯露了出来。烫过热水,宿印怀倒了一杯热茶,推至司路跟前。
淡淡一语缓缓传出来:“我需要姑娘帮我一忙。”
司路抿了一口茶,面不改色:“我说过,我不会帮你。”
“这几日,我一直被一问,缠得难以安寝。总是在猜测,姑娘究竟对轻功有无兴趣。”
宿印怀戏谑忧愁的声音一落。司路的手就顿了一下,她一直忌惮的轻功?用一个忙,换轻功,这买卖,似乎不亏。
“什么忙?”司路放下茶,凝着宿印怀。
“不偷不抢不杀,到时你便知道。”宿印怀抬眸瞥了一眼司路尚不太利索的右臂,“但是,不论是你的外伤,还是内伤,皆未痊愈,所以在你的伤治好之前,我不会教你轻功。”
司路一惊,却又听他道:“明日辰时你与我一起出城。”
“去找一个人。”
司路不用问也知道了,那人,定是能治她病的高人。
“不是平常肺病么,城中大夫无法医治我的病?”
宿印怀不由低低一笑:“原本是,被九儿那丫头一整,就不是了。”忖了忖,他又道:“我无针对你之意,本就想他给你看病,除了他,我想这世间没人能短时间内根除你的病。”
“我知道了。”司路站起来:“至于你需要我帮的不偷不抢不杀的忙,说到做到!”
她说完推门走出了房间,月色清冷,她停住脚步。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今日正好十六。果然很大,很圆。再怎么说,在这世上虽是分隔两地,但至少看到的,还是同一个月球。福大命大,相信雷扬等人,必会平安无恙。
翌日辰时刚到,司路打开房门,迎面就见一人。一袭水蓝色俏皮长裙的岑九,笑嘻嘻地盯着她:“姐姐。”
“你在这里做什么?”
司路瞥见她肩上的包袱,抬眸问道:“你也去?”
她不好意思地笑笑,又略带歉意:“主子让我跟去照顾姐姐,姐姐的伤是我致使的,毒缠在肺部上不肯出来,又只有我能抑制毒素,所以我要跟着姐姐直到找到我师兄。”
“那走吧。”
“等等,姐姐。”岑九从包袱中拿出一块黑布,坦然道,“姐姐,请闭上眼睛。”
这把戏让她想起她遇到黑衣人那夜。她缓缓闭上眼,黑布蒙在脸上,与那时有同样的感觉。岑九确定司路什么都看不见了,才带着司路横穿地央宫。
司路的确就算睁开眼也什么都看不见,她也没打算睁开眼。看不见,可是她其他所有感官并未消失——她一共右拐了十二个,左拐七个弯,穿过三道门,爬了二层楼梯,最后一声“嘎吱”。
她听到一声“主子”,随后她眼上的黑布被解了下来。
一辆精致的马车出现在她眼前,制作马车的材料皆为上等,雕刻的手法也是细致入微,能有这等手笔的人,除了皇帝,无外三种。王室,高官,富商。
她看了看四周,这是大街,眼角瞥见一尊石像。她转过头,身后是一扇敞开的红色大门,大门上方,是豪迈的两个大字:宿府。
——“这个世上,除了国师宿印怀,没有人能揣摩出当今陛下的心思。”
司路盯着后面那个气质非凡的男子,心中默念:宿印怀。
司路看着宿印怀钻进马车,旁边的岑九推了推她:“姐姐,上去吧。”
后者点头,走上前去,却瞥见马车前头坐着张熟悉的脸。武诚面无表情地朝她点了点头。司路也没有说话,在岑九的掺扶下上了马车。马车内很是宽敞,左右两旁长椅上放了一排同样长的软垫,后方则置了一张软榻,宿印怀正躺在上面假寐。司路在宿印怀躺着头的那边坐下,屁股一沾座,马车就徐徐动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