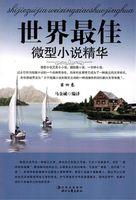刘江国父亲在世时,让他在私立学校里念了几个春冬。由于他好读,心灵,还算是有点文化。他像他父亲,个子高,但不像父亲风趣,诙谐,幽默。他胆小又刚烈,虽很懂理,讲理,却爱钻死理,常常为一句话与对方争得面红耳赤,为一件小事,常常会造成大的裂痕,他就是这种脾气性格。
他父亲牺牲后,他过早地担上了管事的沉重担子。攒牛,放羊,种地……是那么苦,那么累,他认为没有苦与累就没有事业的成功,也没有安居乐业。人常说,男儿“十七多负之”,女儿“十七领家之”。江国可为一个好男儿,村里人都夸他是个好孩子。兰兰回家闭口没说生虎好色,邪恶欲望那事儿。但不知江国怎知道了,他很生气,他说一定放不过那小子。
中午,江国正好在三进院的大门外遇着了生虎。就气忿地要还他的礼了,“你与我妹说啥呢?”说着快步赶到他面前狠狠地瞅着他,要欲欲动手。他害怕了,像条认输的狗,既汪汪又后退。两眼惊恐地瞄着他。江国逼近他的面前“啪啪”!给了他几个耳光,生虎既吃惊又害怕,他觉得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打耳光是那样的疼痛;江国是那样的厉害;自己是那样的胆怯和那样的懦弱。他就忙伸出两手紧紧地捂着自己挨了揍的,火辣般的脸颊,呜呜地哭了起来。他一边哭,一边愉愉瞅着江国,怕他再给“啪啪”起来,——“啪啪”这种响声太可怕又难受,因而他是那样地心惊胆战。而江国更逼近一步唬他说:“你当流氓啵?”
他像个耍猴人鞭下的猴子,瞅着鞭惊惶地又是退,又是躲,但也被迫着扭起来——他那尖、软、丑、恶的原形毕露了。他妈王氏耳听大门外吵吵嚷嚷,就忙跑来,她没问双方为啥不为啥,因为她知道儿子的坏,也知道江国是个好小伙子,和言悦色地与江国赔情道歉。她和言蔼语地对他说:“江国,你别生气,也别打他啦,没用。他呀经常做赖事的,是会有人收拾他的,只是时间不到哩。
“我那两个赖气的活宝贝儿子,又把他老子的鞋穿上啦。我知道——哪有个母亲不知儿子的好坏呢?要说不知那是屁话。唉,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不好儿?”她说着,气忿地把儿子用拳头一撞一撞地滚回大门里去,咬牙切齿,气呼呼地返回自己的院里。
“我我我有啥办法呢?唉唉唉,养了人,养不了心……”她回头又对江国说:“看在大婶的面子上,饶了他吧。走着瞧,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报是时辰不到。看他的后戏吧,恶人总有恶人魔,砒信毒还有吃砒信的虫哩。他兄弟们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气死我啦。”
她走了几步,又返回来说:“他呀,迟与早不说不会有好结果。别看我是个女性,我清楚地认识到了。谁都清楚,江国,你是个有出息的孩子,好娃娃,将来要成大器呢。”
“我那两个不成器的赖儿,若不趁早改邪归正,会要吃大亏呢。不信,你们走着瞧。”王氏自言自语说。生虎不言语,而生龙嘟哝着说他母亲是个泼妇,怪他不该“家丑外扬”,不该对着江国和众多的看客,把亲生的儿子挖苦成不人不鬼的,就气忿地冲她说:“妈,您不是常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钻孔洞。’要说儿子赖,根儿就在娘身上。”他说完恨恨地瞅着她。他妈被他顶得干气而无言。
养儿知性情,王氏清楚:“大儿尽管是走邪路做赖事的人,但他话少,不嘴伤人。生龙呢,是个多嘴,脏嘴,也像个疯子的嘴,啥难听的话——不该说的话他也能说出来。”她说:“妈的乖乖,生龙,是妈的不好。”然而她又一反口说:“你你你啥话也能说出来,啥事儿也可做出来呢!”她竟流泪了,身子也抖动起来。“妈!哥做赖事,您为甚找我的麻烦?”生龙反问。母亲说:“他做赖事我管教,你为啥偏理庇护,又没理的强辩?说呀!给当妈的讲清楚好吧?”
“您为甚家丑外扬?”生龙强辩。
“生龙的话我赞成!”生虎说。
他妈冷笑了,她放低声音说:“唉,完啦,一个比一个坏。要说家丑不得外扬,固然是人们传下来的名言:但我总认为人家是指家里人与人之间的生活琐事而言;你们是在外边做了坏事,要封我的嘴行吗?那岂不是‘掩耳盗铃’?就算是家里的坏事儿,只要做了,是会让人们知道的。棉花能包住火吗?荒唐!自己错了,不认错,强词夺理,无耻地侥辩行吗?”
生虎无言以对,但他满腹的情绪。母亲的反复论述与指责,他实感不满和反对,只是装在肚里忍在其中。但他今儿破例地反驳他母亲了。他怕挨打,预先把距离拉开,离母亲老远。他说:“什么道呀,理呀,谁爱听呢!哪有这些看不着,摸不见的东西呢?‘理’,‘理’,讲‘理’没了钱啦,谁愿讲它?有钱有势就是有理的。假如你没钱的话,有理顶屁用?软弱无能的您成天开口闭口不是怕这便怕那,有啥可怕的?都怕死谁做鬼呢?”
他妈更气了,因为她是个知理讲理论道的人,是个以理服人的人。气破肚的大儿竟说出如此偏道不理蛮横的话儿,使她生大气了:他不仅脸部变得通红,而她的眼也被气红了。她说:“呀!苍天呀!”她高声地叫起来,眼泪也被气冲出来,她的额头渗出了丝丝的汗潮,就使劲地拍起手来,说:“我的天呀,完啦!这人家的好光景过够啦,非倒霉不可。万贯家产眼看要毁于眼前。”她说完,坐在大门口放声地哭着哭着。
李小狗去世家里乱了。王氏以为乱的原因是没养下好儿子。好儿一好百好,一顺百顺。赖儿呢?儿子大了光景完了。尽管王氏苦口佛心去教育。还是成天嚷哄闹腾搞舌战,其结果是枉费了心,白磨了牙。因此,她成天忧愁而坐卧不安。她想:“为什么姓李的富豪老没老、少没少,一代不如一代呢?先兆不好,前景渺茫。俗话说:‘发财有个法,倒霉有个根’,怎么办呢?”她又想:“莫非是鬼怪在作崇?”于是她推门跑到吴长梅家去,要仙家救救李家。
她一进门,生虎不知啥时溜来,正与长梅……生虎见母亲进来,慌里慌张地不知所措,忙低头溜了去。
王氏怒色于面,全身的筋骨咯吧咯吧地响,一股麻麻的难说的滋味从骨头缝弥漫出来。她坠入了昏昏沉沉的状态之中。唉,奶毛没褪就大吃大喝,横嫖聚赌起来。长梅连忙拉起退在脚腕的裤子,脸儿忽红忽白傻兮兮地龇了龇嘴,像要说什么,但没有说什么,只是嗫嚅着把要说的话又咽了回去。很不好意思的迟疑着搭讪说:“婶子有事吗?”她说完忙把羞臊而堆满红云的脸转去。因为男女之间的床事,是明事暗做哩,何况是不正当的流氓勾当呢?“有啥事尽管说出来呀,只要我力所能及的,毫不推辞。王氏既觉得难堪又不好意思——儿子竟……此难言而烦人肺腑的赖事,也恨她长期勾引野男人养汉寻欢不是正经味道,不是正经妇道。但为了求她办事,就只能装出一付嘻皮笑脸的模样来,她竟搭讪着说:“唉,其实——也难说,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来祈祷神灵啦,愿仙家保佑李家人平安,家财不流失。”
糊涂蛋一听有人求神拜卦,不知他从哪里钻出来,忙跪在仙家牌位前烧了八张纸,点燃八柱香,磕了八个响头。装腔作势地念念有词,不是什么“显灵”,就是没完没了的“保佑”。
长梅见丈夫一切安顿停当,就地辅了垫子,坐在牌位前,调正了神态唱呐道:
小财由人,
大财命定。
穷人返富,
富翁要堕。
顺天者兴,
逆天者亡!
她唱呐完了,就慢慢地睁开了眼整了整精神,定了定气,说:“大婶呀,尘世上人人谋胜不谋败,可呀,天意不从人心。人家的成败,光景的好坏,是天数,不由人也。孩子长大不由娘管,他爱咋就咋。爱吃苦的是一辈子;爱享乐的也是一辈子。”她画了神符递给王氏说:“此件贴在堂中,可迎神驱鬼。”还让她在张贴时,嘴里默念“太公在此,诸神退位。”如看着或听着理解不了的或自以为是鬼怪的,就默念“见怪不怪,其怪自败。”
糊涂蛋说:“是灵的,你家从此以后就一顺百顺,平平安安,百事大吉了。可怜小人供俸神仙辛苦,多给些圆的……”
王氏有钱,而她素有施舍的美德,他要用钱换取灵神的诚意,就毫不吝啬地从衣袋里“哗哗”抓出几把银洋,放在仙家牌位前,以示真心舍财而求灵。
“多谢!多谢!”糊涂蛋哈哈一笑,收拾了银洋。
王氏捧着黄纸写着朱字的神符谶语,如获至宝地要回家去。在回家的路上,只见小叶手里拿着本书,在分河上边拾柴枝、草叶。人常说,一个人的性格是天生一半,学一半。小叶克勤,克俭的独特性格,除了天生一半,另一半是从艰难困苦的生活中磨炼出来的。他所经历的那种艰难生活日常了,也就习惯了,就是自己生活所遵循的做法和追求。
他五分钱买支沾水笔尖,已磨去半截还在使用着;八分钱买张板纸,他写完正面写背面;三角多钱买瓶墨水,加水一半(变了质)也要使用半年。有时以水当墨,以指为笔,书桌当石板,板石头当纸来做作业。
晚上他俩面对着食油灯自习,书桌上搁碗生水,把桌子擦得光溜光,把应写的语文、数学作业全做完。看起来像是没做作业——要说做,本子在哪里呢?他的回答是:“在肚里。”
“半夜啦,你们忘了睡觉!”奶奶醒了,爬起来从窗口眺望了天色,说:“过了今日没了明日吗?熬病啦。”
他俩看了看奶,应付地嗯上声,表示要听从她的指教。但是谁知他们只应承而不去休息。那种爱学、狠学的精神,使他们越学越想学,兄弟俩,只有学会,心里才踏实。
奶奶又睡醒了,他俩还在学习着。她气了,爬起来一撅嘴把灯吹灭了。但兄弟俩还在低声叨叨着。奶仄耳听了听,拿起笤帚要打他们了,说:“灰孙子们!你们长着月眼吗?”
他俩无声无息的睡了,奶奶却还在生着气数落他俩,说:“难说呀,你们把学习文化看成命啦,整夜不睡觉,身子骨受得了吗?哪家的孩子鸡叫还在读?一夜就可种个状元吗?心急有用吗?唉,唉,你们把身子骨累垮后悔也迟啦!”她听着他俩睡着了才不说教了。
尽管佳事难出名,然而小枝兄弟刻苦求学的精神却成了村里人们茶前饭后的口头阐了。郝秀才说:“寄蜉蝣于大地,渺沧海之一粒”。人生于世尽管短暂,而小枝兄弟与时间赛跑,岂不是很有价值的人吗?
小叶从学校回来,一进门放下书包就看自家的柴垛子,面缸子,水罈罈。他见没水了,就用大罐子一罐罐地提了回来。他见粮少了,就要奶奶少做少吃。他为日常用的柴、米、油、盐常挂在心上去思量,去发愁。他认为穷光景只靠哥一人来维持是不行的。他认为他不是自己的绝对依靠者,而他也没有那个能力。
盛夏的响午,蓝蓝的穹空挂着轮炎热的火球。人们躲在家乘凉,有的还摇把扇子也止不住无情的汗水淌流。然而谁知不怕苦的小叶瞒着奶奶,独自一人爬上了铁架山去刨小药材。他傲视火爆爆的夏天,高温烤着小叶汗水直流。他上了铁架山的山峰,退下了山腰,爬上了山崖,一根根地刨着什么的蓁艽、柴胡。捡去头尾,扯掉了层层老皮。刚刨了几把。忽然倾盆大雨直泻,铁架山平地起水。他的下落谁都说不清,因为是午休时间,小枝见弟不在家,才知道是刨药材去。他冒着大雨跑了出去寻找小叶。他自言自语说:“我的弟呀,你在哪里……”
奶奶急得坐卧不安,满地打起转转来。转着,转着,就跑在地上求天神、地神、雨神保佑她的小孙子。一会儿发疯似的出了院,向着叶子常去的铁架山方向望着,叫着,哭着。她那干瘦枯黄的脸颊,涨得通红,高声地嘟哝起来,顿着小脚吼叫起来。她仿佛那山里发回的音是叶子在回答——是奶的愿望。
奶奶气了——她生叶子的气,她说他性子倔强不听话,也批评他不怕死——真的,幼年的他在已死而未死中多次挣扎而生。一会儿小枝把他背了回来。他说叶子差点儿被洪水冲跑。他的身上糊满了泥,裤子被石块捣破了许多破绽和孔洞,还扯去几片。他哭着哭着……奶奶心痛地安慰他,也批评他。他说:“奶,我的裤子不能穿了,呜——!”他哭了。
奶奶抓着他,问他被洪水冲到那儿?为啥不言语?一边给他脱去了泥衣,一边在他屁股上打,让他尝苦头再不干。她要给他穿新裤,可是他要拒绝奶奶的好意,硬要奶奶洗去泥巴,补好还要穿哩。
小叶生来不爱穿新衣而爱穿旧衣。他有“敝帚自珍”的个性。因他不穿新做的衣服,家里出现了小小的故事风波。
他上学读书,奶奶给他做了身进口时髦的海冒蓝衣服。奶奶多次让他穿,可被他谢绝了。奶奶恳求着他说:“衣服做起几年啦,衣服不长,可人长哩,眼看就不能穿了。”说着就帮他穿新衣。却被他执著的性格拒绝了。“我不爱穿一身新呀,太碍眼了。我爱穿旧衣。旧衣穿上不碍眼,自然随意,舒服。”小叶低着头又无意地扳弄着手指的指甲。“依了我吧,奶。”他也恳求着奶奶。
“学校里数你的衣服破哩,你不怕同学们笑话?”奶指着他说,“你光记住个‘旧’字,新衣服不穿,旧衣服从哪里来呢?”他说:“旧不等于‘破’和‘脏’,老师说,‘笑脏不笑破呢’。他又说,‘穷光景难过,挣不回钱来,节省下来的也等于挣回来的。’‘新三年,旧三年,补补缝缝又三年’。老师说得多好。咱没钱呀……”他还是低头扳弄着指甲。
“他倔强,您比他还倔强!”兰兰说,“性格是生的,难改。您跟他吵有用吗?叶子的脾性您是知道的,是吧?”奶听了兰兰的话,没做声,她似乎也同意小叶的意见,说:“小叶不是不穿新衣,他是说,他的衣服还不算太破的,还可穿。新衣是在洗,补旧衣服时暂穿;出门作客,过年过节时穿;旧衣服实在破得不可穿了,最好是一件新,一件旧,穿着全新一身,他觉得不但碍眼,而是连步也迈不开。总觉得背后有人说三道四。”
小枝放下手中的书,从奶的衣包里取出小叶的新衣服,摔在他的面前,指着他,忍着性儿以好话说服,不从;就逼他说:“你穿不穿?今儿就让你穿!你好穿也好,赖穿也好,总之穿上为止。”
小叶见他哥发火了,自己就越把头低了下去,无声无息地掉着泪珠儿,不顶不撞他哥,沉默不语,伸出两只小手把泪水在脸上抹来抹去,看样子他的倔劲儿越来越倔。然而他没敢动。他那软而绵的性格像只弹簧,硬中软而软中硬。总之,他不干的就是不干。
兰兰看火了,拉了小枝把,意思是要小枝别硬逼他,因为人家懂事了,不与往年一样了。“由他吧,他爱啥,就穿啥。生那闲气有用吗?你能把他性子扭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