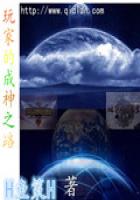一夜狂风,不曾停歇。怒吼声几乎将挂在夜幕之上的星辰吹落。无助的木枝,在风中无力的摇晃,终于被咆哮的狂风吹折,荡在空中,是那般的惹人怜惜;散落一地的碎花瓣,在浅草间,无奈的翻滚摇戈,凋残的花骨朵,遥遥在望;散落在草间的花香之气,已经没有的欢愉之情,偶尔才会爬上窗沿,溜进屋中,却也早已失去原来的那不忍不闻的花香,此时,终究还是夹着一缕浅浅的腐败之味。却也不知是残花之味,还是草间的腐味···
仿佛空气之中,随处便是如此之味,想要逃开这样的味道,却寻不到一个那样的地方——可以暂躲一时的地方。
袅袅的青烟,笔直而上,在云端嬉戏,俯瞰着这一座千年古城,望着被狂风折磨一夜,此时依然留着昨夜的痕迹的街景。
幸好,行走在街道之上的行人,无几人关心。只有寥寥十几个轿夫在嘴中抱怨着;而轿上之人,偶尔还会牵动轿帘,将目光探出窗外,搜寻一丝惊奇,望望那些倒在街角之上的可怜之人。嘴角便会荡出一丝哀叹可怜之意,就连眼角处,亦是如此神情。只是他们的感情,也只是现在此处,绝不会压下轿子,伸出温暖的手去帮助他们——那些可怜之人。
每当轿帘牵起,路边的小贩瞧到探出窗外的那一双目光,总是会将自己的声音再提高些许——几乎是用尽身上全部的气力嘶吼而出,那声音,即使是一个常年的聋子,亦会有所感觉。如此的吼声,总是会将轿上的人的目光吸引。即便是稍微的停留,他们亦会有一丝机会,心中便会有一丝希望。更何况此时,已经有一人缓步而出,停在眼前。
见到那人一身的绫罗绸缎,小贩的眼睛闪出了炙热的光芒。只是这一道炙热的光芒,瞬间变的有些怨毒,冷冷的望着倚在墙角的一老一少身上。年迈的老人,面上满是岁月的苍桑,还有岁月的挣扎与煎熬;一双本该是童真无邪的眼睛,此时却也满是痛苦之色,寻不到这个年纪的一丝欢愉,只有数不尽的伤痛之情。
李慕崎解下自己的袍子,轻轻的将它披在小女孩单薄瘦弱的身子之上。见到李慕崎如此,小女孩眼中不仅没有谢意,却出现恐惧,慌乱无助的躲避,想要避开李慕崎那温暖的眼光,瘦弱的身子,此时已在老人的怀中瑟瑟的抖动;老人见到李慕崎如此举动,眼中亦在闪动不安的目光。良久,见到李慕崎目光是那般澄清,并未感到一丝恶意,老人的嘴角方才稍缓,露出一丝笑意,昏暗的眼中露出点点歉意,满是褶皱仿如树皮的手掌,轻抚着女孩的脊背,安抚着她不安的心绪。
不用过多的言语,李慕崎已经能够想象她们经历过怎样的煎熬,经历过怎样的苦难,经历过怎样的日子。世上,总是不乏口是心非之人,打着做好事的幌子,做着无耻之事——令人难以,不敢想象之事。
李慕崎回身在轿夫耳边低声交代几句,从身上解下一块美玉,交给那一位满眼感激之情的老人手中。老人的手中捧着李慕崎送与她的美玉,拉着自己的外孙女,想要施一大礼。却被李慕崎双手搀起,温柔的目光望着这一对婆孙,轻声道着莫要感谢之言。
见到轿夫抬着骄子远去,李慕崎方才与李安桐转身离去。一声极低的声响在背后响起“世上居然还会有如此的傻子,奇怪奇怪。”小贩不断的摇着头,叹息着,却也在埋怨着李慕崎为何不将那一份“傻劲”留给他···
此时早已过了上早朝的时辰,李慕崎有意耽搁,便是想错过那个时辰,他不愿在那里耗费自己的时光。只因那里只有无数的心机,却没有一丝一毫的真情——真正为百姓谋福之情。
寥寥几天,京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并不是京城之景,那里的景致,仿佛不会有四季之分,永远的少了一分美丽——自然之美。这变化,主要还是说人,人的变化。这些事,已经在百姓的口中传诵。他们的描述是那样的透彻清晰,仿佛就发生在眼前一般。不知他们究竟怎么学会如此的言语,哪里学来的如此口才。
李慕华的婚事已定,年终之时,便是他的大婚之日,如今已有太多的人在为他准备此事,操劳此事,也有人因此在不断的挨骂受讽。最令人意外的便是韩馥,居然会在此时封为郡王。此时说来奇怪,却也不是特别的奇怪。母以子贵,父以女显,韩府二小姐韩诗翎,就在李慕崎离开的第三日,便被李书衡由才人封为贵妃,而贵妃与皇后只有一步之遥;而这一步于韩诗翎实在太近,就在第二日其父亦被李书衡封为郡王。至于张政纲所求之事,李书衡并未出面,已被韩馥婉拒,毕竟此时的韩馥不愿违李书衡之意。
日照斜斜,几乎没过肩背,立于头顶。而此时,李慕崎刚好来到皇城脚下,李书衡正在咆哮朝堂,面上浮着一层冷冷的怒色,望着朝下文武。厉声道“难道除去这些琐碎之事,列位便无其他之事所奏?”众官面面相觑,实则在等待某一人的点头,又或是某一人的眼色。如此过了良久,李书衡依旧不见有人言语,怒气瞬间流遍整个面容,度着碎步,细瞧着朝下文武,瞧着他们的面色。心中已经明白有几人已经知道此事,此时如此踌躇,只不过是在等待,等待他人的首肯。见到此景,心中俱怒,突然用力的将手中的奏折甩出,狠狠的砸在一文臣官服之上。那人一惊,慌忙跪倒,刚好瞧到上面所书之事。
这上面所书之事,他并非不知,只是不愿将此事第一个提起。
李书衡是昨夜褪下衣衫,即将睡下之时,一道八百里加急的折子,慌忙送到内宫,由传礼监交于李书衡近身内监。见到那个匆忙有些慌乱的太监,他刚要出言责备,见到那个太监手中之物,慌忙接过,不敢停留,亦不等通报,匆匆走进,将此物交给李书衡。
见到此物,隶属衡的睡意瞬间消失,翻阅良久,将此物重重的摔于桌上,在殿中徘徊许久,终究难下决断。恰在此时,东方微白,有一缕光明在那一片黑暗之中努力挣扎。
李书衡忍耐着将文武所奏的那些无关紧要之事听完,却不见他们提及此事,心中不觉浮起一股怒气;细瞧他们的面容,怒气大增。
众文武将李书衡摔下的奏折仔细翻阅完毕,朝下依旧无人出言。
李书衡望着朝下武将,怒道“难道如此被他方欺凌,竟无一人生气,竟然无一人为朕分忧,为朕解决此事?”瞪着武将,厉声道“你们的勇气何在?你们的怒气何在?”
武将唯唯诺诺,无人出言。有几位年轻的将领,刚要移步开口,却被眼神制止。
恰在此时,司马长明向前一步,躬身一礼出口道“此事已发生,此时不可轻动。”
“那依丞相之意,朕将若何?”
“依老臣之见,”司马长明道“绝不可开战,只可与之求和。战则会败,求和则安,以保数万黎民免受战争之苦,分离之痛。”
“求和?”李书衡的面上不禁浮起一层怒容,厉声道“还未战,便求和,你叫朕如何面对先祖,如何面对先皇,又将如何数万兵士?”
“若是一战,恐为难胜,求和才能保土,卫民。”
“卿等俱是此意?”李书衡环视着一众文武,厉声道。
此时,朝下文武纷纷言语,武将有言战者,细细望去,是一些立于朝尾之将,只有些许的微薄寸功,想要凭此大显身手;沿河武将,大多是一些年老之人,不愿失去此刻的地位,更加不愿失去身上那些不知是因侥幸而得来的功劳,还是凭借自己的言辞诳来的功劳。文臣中言战者,几乎全是一些有着满腔怒火,不懂兵事的新进之人;而求和者,几乎全是司马长明羽翼下之人。
“若是先皇在位,尔等亦是如此之意?”李书衡听着众人言语,怒视着司马长明喝道。“尔敢劝说先皇如此?”
“若是先皇在位,只怕边境诸部落亦不敢如此放肆,怎敢犯我边境,又怎会发生如此之事?”司马长明挺胸,望着李书衡轻笑道。“他们如今敢如此,只怕···”
“难道是你认为,是朕无能,才会如此?”李书衡的眼中已然没有了怒火,冷冷的瞧着司马长明,冷笑道“依丞相之见,何人可堪朕位,方能立威于边疆,叫边境部族,不敢犯我之境?”
“老臣绝非有此意,”司马长明面上并未露出惊恐之意,依旧轻笑道,“换做他人,不见得有陛下的才能,将百姓带入如此境地···”
“你···”李书衡的面上不觉浮起一层怒容,怒道。不过这一道怒容,片刻既逝,面上又浮起一丝笑意,望着司马长明,冷冷道“丞相之言,朕自会思量。”目光一转,望着张政纲,道“不知卿等还有其他妙策否?”
张政纲见到李书衡投来的目光,缓缓低下头,不愿与他对视。见到张政纲如此,李书衡心下巨震,不觉一惊,思道;难道自己的那一个决定,已经将他与张政纲的距离拉到了危险的边缘?
恰在此时,张政纲挺身而出,望着司马长明道“司马丞相之言,老夫甚觉不妥。还未战,便求和,此事不仅是在辱没先皇,亦在侮辱陛下;况且,还未战,即求和,还想请问司马丞相,打算已何代价求和?”冷冷的望着司马长明,冷笑道“司马丞相如此作为,难道暗通他人,许下什么承若?”
听到张政纲如此言语,司马长明面上浮起一层怒意,与张政纲舌战在一块。
见到如此情景,李书衡心下稍安;他们如此争论,定会得出一个结果,一个他想要的结果;即使他们二人不会给他那个结果,他亦能够在他们的言语中寻到一个关键,将自己的意愿加入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