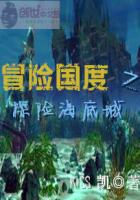最后的一缕余晖终究还是被那一座大山所遮挡,烧的通红的云朵仍在山前徘徊,久久不肯离去。似是在与夕阳道别,述说着一路的风景与不舍;又似是在作最后的挽留。无情的风吹来,拖着那一朵红云,撕扯着它,拍打着它。终于,将它撕成几段,又被远远的拖去。
风,很是无情,那人呢?人,岂不是最无情。
就在距离那家官栈还有五里之处,屹立着一家客栈,门窗尚未紧锁,风吹过,激起一阵空谷的回声,还有门窗拍打的响声。一只通体黑色的乌鸦正站在一株枯木之上,望着被风击碎的红云,发出阵阵哀鸣。猛然间,振翅而起,望着红云而去。哀鸣之声,在空中留恋,回荡,久久不散。又伴着呼呼风声、门窗叩打之声,显得更加的凄凉···
李安桐所骑之马稳稳地地停在客站门口,飞身而下。站在那一株枯木之下,抬起头,望着门前的匾额“天香居”。匾上的漆几乎完全掉落,露着木色的底面,满是斑驳与裂痕,似乎经过许多岁月。经历过无数的风雨。屋内的座椅之上,布着厚厚的一层土,桌上的杯碗餐筷依旧整齐的摆在上面,只有两张桌子的杯碗不是如此,不知因何故,被击的粉碎,片片残片,零星的散落在桌旁。屋顶有一个大窟窿,可以望见点点星光。借着星光,望着幽黑的过道走廊,心中莫名的有一丝恐惧浮现。耳边响着呼呼的、在黑暗处盘旋的风声,听来仿佛是地狱恶魔的呢喃。饶是李安桐,心中也有些不安。脑海莫名的闪现着许多幻像,越是压抑,越是清晰。李安桐不敢在此停留,即使他的心中没有恐惧,但是他此时的思想已经有些恐惧。人,恐惧的并不是事物的本身,而是对事物的想象;害怕的并不是事物,而是思想,只有思想才最是可怕。
李安桐拨转马头,急加一鞭,健马吃痛,四蹄疾飞,追上行在前方不远处,缓缓而走的马车。见到李安桐追来,杜如康也加了一鞭,望着官栈疾驰而来。
白色的灯笼,书着大大的墨色“官衙”的字样。灯罩之内的火光,猛烈地跳动,愈跳愈快,几乎将灯罩点燃;灯影也随之跳动,随着夜风晃动,打转。
健马一声轻嘶,稳稳地停在四盏明灯交汇之处。明亮的灯火将健马的影子拉的长长的,而且不住的晃动。拉长影子一直蔓延在黑暗之中,亦消失在黑暗中。
杜如康跳下马车,慢跑到门前,轻轻的叩打着门环。李安桐也已跳下马背,站在马车之旁,如炬的明眸,环视着四周。
金环叩门之声在夜风中回荡,久久才听到一声不耐的人声。厚门吱呀一声打开一条只容半人出入的缝隙,探出一颗圆圆的脑袋,向外张望,恰好望到杜如康笑眯眯的脸。
杜如康见到这张圆脸,急忙躬身一礼道“打扰几位官爷用膳,实是抱歉之极,还望您莫要怪罪。”然后又是一礼,从怀中拿出一锭银子,放入圆脸衙差的手中。衙差将手中的银子轻轻的跌了跌,忙收入怀中,圆脸之上浮起一抹笑容,道“无妨无妨。”斜眼上下打量了杜如康许久,方道“你们可是想在此处留宿?”
“正是,”杜如康点头道。又是一礼道“还望官爷能够应允。”
“嗯···这个···”圆脸衙差面上现出一丝为难之色,迟迟不答应。杜如康见到他如此表情,又从怀中拿出一锭银子,放到圆脸衙差手中。见到这一锭银子,圆脸衙差边将银子收入怀中,边道“这个我也做不了主,你们且稍等,我去通报一声。”
“如此便有劳官爷了。”杜如康又施一礼道,心中属实将那个圆脸的衙差狠狠的骂了一通:如此贪心,怎可为官。若天下之官皆是如此,只怕真是百姓之哀,百姓之苦。
杜如康站在门边静静的等待着他的回应,透过门缝,便见到一片灯火通明之处,灯火之下,是一片正推杯换盏的人影。欢快的人声,透过窗纸,清晰的传到耳中。还未到时,杜如康已经远远的瞧见那一片憧憧人影,只是未曾听到人声。此刻虽已听到人声,却又觉得还不如未听到时的那种心情。屋内的,又岂能称之为人声,简直是动物的嚎叫,而且定是最低贱的动物的嚎叫声。人,岂会发出那般污秽之言。
大约过了半盏差的功夫,那位圆脸的衙差映着一位瘦高之人缓缓而来。一路之上,圆脸衙差不住的点着头哈着腰,猥琐的笑着。那位瘦高的衙差,左摇右晃,前进三步,倒退一步,大约百十米的路程,他如此行进了约有一炷香的功夫,方走到门口。杜如康却也只能干望着,不敢催促。
“到了吗?怎么感觉走了这么远,你小子不会是故意带错路吧。”瘦高衙差打着酒嗝,询问着。“奶奶的,一会儿回去,老子定让那几个龟孙爬着回去。奶奶的,门口是什么人啊?”
“到了到了,”圆脸衙差扶着瘦高衙差忙答道,用另一只手将门又拉出原来那半人的缝隙,虚指着杜如康道“大人,您看,就是他们。”
“哦?”瘦高之人眯着醉眼,上上下下的打量着杜如康,猛然泛起一股酒意,结结实实的打了一个酒嗝,一股浓烈的酒味,迎面扑来。杜如康不能躲闪,只能任由那股带着酸苦之味的酒气扑在自己的面上,随着呼吸进入肚中。那股怪味刚刚进入,杜如康的胃,就开始轻微的蠕动,收缩。若不是杜如康强行忍耐,只怕此时已经跑到树下,将胃中的食物全部的吐出来。瘦高的衙差见杜如康施了一礼,刚抬起头,望着杜如康的面容,仔细的又瞧了瞧,才道“你··你们想··想要投宿··是··是吗?”伴着酒嗝,终于将言语说完。扶着他的那一位圆脸的衙差,想必也受不了那一股浓烈的怪味,将头别在一边,额上满是细汗,脸色煞白,右手用力地托着瘦高衙差斜靠过来的身体。
幸好,他的身体不是太重,不然此时,只怕已经重重的摔在地上。
“我们是路过的客商,”杜如康拱手道,“只因附近并无一家客栈,因此想在贵地借宿一晚。”
“咯···”瘦高之人长长打了一个酒嗝,眉宇间露出舒爽之色,苍白的面色有了一股血色,张着朦胧的醉眼,又仔仔细细、上上下下打量杜如康许久,方道“做什么生意?”
“倒卖粮食,”杜如康回道。
瘦高之人冷冷哼了一声,不屑的道“又是一**商。”然后又望着李安桐与马车瞧了瞧,道“车上是什么人?”
“是我们东家。”
“出来让我瞧瞧,”那人摇摇晃晃的望着马车行进。圆脸衙差小声提醒道“大人,小心,最近听说有强盗在这一带出没。”瘦高之人面上浮起一丝不悦之色,厉声道“量一群无胆草寇之人,有何可惧?况且他们只是商贩。”
李安桐已听到瘦高之人的言语,又望到杜如康投过来的眼神,心中微一思考,便将车门打开。恰在此时李慕崎与洛秋河正打起车帘,慢慢的走出。站在车上望着瘦高之人,拱手一礼。穆荷也慢慢的将头探了出来,闻到一股浓郁的酒气,以及那一股怪味,赶忙又将头缩了回去。
“就这么几个人吗?”瘦高衙差大呼道,“车中还有没有其他之人?”
“没有了,”李安桐道“只有我们家少爷,还有他的随身婢女。”
“那这个老头是谁?”瘦高之人虚指着洛秋河道“他是什么人?”
“他?”李安桐顺着瘦高之人所指的方向望去,见指的是洛秋河方道“哦。这位是我家少爷请的大夫,他最近身体不好,需要调理。”
瘦高衙差又是冷冷一哼,道“你们这些富贵之人,总是容易得病。不懂得节制,只是一味的纵情于酒色之间,能不得病吗?”瘦高之人朦胧的醉眼已望到了穆荷,拉长自己的脖子,想再瞧一瞧她的容颜,不想穆荷钻到车厢之中,不再探头,心中十分的失望,却也不能明言,又听到李安桐的言语,心中猥琐的想想了一会儿,冷冷哼了一声。
“大人说的是,”李慕崎拱手道“日后定会注意。”
“我这里是官栈,按理说是不能留宿如你们一般的外来之人。”瘦高衙差斜眼又瞧了一眼李慕崎,心中一叹:好好的一位姑娘,就被如此之人给糟蹋了,哎!实是可惜,可惜。缓了缓又道“我总不能费了规矩。”
“大人,”杜如康小跑而来,躬身一礼道“您想想办法。”边说边从怀中拿出一锭金子,塞在瘦高衙差的手中。瘦高衙差见到那一锭黄金,心中一喜,面上却未露一丝喜色。杜如康瞧到那人将金子,慢慢的收入怀中,心中也是一喜。道“我们出门在外,十分的不容易。恰在此地又赶上无一家客栈可投。如今天色已晚,只怕前面已无客栈可投,还望您能通融通融。”
“嗯···”瘦高衙差迟疑道“总不能费了规矩,违了国法。”
“规矩,本就是人定的,既是人定,便有人情可言;国法。是不可违背,但是国法亦有人情。”杜如康缓了缓接道“这方圆五十里,只怕已没有一家客栈可投,难道您人心让老人与妇人夜宿荒野?”
“这···”
“况且这里本是您管辖之地,您就是此地的国法。”
“哎,岂能如此言语。”瘦高之人摆手摇头道,心中却十分的高兴。琢磨良久,方道“既是如此,也只好权且处理。”然后转身,看着圆脸衙差道“近闻强盗出没,百里之内已无客栈,权且收容他们投在此处。不过,伙食住宿费用需自付。”
众人忙回道称是。瘦高衙差又道“这里本是官栈,今日容你们留宿于此,实是因此地强盗出没,并非我一人弄权。”
众人又回了一声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