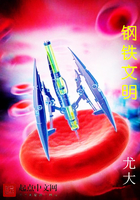韩忠邦引着兵士望巴图鲁部落而行,心中思索着李慕崎之言,有些疑惑,又有些不解。实在难以认同,但是想到李慕崎嘴角的那一抹自信的笑容,还有他的那一句言语,令他不安的心,稍微放松:他们素知我奸诈,你如此而行,他们必然认为我军主力已经到了巴图鲁,再不怀疑。
韩忠邦思道:倘若是自己用兵,必然会大张旗鼓,将李慕崎的帅旗摆在军中,而不是留在此时的李慕崎大军之中;定然速行,而不是如此缓慢的行军,只有在夜间,才会迅速的行军。
直到韩忠邦来到巴图鲁部落之东的那一处李慕崎指定的山脉之时,韩忠邦才知李慕崎心中真正用意:那里王破旅已经为他立下营塞,依山傍水,实在是一个用兵之地;而在那一座山下,还有一个营塞,却是一个空塞,虚设营帐,还有灯火,午时与日落之后,还有炊烟升腾。而王破旅之部就在韩忠邦营塞的对面那一座山上——是一片密林遮盖的山。站在韩忠邦之处,只能够隐隐望见一片营塞,根本不知多少,更见不到塞中虚实,不知兵数。而当韩忠邦踏进那个营塞,心中暗暗心惊,更加的佩服王破旅布兵与立塞之能。
叙礼毕,王破旅将韩忠邦引入大帐之中。
韩忠邦方落座,王破旅便将帐中士兵遣出,从怀中取出一封书信,交于韩忠邦,韩忠邦猛然见到这一封书信,不觉一怔。待他将信上所述内容细细读完,面上方才露出笑容,大笑道“妙。妙。果然是妙计。如此定会将敌人主力牵制,受制于我。”
早有细作将韩忠邦的动向报于敌军主将扎赫尔,而随着扎赫尔的军师亦是满都啦。
那一年扎赫尔兵败而归,受到众将士的侮辱与排挤,却有一位可查王子伸出援手,将他收入部中。而在争夺首领之位时,可查并没有得到老可汗的赏识,而老可汗将汗位传于他最小的那个儿子。
可查没有得到汗位,每日沉醉于酒水之中,浑浑噩噩,不理任何人。扎赫尔见到他如此摸样,心中担忧,便找那时很是得宠的满都啦。满都啦见到可查如此的模样,便劝说扎赫尔离去。闻言,扎赫尔大怒,便将满都啦撵出。见到扎赫尔如此反应,满都啦不怒,反而大笑。
见到满都啦面上的笑容,扎赫尔瞬间领悟满都啦之意——他是在试探扎赫尔。扎赫尔便与吗满都啦赔礼道歉,重新将满都啦引入自己帐中。
扎赫尔屏退左右,望着满都啦道“你可愿出手相助可查王子?”
“若是我没有此意,又怎会来此?”满都啦笑道,“待听到你相邀之言,我就猜到你绝对是为了可查王子之事。方才请赎我无礼?”
扎赫尔忙摆了摆手,道“无妨无妨,只要你愿意想帮,受再大的委屈我也愿意···”、
“当真?”
“绝不反悔。”扎赫尔面色一转,变的十分肃穆道“我以我扎赫尔之名向草原之神起誓,若是有违此言,甘受···”
满都啦笑道“我已知道你的心。”身体微微的靠近扎赫尔道“也素王子,并适不适合治理草原,若是将草原给予他之手,只破我族只会被那几个部落吞并,直至我族灭亡。”面色突然浮起一阵悲凉之意,淡淡的道“老可汗必是受到也素之母的蛊惑,又听到其舅的建议,才将可汗之位传于他。而能够将草原带向美好未来的只有一个人——可查王子。只有可查王子当上了大汗,才能将我草原带向光明。”
“可是如今···”扎赫尔深深的叹息一声,“如今可汗之位已经落到也素手中,我们又怎能够···”
“中原人有句熟语“大丈夫有所谓而有所不为。”你可懂此言?”
扎赫尔一怔,久久的望着满都啦,面上浮着挣扎难决的神情,许久方才将面上的挣扎之色退去,望着满都啦道“一切听你安排。即使···”
扎赫尔并没有将剩下的那几个字说出,但是即使他不说,满都啦心中已是懂得。明白。
满都啦亦叹息一声,缓缓道“只是,此事并不在于你我二人,而是在于更重要的那个人,若是那个人不同意,你我即使拼上性命也于事无补。”
恰在此时,一个人摇摇晃晃的闯进扎赫尔的大帐之中。见到此人,二人面色大变,心中巨惊,扎赫尔的手已经握在自己的刀柄之上,望着那个人影厉声怒道“不听传唤,竟敢汝我大帐。”言语一毕,道光已经飞出,直取那人白颈。若非那人及时的一句言语自嘴里呼出。只怕扎赫尔手中的刀已经落在他的颈项之上,此时已经有一片血光,闪于满都啦面前。
“为了草原的未来,一切罪过,全由本王承受。”见到慌忙跪下的扎赫尔以及满都啦,可查虽然满身的酒意,眼中却寻不到一丝醉意,速将二人扶起。听着扎赫尔在耳边直呼有罪直言。望着扎赫尔笑道“你又有何罪?有罪的是本王,只有本王一人是罪人···”
就在那一晚过后的一个月,也就是老可汗死去的两个月后,忽然有一个说法在草原的每一个部落之中传诵,尤其是曾经为了争夺可汗之位的那几个王子此时所在的部落之中。听到这个传言,草原之上瞬间燃起一股火焰,虽然这簇火焰此时还并未形成一股巨焰,还只是跳动的火苗,在风中晃动的微弱的火光。但是,每个人心中似乎都知道,它总会将整个草原点燃。
只有一个部落没有动静,一点动静也没有。仿佛没有一个人听到过那个传言,似乎所有的人都不知道那个传言。但是,他们听到了,每一个人都知道那个传言,几乎每一天在月光中谈论的也是那个传言。而他们之所以会如此,只是因为可查的一句言语。他们一向认为,可查绝不会欺骗他们,也不会令他们受到伤害。可查是他们心中的神,是他们最爱戴的人。
那一场大火,终于在草原之上点燃,而点燃这一团火焰的人正是扎赫尔与满都啦推测之人——默读王子。他是一个极易暴怒之人,是一个没有任何的耐心之人。心中的所思所想,几乎全摆在他的面容之上,只要认真的看一看他的脸颊,就能够知道他心中的想法。这样的一个人,极难将别人的言语放在心中。若是他嘴里说同意,知道,定不会忘记,那只不过是因为他不愿再听唠叨,敷衍的言语而已。而这样的人,一定会被他人所利用,被他人当作工具。而将他视作工具的人,并不是可查,也不是满都啦或是扎赫尔,他们绝不会将他视作是他们的工具,他在他们的眼中根本就没有这个资格。而将他视作工具的正是他们把他当作工具的那些人。
人,一生在世,总是自认为将某一个人玩于鼓掌之间,殊不知他自己亦是别人的玩具;是别人利用的工具而已。也许,他的价值就是如此···
默读,再也难以忍受等待,再也不愿意在等待中煎熬,终于带着本部兵马杀来;而他能够得到的只有一败。败便是死,而在他面对死亡的那一刻,眼中亦在望着曾经与他合谋,答应作他后应的那些兄弟的影子,心中还是认为他们绝对不会欺骗自己,绝不会不支持自己。他是如此的信任他们,他们亦会如此的对待自己才是。
真心并不会绝对能够遇到真心。往往会遇到伪善的真心,披着厚厚的伪装的真心,满口谎言填充的真心。世上之事就是如此——如此的令人难过,恐惧,害怕。但是,若是不将自己的真心拿出,一生也不会遇到一个真心之人。面对着恐惧,还得颤巍巍的守护自己,小心翼翼的守护着自己的真心。
他们一定会来,他们绝不会不来。只不过那时,默读已死,他已经看不到这样的日子,已经看不到这样的情景。不见,于他来说只能够是一种幸运,并不是痛苦。若是见到此景,即使他不死,也会被气的吐血。
杀意。将每一片青草染上了鲜红的颜色,仿佛每一株草都被染过血液一般,鲜红,而透漏着一股淡淡的血腥之味。草,会是如此的鲜红,也许是因为挂在天边的夕阳,那一轮被鲜血染红的夕阳。乌鸦在夕阳之中啄食着地上的尸体;而草原之上的雄鹰,亦在夕阳之中低声的悲悯,似乎如此的血腥之味,亦令他感到伤心难过,甚至不安···
此时草原之上的每一个人都在渴求着和平,希望见到从前的平静,从前的安宁。他们的心中此时已经满是恐惧,耳边总是响着哭声,响着叹息之声,一声声令他们心惊恐惧的声响。而此时仿佛只有一个地方是他们心中的天堂,而他们的心中不知何时升起了一个希望,一股点燃他们生存下去的力量。
之所以会出现如此激烈的战争,只是因为默读死后的第三天,新可汗却死在他的床上,而他的头却出现在默读的荒坟之前。可汗之位空悬,又有谁会不动心?又有谁会不去触摸那一个令人血脉膨胀的位置呢?他们是狼,饿狼,已经忘记了思考,忘记了怀疑,忘记了自己的理智,只知道拼抢眼前的东西,而忘记了一直在背后设下这一个陷阱的猎人。
越是华丽,越是令人兴奋的事物,越是危险。若是想要将他收在怀中,并不只有将自己的敌人打败就能够如愿,还得懂得一件事,知道一个方法——将它身上的所有危险除去。但是,世上很少有这样的人存在,每一个人都会忘记——忘记思考,总是会将它直接收在怀中然后看着它从自己怀中流去,甚至还会将自己性命被它一同带去···
和平,或许对于在战争中挣扎许久的人来说,并不会太晚;但是对于一个曾经活在幸福之中的人而言,实在太晚。甚至有些怀疑,不敢想象。不敢想象曾经,也不敢想象未来,甚至不敢将自己的眼睛闭起来,总是会担心此时此刻幻觉,只是一场空梦···
和平,对一个想要过上安逸生活的来说,是世上最珍贵的礼物,但是对于一个心中满是欲望,心中满是对自己也不能够确定的未来的人而言,只是一个阻挡他前进的绊脚石。所有的欲望,所有的未来,必是须将此时的平静打破。只有打破此时的平静,才能够见到那个自己想要的未来;而想要实现心中的欲望,只有不断的杀伐,只有不断的征伐才能够得到。若不如此,怎能够将欲望的空洞填充?
望着眼前的满是疲累之色细作,满都啦缓缓的将自己的思绪收回,将自己的目光集中在他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