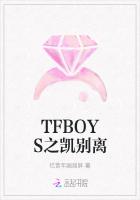“的确,我注意到了你眼睛不自然的红色。”他蹭了上来,呼出的热气盖我一脸。
“你也想到了不自然这三个字了,看来也不是我的主观意识才这么认为的。”
“我可以不相信自己的感觉,但我得相信我的眼睛看到的东西不会有问题。”他显得有些“不正经”。
“不是充血,”我用拇指和是指将其中一只眼睛使劲掰开,面向着他“更不是血丝。”
“看见了。”
“有什么感想吗?没准我命不久了,说说吧你有什么感想,警官大人?这或许是我们最后的谈话呢没准。”
我继续埋下头看着无聊的文本,一边跟他聊着天。
“凡事都不要那么悲观了,既然排除了疾病感染,那就还有其他的解释。”
“我可从不会对所有事都那么乐观。就算是辐射,更不见得是好事了。”
“我可不敢保证是辐射引起的,但我干推断,在那间房里的某个角落存在一些放射性元素,我更偏向于镭系,这破坏力足以符合铀系所表现的破坏力。”他满意的点点头,好像把我撇在了一边,好像在为自己的重大发现心满意足一样。他抬起咖啡,抿了一口。
“铀?”我抬头问。
“没错,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资料所见,正是铀。”
我读着这篇关于铀的资料,一种前所未有的无知感涌了上来——我只字未懂——文末的一句话倒是稍微能理解:对于基因的改变造成的症状,并不局限于表现在局部或是某个器官的畸形和病变,更有极大的可能会波及到半身和全身,严重者会在短时间内死亡。
“半身?上半身还是下半身?”我问。
“是左右半身,”他否决了我“这跟某类疾病的偏瘫和偏身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你是想说,多型性神经胶姆细胞瘤。”我放下无力的右手改为左手举杯,抿了一口。
而最近表现出的“偏瘫”,也极为严重了。我的内心不知从何时起产生了一个小小的冲动,绝不活到瘫痪的那一步,真到那一步的话,就是我离开的时候了,希望是“题有完肤”的离开。
这么想着我好想好受了一些,将咖啡一饮而尽,于是此时的我又端着第二杯咖啡似懂非懂的看着眼前的资料。这些资料好多都超出了我理解的范畴,这点我得承认,所以我选择性的看着,近乎于一目十行。
“问题是,”我说“就算是真的有你所说的放射性元素,那又存在于哪里呢?那房间就那么大点要知道。”
“这跟房间大小也没关系啊,也不是要几顿多的铀才能有那么明显的辐射效果,恰恰只需要那么一丁点,就会让你成为一个变异人。还记得那幅画吗?红红的眼。”
最后的四个字不由得让我一惊,据我所知那幅画他并未看过。好吧让我吃惊的事情好像也不少,但我得承认此时的我很吃惊。
“你怎么知道那幅画?”
“不为什么,我就是知道而已。我知道的事情远比你想象到的还要多,也比我想象的更多。正如我知道了那幅画并不是出自白杨之手一样,而在当时闻名一时的红红的眼巨作,后来不知为何列在了白杨的名下,传闻并不是他画的,但署名却是他,这点好像也能说明一些问题。”
我注意到了他用了一个不谨慎的词“不知为何”,既然他都了解了那么多,为何又一瞬间“不知为何”了?
“所以我看见的那幅画,是真迹?就是遗失的红红的眼巨作咯?”
“照目前看来,正是这样了。”
“这跟放射性元素有什么关系呢?”
突然一阵眩晕,我不知人事睡了过去……
“唐言川……唐……川……”
半梦半醒之间,一个女人的声音像是在一间空旷的屋子里回响着,像是寂静的老林里传来的画眉声,如此空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