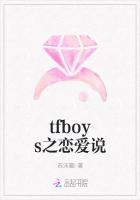“你的乞力马扎罗。”
“加糖了吗?”我问着这家咖啡店的服务员。
“按你要求,没有加。”
“谢谢。”
我安详的——或是表现得安详的坐下,咖啡散发的浓香迷惑着我,转眼我就像是一个克制不住的吸毒犯,端起了咖啡。而我并没有失态到一饮而尽,而是抿了一口。
“她是自杀的。”
“不,她不是自杀的。”
两个声音从脑后传来,我转过身。
声音停止了,我后面并没有人。
“她不是自杀的……她确实是自杀的。”
我转回来,对话声再次响起,而我也没再回头。
“众人参与的自杀。”
“很不幸。”
“但她最起码走了,没再被伤痛折磨,比我们还幸运,看看你,再看看我,我们都成了逃犯。”
“折磨人的都是活着的自己罢了。”
“可她的自杀我们都参与了。”
“那她为什么自杀?”
“不知道,这不是每个人都能知道的。我只注意到了逃犯的眼睛,他们好像很惊讶。”
“这没什么惊讶的,但是,听着,这里没有逃犯,她只是自杀而已。”
“众人参与的自杀,我们都是自杀的参与者,至少我们目睹了,假如我们没有目睹这一切,也许情况还稍微好些。”
“我们没有罪,至少我没有罪,我只是旁观者,我一直这样认为。”
“旁观者才是最大的罪人。”
……
“你的第二杯咖啡,卡布奇诺。”
“谢谢。”
我看着转身的侍者,再次低下头。
“罪不可赦的旁观者,每个参与者,还在苟且偷生着,想想吧,这个说法毫无夸张,总的说我们都是参与者,我们十恶不赦。”
“但我们不是知情者,只有知情者才有罪。”
“但……我们却知道了她自杀,目睹了她的自杀,这个理由足够证明我们是有罪的。我们都安详的坐在这,好像对之前的事一无所知,又好像对之后的事一无所知,我们是罪人,恐怕永远得不到宽恕,带着这一抹罪恶悲惨的活着,直到死去,直到化成灰烬。”
“而灰烬也还在空中弥漫着。”
“那我希望是……深埋在地底下的一无所有。”
“她就是自杀而已,有罪的不是任何一个人,也不是她自己。”
“那就是我,我有罪,我承认,我不希望得到原谅,我只想得到一分宁静,如果到最后我宽恕了自己,那才是最大的幸运,我从不奢求人们的宽恕,那没有意义。”
“何为意义。”
“意义在于,我能原谅我了,也正是罪恶消失的时候。”
“那你什么时候原谅你?”
“不知道,我得想想。”
“分散注意力不代表罪恶感消失。”
“我知道。”
“尝试抹掉罪恶也不能使罪恶感消失。”
“我知道。”
“你始终要得到她的原谅你才能更好的原谅自己。”
“可是她死了。”
“悲催的就在这里,你得不到任何原谅,只能孤独的自我宽恕而已。”
“罪恶感不是我的思想引起的,我想,这是一种感觉,幻象而已,这不是我本意,我的灵魂无法左右我的幻象,我的思想也一样。”
“那是什么样的灵魂呢?”
“我的灵魂只会在放肆的冲击我,我的思想也只能主导我的行为,听着,我很好,我的罪孽都是我的这里在作怪,即是我的心。”
“那就是灵魂了。”
……
“没有拿铁的咖啡豆了,所以我们给你准备了这杯哥伦比亚,这是我们店长推荐的。”
“没关系,谢谢!”
侍者收起了两个杯子,于是在我眼前的这杯哥伦比亚倒像是成了世界上最好喝的咖啡。
“我从不认为灵魂是主导感情的因素,思想也不是,感情是独立的,任何感情都是独立生成的,毫无做作的成分,毫无理性的成分,带有理性的感情都是作假的情绪。”
“只是情绪?”
“只是情绪,不是感情。”
“幻象也是情绪罢了。”
“才不。”
“感觉也是情绪罢了。”
“也不。”
“那是?”
“带有理性的一切情感,都是情绪罢了。”
“所以这就是你存在的罪恶感。”
“正是。”
“所以你在放纵这样的罪恶感,不伺机收回。”
“我收不回来,我是这么认为的,我只希望它会平白无故的消失。”
“平白无故?”
“也许能在一个不经意的眼神间,一个看上去不重的语句间,它就会消失。”
“那是什么?”
“无从所知。”
“好吧,我也有罪,我目睹了你的罪,我好像更加罪不可赦。”
“你得看你的定义而定,什么是罪,什么不是。”
“不,我要否认你的观点,在我看来思想和灵魂才是主导情感的最大因素,情感不是独立的。”
“没准是吧。”
……
“谢谢你的蓝山!”
我起身望着侍者,抿了一口咖啡。
他好像很惊讶,随后说道:“你刚刚喝的是哥伦比亚,不是蓝山。”
“不是?哦,那奇怪了,我一直以为我在品着蓝山。”
我走出了店,摇了摇头,我更倾向于我喝了四杯咖啡,尽管我只喝了三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