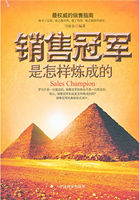在上一篇的结尾处我提到我仿佛嗅到了20年前的气息,有同学就说那是桂花和栀子花的香气。的确,学校里有桂树和栀子花灌木,夏天,有微风的日子,到处都香气扑鼻。但是这些桂树长在哪儿,白色的栀子花开在哪儿,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了,记得最深的是身高叶阔的法国梧桐树,夏天浓荫蔽日;秋天叶子变黄,倦了,十一月份左右开始有落叶;那落叶没有纷纷而下的景致,而是一片两片的,像人怀着眷念的心思一样慢慢地凋落;叶落要持续一整个冬天,直到来年三四月份树叶才会落尽,然后在一个不知不觉的夜里摇身一变,以一身亮闪闪的新绿登场。
从学校西北角正门一进来的理工大道上,南侧正是一排法国梧桐树,与北侧则的夹竹桃形成一个夹道,给人一种幽深幽深的感觉。大一第一学期,我们的早操集合就在这条路上。记得每天广播一响,我们从被窝里爬起,匆匆梳洗一下,然后拿着饭盆冲下楼,把饭盆放在楼下门口的铁皮桌上,跑步来到这里签到。我们既不做早操,也不跑步,就是签到走个过场,倒是有个年纪大概五六十岁的男人,每天从我们身边跑过,我之所以记得是因为他跑步光着膀子,不管多冷的天。理工大道走到头右手的地方就是学校的中心所在地——行政楼,楼前广场上的那个发动机叶片的标志还在,台阶以上的地面上换了方砖,两侧的松柏树苍翠欲滴,看起来跟20年前一样。行政大楼我只进去过一次,是作为新生报道的时候。一楼大厅里各个系分别摆了桌子,有老师坐在后面登记注册,然后让我们去财务处交钱。因为我是头一次出远门,一个人去学校,家里人担心路上会遭小偷,所以临出发前,母亲用一块布在我的裤腰里临时缝了个口袋,把钱塞进去,然后封上。我不知道这钱什么时候用,没有及时取出来,到交钱的环节上我才意识到我的700块钱还在裤腰里缝着。得找个避开人视线的地方把钱拿出来。我从大厅出来,看见右手的方向人少,就走过去,到一栋废弃了一样的楼下,准备拿钱。与此同时我看见草丛遮掩住的门前台阶上有一对男女,男的坐着,女的躺在男的怀里,一动不动。我没现场见过情侣们拥吻的场面,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是死的还是活的,吓得我呆在那里不知所措,半天才回过神来。我想不管他们是死是活,我的钱必须取出来交给老师。所以我走过他们到了那栋楼的东侧,把钱拿出来。回来的时候那女的已经坐起来了,让我松了一口气,庆幸自己碰见的不是死人。后来我才知道,那栋楼叫东附楼,我们军训的时候就在它前面的球场上,周绍雄和陈赦就在那里因为走步同边手,被排长逮出来给开小灶走步。球场现在仍然是球场,不过篮球架破损,地面上的水泥也有一块一块的松动,地缝里长出一丛一丛的草,看上去荒芜了。倒是西侧的西附楼仍然繁华依旧,现在改成了网络教育和继续教育学院,两个白底黑子的牌匾挂在铁门两侧。我们在这里上过制图课,记得里面的课桌就是一张张倾斜着放置的绘图板,图板都旧了,上面写满了各种字体的文字,人称课桌文学指的就是这个。我曾研究过这写文字,有的是一个人名,有的是一句歌词,或者随便一句话,大都以表达****为主,也有骂老师、骂同学、骂食堂饭菜不好的,总之课桌是个很安全又可以自由表达思想的地方,也难怪那时候那么盛行。现在这里已经没有了教室的样子,像个办事机构。2006年我在南山电信上班的时候,收到过一个传真,是我们学校发来的招收电大本科生的广告,我说我的母校怎么沦落到这种地步来招生了?有同事就回答说我们学校就是一个制售假文凭的地方,笑我不闻窗外之事,让我感到很没有面子,现在想来就是这两个牌匾下的机构搞的乌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