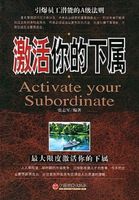列车即将抵达武汉。我靠在车厢玻璃上,看窗外不停闪过的高楼广厦、庞大车流以及穿着暴露的女性掠影。就我本人而言,这个中部城市已经是我有生以来到过的祖国最南端了,在北方生活了将近二十年,对于南方,我始终保有足够多的好奇。
车厢发生一阵骚动,人们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收拾起各自的行李。
“嘿,面霸,别看了,瞧你那色迷迷的样儿,敢情没见过美女似的。快过来帮我一下。”白曼菁半跪在上铺正要往下递行李。
“你怎么知道我在看什么,你以为我像你那么低级趣味啊,见了帅哥眼都直了!”
“这车厢咱们也走了一个来回,你倒是说我什么时候见帅哥眼直了?”
“我刚上车那会儿……”
白曼菁的脸一下子红了,表情凝固,半晌说不出话。
我上前把箱子接过来,询问道:“你没事吧?开个玩笑不行啊?”
白曼菁恶狠狠地瞪我一眼,然后说:“墙皮和你的脸皮比起来那就是小巫见大巫。看来我真是明智,叫你‘面霸’简直太符合你的特征了。”
“你……不能这么说我!”
“只许州官放火,就不许百姓点灯啊。”
白曼菁一口伶牙俐齿,说得我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我于是大言不惭地说:“好了好了,好男不跟女斗,你厉害行了吧!”
白曼菁转而面露喜色,哈哈大笑:“这不就得了,算你还有些自知之明。”
我和白曼菁拎着行李下了车,刚站住脚,便被汹涌而来的热浪所吞没。那感觉就像一出校门被人用麻袋套上掳了去一样,给我当头一棒。我措手不及,浑身是汗,四下一看,发现自己真是傻叉:刚才火车上空调有点冷,我嫌外套往皮箱里塞着麻烦就穿在了身上!我说怎么那么多人用异样的眼光看我,我还以为他们没见过外地人呢……这下丢脸丢大方了,我意识到这一点,迅速挪开车门的位置,三下五除二把上衣脱下来,想起刚才看到的那些穿着暴露的姑娘,我此刻由衷地感到理解:看来开放的尺度是与天气的温度有着紧密而直接的联系的。
白曼菁显然比我有常识,她上身穿了一件薄薄的花格子衬衫,下面是浅色的七分裤,甚至连鞋都换成了凉拖。这还不算,当我热得快要抓狂的时候,她居然淡定地从背包里缓缓取出一把折扇,悠然自得地摇了起来。
我当时那个羡慕嫉妒恨啊,一窝蜂涌上心头,没好气地说:“有那么热嘛,你可真会摆谱,要不要再往头上架个风扇可劲儿吹!”
白曼菁得意洋洋地说:“好啊。”说着像变戏法一样又从背包里取出一顶帽子。这顶帽子还真是不一般,帽檐前边居然有一个小风扇。白曼菁娴熟地把它戴在头上,也不知道还摁了什么开关,小风扇就鬼使神差地开始呼呼地转了起来。
我木然站在一旁,不敢再吱一声,担心自己的话稍有不当,白曼菁说一句好啊立马又从背包里取出什么新奇的玩样儿来。我就纳闷了,难不成她和哆啦A梦师从同宗?
“快点走吧,想什么呢,面霸!”白曼菁一边拖着行李箱朝前走,一边不忘回头招呼我,“给,这把扇子你拿着用,我有帽子就行。”
我不得不说,这是让我在炎热包裹的武汉第一次感觉到凉爽的一句话。
我有点小感动,接过来不好意思地说:“谢谢你。”
“这么客气干嘛,要谢也是我谢你才是啊,多亏你一路上对我的照顾,你知道女孩子一个人出远门很不方便的。”白曼菁认真地说。
我大为感动。这话就像春雨般洒落在我心田,滋润得我心花怒放;就像春风般吹拂过我脸颊,呵护得我心神荡漾。这样的感觉在我人生阅历中似乎时有体会,我记得它上次出现的时候,是我妈在我软磨硬泡之下答应给我买一部新款手机。
“这点照顾是应该的,以后要是有什么事需要帮忙,尽管给我打电话,只要我能帮上的,一定不会推辞。”我受人之桃理应报之以李。
“你电话号码是多少?我打给你。”白曼菁拿出手机做好拨打准备。
“这个……我不记得了,好像是13……13……你等等,我应该记在本子上了。”
“不用,你把你的手机给我。”
“你要……我的手机干什么?上面显示不出我的号啊。”我不解道。
“我知道,我用你的手机给我打过来。”
“哦,好。”我把手机递过去。
白曼菁很快拨出自己的号码,片刻后她的手机发出清脆的铃声,她摇了摇手机,冲我一笑:“好了,我已经收到你的号码了。估计到了学校要换号,到时候我再打电话通知你。”
“你只要别半夜打过来吓我,我一定不会不接。”
“喂,面霸,不许你再开这样的玩笑!”白曼菁斩钉截铁地说。
“好好好,不开就不开。”我摇动手中的折扇向前指道,“别傻站着了,一会儿要赶不上二路公共汽车了。”
白曼菁抿起嘴笑着说:“那快走吧。”
顺着人流穿过阴暗的地下通道,走出车站的一刻,空气中的喧嚣在我耳畔回荡。混乱而庞杂的火车站,迎来送往多少离合悲欢,但它更像是一只偌大的容器,承载着在此扎根的黄牛小贩扒手**乞丐的身家和性命,卖艺拉客偷窃坑蒙拐骗乞讨……每天都在上演的剧情,不停变换的主人公,这一切在它眼里都是那么微不足道,它只是呆呆地装逼式地矗在那里,不悲不喜,不吭不言,不闻不问……
白曼菁打车离开,临行前给我做出一个电话联系的手势,我点头微笑。
我拖着行李箱,漫无目的地走在大街上,完全不似一个刚刚结束长途旅行的人。旅行的人总是带着疲惫的灵魂,这之于我却不然,我的心中充盈着对于大学生活的憧憬和向往,对外面世界新鲜事物的好奇,对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的期待……我感觉自己浑身都是使不出的劲儿,想找一个地儿把他们挥洒出来。而这个地儿,我翻山越岭从千里之外赶来,如今它就站在我面前,我忍不住想大喊:武汉,我来了!
三年以后,当我和大学同学围成一桌喝着小酒畅谈初来武汉内心的感受时,除了一个被取名“**”的同学之外,大家都认为我当初的想法太过幼稚矫情,而他们的则显得很务实——他们那时普遍的想法是:武汉的姑娘,我来了!
而“**”同学之所以没和他们同流合污对我的想法进行批判,是因为他下了火车包就被人扒了,损失不小,在心理上留下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他当时的真实想法是:武汉,我草你大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