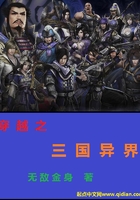第六回
国破子离夫人蹈海
山高水远右王勔行
冒顿在且蛰出发后不久就上路了。由月氏正、副两名使者和几名随从人员监护着,冒顿稍稍勒住马缰,磨磨蹭蹭走在被车马碾踏出又被风蚀了的道路上。路上的马蹄痕迹,是且蛰和他的小型卫队刚刚留下的,这使月氏人多少产生了一些联想。
一队两帮人,各自想着心思,互相猜度,无论表面多么从容自信。月氏使者确实显得大度,随冒顿,爱咋走就咋走,快慢止歇也都能将就,反正大方向没有错。
使者名叫居敕臼,此刻头发披肩,格外洒脱,有一番超然优游的雅致。对他来说,能不辱使命,带着鲜活高贵的猎物向月氏天子交差,而且没费什么劲,心情便是愉快的。当然,他对此次出使如此顺利有所不解,暗里也不免犯些嘀咕。
侥直那悉心履行职责,日夜护卫着冒顿。行程十分缓慢,倒是居敕臼的副使骐冼性急,不时打马绕前绕后地跑动,作一种敦促的暗示,但完全一种用钝刀子割风干牛肉似的无奈。急透了,就朝着旷野烦躁地叫嚷,但无论怎样折腾,都无济于事。
居敕臼不时看看在前面率意走走停停的冒顿,想象他是狮子还是绵羊,不很看得出来!有时,也与冒顿走到一起,他感到,那双偶尔抬起的眼睛,泊予人无法窥测的迷茫。他反复叮咛骐冼和随从人员说:“不可随意拿捏!”太子毕竟是太子,他是一把极其敏感的双刃剑,是战与和的弩机,轻易招惹不得。
侥直那十分强悍,总把持着一种似浅似深含而不露的坚定态度。一切都只在拧劲的体验中,一切都让人感觉不很协调,不那么得劲!居敕臼清晰地知道,自己必须把“活宝”完好地献到“天子”堂前,其余都不重要,因此对谁都十分地将就着,他算得上是一个极能忍耐的人。而骐冼迫于居敕臼的眼色,只能在心里嘀咕:“逮着机会再说吧!”
遥远处有一大片乌云罩过来了,直把心情遮得半阴半阳,很不爽快,雨却没有能落到地面。冒顿抬头了望,乌云下面已经看到山了,右看也是山,于是突生一念,放马向右边叉开的一条路上奔去。月氏人紧张了,骐冼没忘了朝正使看一眼,见居敕臼并不在意,他也就放下心来。随即打马跟了上去,算是不温不火、不即不离,这也是一种心理战术。
冒顿是转向了蒲奴水的方向。蒲奴水从西北到东南,有头有尾地联络起燕然山东南角和涿邪山北坡浚稽山的山峰。似这样走法,从脚底到夫羊句山狭的路程,就凭空多出了一倍,依眼下的速度,要多走三、四天。
沿着蒲奴水南头走过一段,冒顿的心里仿佛找到了某种安慰,多出了一份塌实。他极想折往西北边的深谷中,因为那里有右屠耆王且蛰的大帐。但路程不近,粗算也有近千里的距离,直线略等于从单于庭到夫羊句山狭。
这是一种怎样的留恋呢?因为过了夫羊句山狭南边的鞮汗山,就要进入一片广大的不确定地域,那里是匈奴人、月氏人、秦人,甚至西域人都可以走来走去的地段,是缓冲带,是平衡点,但也意味着,无论谁加强对这个地带的控制,谁的军队走到这里,就会引起多方警惕,甚或破坏战略平衡。
脱离了蒲奴水,真正要走山路了。所有横越山脉的路,都是从山的峡谷中找寻出来的。峡谷蜿蜒着,过了这山上那山,上升了,下降,又上升,盘来绕去,到了涿邪山南的一个险要峡口。月氏人和匈奴人几乎同时发现,夫羊句山狭的山坡上屯驻着一支人马。
居敕臼的脸色发生了细微变化,血涌上了他的头颅,但外表还是不动不摇。骐冼等人有些惊慌起来,他们不由自主地向冒顿和侥直那的位置靠拢,不知是想得到这两个匈奴人质的保护,还是想更随机地挟持他们。
十多天一路走来,慢吞吞几乎一声不吭的冒顿,驱马跃上一座山冈,向峡口看了一阵,突然放声大笑,然后对紧随身边的侥直那说:“我说是谁呢,原来是右王大哥!”侥直那用力点点头,流露出一种会意的表情。
几骑马出了谷口,远远迎上前来。居敕臼心里越发收紧了,骐冼的手握住了刀柄。冒顿和侥直那不紧不慢走自己的路,月氏人警戒着硬着头皮护住左右前后。
此时的居敕臼经过紧张的思考和衡量,把提到嗓子眼的心,重新放了回去。他确定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于是,朝骐冼递了个眼色。骐冼过来了,居敕臼小声说:“别慌张!吩咐他们几个,保护好人质,不管出现什么动静,也要听我的招呼,不得擅自动作!”骐冼答应:“是!”他紧绷的神经也随之放松了些,稍微恢复了弹性。
匈奴人飞驰到了面前,为首一名小将抖擞精神,就马上参见冒顿太子,自报姓名:“卫队长曳当参见太子左屠耆王,特地带来右屠耆王发自内心的心问候!”
冒顿脸上露出了笑容,说:“有点印象,有点印象!”转脸对侥直那说:“原来小将是这等矫捷!”侥直那连忙上前。曳当见了,以手加胸抢先行礼,问候道:“侥直那大哥别来无恙!”侥直那还礼。只因他们肩负的是同一种职责,彼此之间总有些交流,算是熟人。而此时此地突然相见,更增加了几分亲近。
当下曳当几骑马在前面引路,一行人来到夫羊句山狭右屠耆王临时驻地。且蛰迎一行人入帐,对月氏使者亦礼貌相待。全体坐定了,喝了奶茶,寒暄过了,且蛰开口商量说:“太子此去山南,一年半载再难见面。本王要与太子去谷中散散心,说些闲话,不知使者大人心下如何?”
居敕臼此时还能如何,谅右部不敢擅自藏匿了人质,便爽快地答应:“但凭太子和右屠耆王,我们在这里等候就是了!”
且蛰安排右大都尉拔犴好生关照月氏使者,吩咐曳当带了酒肉,与冒顿、侥直那转到一处僻静的山谷。几株大树下,泉水汩汩,一片绿茵铺开在石滩上。冒顿抬头看四下里裸露的巉岩碎坡,感叹一句:“王兄真闲情逸致,竟能在这干沟里找到如此一搭水草!”
两人边把酒边说几句闲话。喝过一阵,且蛰忽然问:“乌孙是完蛋啦,可还有个关键的传闻,不知太子听到没有?”冒顿说:“不知兄长指的是什么事?”且蛰说:“关于难兜靡的一个小王子。”冒顿问:“有什么好听的,说来解解闷!”且蛰笑了:“确实能解点闷。”
话还得从头说起。
祁连山北麓连接西域的河西走廊,春秋时原本分属秦和西戎。“戎”属于松散并不断变迁的广泛的族群概念,北、西、东皆有之。西周金文中称游牧于北方的“猃狁”为“戎”,那是匈奴的祖先。东方有“徐戎”,周初也称殷人为“戎”。春秋时在中原北部广大地域有“北戎”、“山戎”、“大戎”、“小戎”等等。战国末到秦汉,“戎”则专一归结到偏西的族群,出现了“西戎”的称谓。月氏、乌孙分别从戎的泛义族群中分离出来,介入中华史册后有了新的称谓。两个名称,包括“猃狁”的读音都是由汉字摩音所得,拿捏快读起来仿佛都是一个“戎”字,其区别更像是由不同口音转注带来的差异。
两个新兴族群早期的势力分野大致在籍端水、冥水,其东为月氏,西边三危一带则为乌孙。“三危”因山而名,到汉代改称“敦煌”,那里最早的居民为“三苗”,春秋时代则生活着允姓之戎。籍端水、冥水属于今疏勒河中游昌马河段,后来成为汉酒泉郡与敦煌郡的界线。疏勒河出祁连山北,大势呈扁长的“Z”形,中游部分呈南北走向。
随着东邻的秦国逐渐融入中原社会,中原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也渗透到月氏,带动了它的历史进步,而远一些的乌孙则停留在相对原始的阶段,方方面面都处于边缘地位。
作为逐水草而居的行国,匈奴、月氏、乌孙等都具有相似的风俗。他们的头脑中只有合适驻牧的水源、山地和牧场,而领土的概念则难以得到认同。最初的状态是,牧民循着水草放牧,走到哪里家就在哪里;搭上毡房,散开畜群,那里就是他们的牧地。族群凭实力控制地盘,地盘在哪里,所谓的“国”也就在哪里。当然,在一定时间内,族群只能占据与自己实力相当的、相对稳定的势力范围。逐渐,随着新的生产关系的发育,处于特定内部管理体制下的牧民,一般也会动态地获得名分内的多少不等的牧场。
但是,产生于生存客观和原始冲动的领地需求,族群之间总在挑起频繁而无休止的争夺。一旦力量的平衡被打破,为利益而随时发生摩擦与战争当然是极其正常的事。显然,那是一个邻则为敌的时代,月氏与乌孙之间的争端与史俱来。面对战国后期逐渐强大起来的月氏,北部强邻匈奴尚且屈从三分,弱小的乌孙则不得不处于附庸地位。月氏、乌孙又同处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中,乌孙必然成为月氏侵凌和吞并的对象。
屈从历来只是暂时性的选择,不在屈从中崛起,就在屈从中灭亡。不久前,乌孙终于被击灭,牧场和水源统统被月氏占据,部落人群四散逃亡,大部分避入匈奴右部。他们在那里得到了右屠耆王势力的庇护,期盼着恢复自己“传统”的领地和微弱的尊严。
话题有关一位乌孙贵族逃亡中的传说。且蛰告诉冒顿,乌孙国王难兜靡在抵抗中被杀死了。他说:“那是好样的,面对比自己强大几倍的月氏军队,他没有畏惧,没有退却,而是战死在籍端水。”
难兜靡的夫人因为得到了丈夫的掩护而逃离了大帐。“她不得不尽量逃走,因为她与丈夫有一个还在襁褓中的小王子,必须保住王族的血脉。”
冒顿点点头,不由得联想到了匈奴单于的血脉:“……当然还有其他弟兄,还有小弟弟芷劬。可是,他还太小!”他很是怀念自己的生身母亲,她是父亲的颛渠阏氏,这相当于中原皇帝的皇后,在单于族内居有不可撼动的地位。但是,她已经辞世多年了。
“夫人逃到了冥泽……”且蛰说。“她十分惊慌,毕竟是女人嘛,怀里还抱着个吃奶的孩子。眼看卫士一个个战死了,月氏人已经越来越近,躲避不了,跑也跑不掉,形势十分危急。她正要从一片灌木丛附近经过,却勒住了马……”说到这里,且蛰似乎有些激动。“来,喝酒!”两人举杯,一饮而尽。
冒顿当然猜出是咋回事了,说:“只能听天由命了,夫人兴许这么想!”
且蛰点点头:“也只能这样……夫人整了整襁褓,取出丈夫仓促留下的玉佩塞到孩子怀里,裹紧了,小心地把襁褓藏进一堆隐蔽的草丛中。她重新上马,飞快地逃去。最后一名年轻的卫士赶来了,他已经无力抵挡月氏人,只能在夫人身边做一面盾牌。”
冒顿说:“了不起,是这名卫士让月氏人忽视了那片灌木丛!”在一旁的侥直那也不由得点头。
“显然是!”且蛰认同。
冒顿沉默着。
“……来,多吃点,太子恐怕要有一阵子吃不上咱们匈奴的羊肉啦!”
“夫人呢?”
“夫人死了……”
“她是咋死的?”
“她对身边的卫士说,你赶快朝那边跑吧,他们是来追赶我的,你是可以逃脱的……卫士听了,不再跟着夫人,而是转身面对追来的月氏人!”
“我说夫人呢?”冒顿有点着急。
且蛰说:“她掉转方向……”
那是一位高贵的夫人,但她更是一名普通的女人,三危草原上年轻的母亲。她尽力保护了自己的孩子,然后策马朝着浩浩的湖水深处走去,一直到坐骑浮起在水面上,一直到身躯和战马一起沉没……
冒顿的眼眶里溢出了泪水。“来,喝!”不等且蛰端起酒杯,他已经一仰脖子,把眼泪与酒一起灌入口中。“那个小卫士呢?”他问。
且蛰说:“他和他的马都被月氏人射成了箭垛子。就这样,他也没有倒下,好像这样就可以为夫人挡住追兵。”
侥直那紧攥着拳头。他想起了自己对大单于的承诺,内心产生了不由自主的冲动。
冒顿点点头:“孩子呢?”
“谁能想到,离那片灌木丛不远的地方,有一片树林。林子里也藏着一队人马,他们是乌孙人。”
乌孙贵族步厩正带领残部逃向马鬃山。是难兜靡夫人在无意中引开了敌人,让步厩避免了同样的命运。
月氏人撤走了。他们夜间就投入了作战,又追逐了大半天,确实也筋疲力尽。月氏大当户鹩轺立马在海子边上,看望了许久,然后带着士兵返回。
午后天气阴沉,浓重的云层被阳光费力地捅出一个大洞,泄露出上天的意旨。步厩看到在阳光斜射的远处,树丛上方鸟雀翔集,顿感奇异。他飞马赶过去,只见一头母狼慢慢地离开草丛,步厩在它离开的地方发现了襁褓裹着的孩子。从黑地彩线的精致襁褓和孩子的面容,他依稀看出,那就是小王子。他回忆起远远看到的那场追逐,心里立刻明白了。果然,藏在孩子怀里的玉佩证明了他的判断。作为王室近亲,他非常熟悉国王难兜靡的随身饰物。在乌孙,即使像他这样一等一的贵族,也无法得到那样贵重的物品,这是王室的专有。
小王子没有啼哭,嘴角上还留有**。随从和族人们陆续赶过来了,步厩告诉他们:“方才,我看见一只健壮的母狼给孩子喂奶呢;看到一群乌鸦了吧,它们都衔着肉来喂王子,是被我等惊扰了,又叼着肉飞走了!”这眼见为实的传奇深深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他们深信不疑,全都视为己见。
步厩抱着小王子上马,小心地护在怀里,一路向东北方向越过马鬃山,疲惫地歇足在涿邪山附近,仰承匈奴的鼻息。小王子的这段神奇故事在流散的乌孙部落里飞速传播,为族人带来了期冀。
冒顿为这段传奇所打动,饶有兴趣地问:“那乌孙小王子现在咋样了?”
且蛰回答:“我已经安排了奶妈、毡帐和牛羊,专一喂养,责令步厩务必照顾好了,不得有任何闪失。”
冒顿点点头:“兄长远见,承蒙费心啦!”
且蛰回答:“乌孙的事现今就是我大匈奴的事,太子需要小王子时,尽管开口!”
冒顿说:“到时候再说吧,现在我还自身难保呢!”他忽然又想到了血统的问题,找到了一个根据。他曾经听一位忘年之交的朋友聂行说过,在中原,只有嫡出的王子,才能算血统纯正,才能有王位继承权。那么,自己肯定属嫡出,因为自己已经亡故的母亲是父亲的结发妻子,其他只能算嫔妃了,就是小老婆,没什么地位。可是芷劬呢,他母亲是在自己的母亲去世后嫁过来的,父亲又特别宠爱她。看来,芷劬的血统也是纯正的,即使按照中原的规矩,他也是可以继承王位的。不过,老大之后才是……老小……要么,自己为啥是太子呢!
冒顿被特殊的境遇所困扰,脑子里乱着呢。在匈奴,只存在单于亲疏远近,哪谈得上嫡出庶出。血统倒是讲究的,但分辨没那么细致。他想着那个叫聂行的中原商人,觉得此人见多识广,头脑灵活,就像自己的老师一样,这时候有他在身边就好了!冒顿下意识地摇摇头,面上泛出一丝苦笑。
且蛰把冒顿送到鞮汗山,喝过上马酒,行礼道别。他叫过曳当,吩咐:“本王先回大帐,你带上十来个顶事的,好好护送太子一程,到月氏北山后再返回,一路要让太子心情好些才是!”曳当得令,立即招呼人马,随在了侥直那后面。
月氏人和匈奴人又重新出发了。
曳当与卫队的跟随,使双方的心理位置暂时调换了一下,居敕臼感觉自己一行反倒成匈奴的人质。
马队到达居延泽。“居延”,据说是匈奴语“天池”的意思。冒顿似乎有了另一番心思,他骑马在长满芦苇的湖畔转悠,面对博大的湛蓝流连许久,然后策马疾行,不再像前一段那样磨蹭耽搁。居敕臼本就急着回王庭复命,看到冒顿一马当先,心想,看样子能顺当赶路了。
弱水从迷茫的地平线上迂回而下,使者的队伍与护送的骑卫扭结着,向西南逆水上行。正是旺水季节,河道充盈,还不断有细流汇入。不即不离的东、西河道形态紊乱,水系借以为潜伏在半荒漠植被之下的巨大根系提供充分的吮吸,为裸野上的生态难得地涂抹旺盛的生命色彩。
正午时刻,团团着的草地在炽热的阳光下暂时地萎靡着。一路上不全是草滩,有积水的洼地、大片的棘丛和牛皮癣似地裸露的碱滩。
曾被大水掩灌过的地方,泥沙表面呈现大片的龟裂,不断从下面蒸出热气来,使所有的行人都愈加感到困闷。偏偏冒顿又来了情绪,就在这难走又难耐的地方,下了马,旁若无人地步行。弱水在平和的地方打着皱,在急流的地方旋着涡,这都是冒顿无法表露的复杂而又难以自主的心情。
冒顿照样无视居敕臼的置身事外和骐冼的焦虑心情,只顾自己在沙地上费劲地搓步。侥直那牵着太子的和自己的坐骑,紧握腰间的刀柄,寸步不离职守。
命运正逆流而上,还不知终究会把匈奴太子带到什么地方去呢。也许经历艰难磨砺之后,也许……他其实有自己正从沉睡中唤醒的梦想。但是,冒顿就要到达聚集着狼群的地方,在那里,所有的眼睛里都将流露出敌视的表情,所有的胸膛里都满怀着憎恨的情绪,他们时刻都想吞没匈奴的牧场,把匈奴的男男女女,不管是贵族还是奴隶,统统都变成他们的奴隶。
“那么他们将怎样对待自己呢?”冒顿想。他的思绪被疑惑和猜测所缠绕,竭力寻找出路。
父单于会尽快想办法召回自己吗?虽然有了小弟弟之后,父亲就不那么亲近自己了,甚至变得有点冷漠,不,有点冷酷,但毕竟是生身父亲。还有,自己是太子,又是独当一面的左屠耆王,只在父单于一人之下,是被父单于赋予重任的,哪能再用娇惯的心理去看待父子情感呢!这次,父单于派我来月氏充当人质,应该是万分不得已。弟兄们或者地位不显,或者年纪还小,显然不合适,没有第二个人能承担这个角色了,只能如此。
冒顿相信,事情总得有一个通盘的计划,派遣人质只是权宜之计,父亲肯定会尽快设法解救自己的,毕竟太子对于大匈奴来说十分重要。也许,等到匈奴拿下北假,对,再拿下河南地,月氏就会慑于匈奴的日益强大,主动放弃人质……想入非非了。
但是,他确实不知道自己在月氏会遭遇到什么,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回到匈奴,不知道命运将怎样处置自己。他想,生与死就像隔着眼前这条河一样,此岸和彼岸是由无缰的水流左右的,命运其实就这么随随便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