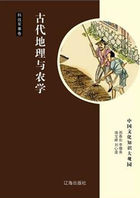第五回
遣质子头曼斥众议
惜月夜冒顿盟小溪
夜扯起一张朦胧的大网铺天遮地,把原野罩入一片混沌之中。在一线闪烁的水波点缀着的营地旁边,饕餮的士兵们依然不屈不挠地坚持着,像鏖战般胶着于火星零落的酒囊边。这一口锅边开放式地劝酒,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豪爽地款待朋友;那一堆火旁掏心窝子聊天,让不听使唤的舌头在嘴里搅动岁月的残渣。有人敲打着剃干了肉的骨头唱歌,踉跄着步伐起舞,看不清表情,只晃动着滑稽的身姿。敞开了封口的酒像流水一样汩汩地涌入腹中,在脏腑中滤留酒精,反复燃起神经对于酒的热情,而把残留的水分灌注到任意一片草地上。像这样源蹙流长,恐怕是一座湖泊也要被喝干了。然而,草原只要得到机会,酒,就是这种整法,哪怕明日喝西北风呢。
屈烈支自管了个不渴不饿,早就到一边的露天里,把长长的马缰绳绕在手腕上,怀里抱紧了刀鞘,腮帮子贴着刀柄睡熟了。在牧民和士兵之间,他更是一名士兵,这一点,他和卫队长侥直那颇为相似。赶走了疲劳,到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他照样弯弓驰骋,照样无比地剽悍而机敏。
出于善意,侥直那耐着性子让手下尽兴。看看不能再拖延,便招呼卫士们停止吃喝,拿水来浇灭了各处的火堆,放了夜哨,安排宿营。
头曼安抚好了夷莪,出到毡帐外,让侥直那去叫醒熟睡中的屈烈支。他们拣一块草地盘腿坐了,头曼开始仔细探讨太子和右屠耆王可能会对月氏的来信有什么意见。屈烈支很是认真,但实在是知之甚少,头曼心中焦躁,但也不必过分为难,便打发他去接着歇息。
等屈烈支去了,单于朝侥直那:“你接着方才的说!”侥直那开言:“想一箭射下两只大雁,那没什么可说的。但是,请单于看——”他从马鞍上解下那两只射穿在一起的野鸭,“即使如此,那箭也是先射中一只,再刺中另一只的。”
头曼边听,沉思半晌,说:“你认为该怎么对付月氏?”侥直那回答:“大单于意图牧马北假,月氏肯定是想到了这一点,特意来要挟,其实是试探虚实。如果他们侥幸得到人质,便掌握了主动,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这也就是陷我大匈奴于被动之中。”头曼问:“怎么解释?”侥直那回答:“我强,却奈何它不得;假使我们别处失手,形势稍一转弱,东胡、呼揭、鬲昆、丁零、浑窳、屈射、新犁等大小部落难免群起而从中取利,那时,最为有利的就是月氏……”话到这里,侥直那忽然意识到了什么,立即表态:“如果大单于有用得着的地方,末将必定万死不辞!”
头曼点点头,表示嘉许。转即沉吟有时,觉得周围有些阴冷,没来由丝丝儿寒气穿透了身体,直在心底里发抖,又琢磨不出是怎么回事。他问侥直那:“你身上冷吗?”侥直那回道:“这天儿是有些凉了,可我还总在出汗呢!”感到问话蹊跷,反问:“大单于没喝多少酒,怎就会畏寒呢,可是身体不爽快了?”头曼有所省悟,摇摇头,说:“睡觉去吧,天亮还得往回赶!”
夷莪搂着睡熟了的芷劬,反复瞪大困顿的双眼。过了许久,让那些服侍在周围的人都去睡了,自己仍然坚持着。等到头曼回到帐里,便重新打起精神来。
头曼进帐,来小阏氏对面坐了,说:“你尽可睡的,何必等我呢!”夷莪说:“那可不能,大单于不回来,就是等一整夜也是要等的!”
“小傻瓜!”头曼爱怜地说,然后摆出无可奈何的样子:“我们只能先回去了,待日后有空……不,就在大会蹛林之前,必定与你去龙城。将来,还要带你到阴山南边去看九原,那里本是我大匈奴的,但被赵国人修建了要塞,今又有秦朝派人守着。我发誓不但自个儿要去,还要我的阏氏和小王子也一同在那里的草地上遛马。”
看到夷莪只管拿睡意朦胧的眼睛盯着,便问:“还不睡?都瞌睡到家啦!”夷莪说:“我只想听你说话。”于是,头曼想了想,往下说:“赵国的国王是跟东胡学了穿短袄和裤子、靴子,骑马射箭,这才打败了本听命于我大匈奴的林胡和楼烦,修筑了九原城。但我大匈奴不久就要回到那里,这说明我们是最厉害的,你说是吗?”夷莪乖觉地点点头,应道:“大单于说谁厉害谁就厉害,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也许是头曼心理变得有些复杂的缘故,他因为夷莪无条件地通情达理而十分感动。夷莪又说:“我替大单于担忧呢,那月氏分明是乘机取闹,想从匈奴得到什么好处,真碍事,真讨厌!”头曼一愣,接着冷笑一声:“小小月氏,休要痴心妄想!”夷莪追问:“那就不派人质啦?”头曼说:“抱紧了咱们的芷劬,我不会为难你们母子,其他你就别操心啦!”
得到了这句承诺,夷莪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尽管身为阏氏,与单于的感情好得不能再好,但论及贵族女子在奴隶制王权下的地位,其命运也只被男人的兴趣操纵着。在内心深处,除了年纪尚幼的儿子,夷莪还能操心什么呢?头曼又何尝不知她的心思呢!
回到王庭,头曼召集臣僚,并没有进行大家期待中的讨论,便直接宣布了一个重大决定。
他叫来裹头巾的月氏使者,看时,真好人才!那使者不卑不亢直立帐下,身材结实略显高挑,窄袖长衫衣着鲜亮,脸皮白中透红,胡须修剪得非常漂亮整齐,浑身显露着浓重的贵族气息。头曼在心里感叹:我大匈奴何曾见过此等人物!
观瞻有时,头曼开口说:“本大单于决定派太子左屠耆王去为你家大王纾解郁闷,明天就可以动身了!”月氏使者尽管表现沉着,但还是对头曼如此痛快的答复感到意外。他连忙把手搭在胸前,口中表示感谢,难以掩饰地流露出惊讶的表情。
头曼之所以这么决定,想是有一定道理。当年燕、赵在强秦打击下渐见衰落,锋芒初露的头曼渔翁得利大举扩张,实力与日俱增,甚至乘虚抢占了林胡、楼烦旧地。但机会也同样属于月氏、东胡,在彼消此长之间,月氏兴盛而东胡也号称强大。及至头曼被蒙恬驱逐,历经数年,匈奴只能望漠兴叹。而月氏则基本与秦朝相安无事,秦对东胡更可以说鞭长莫及,彼两者都经历了一个稳定积累实力的过程。目下不等匈奴动作,月氏就敢于先发制人,也许就是一种佐证,这便不可不小心应对。但令众人惊讶之处,却在于头曼过于“示弱”,尽管这属于匈奴传统的军事策略。若论匈奴目前的实力,再不济也不至于如此屈服于月氏。
打发了使者,头曼便要众臣散去。但是,好半天,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有挪窝。也有想走的,看看别人没动,连单于也还没起身,便不得不陪坐。
左骨都侯叻俟祜几度欲言又止,他一直盯住坐在单于旁边的太子冒顿看,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方才下得决心,却听到右屠耆王且蛰先开口了:“敬问大单于,太子被派到不讲信用的月氏去,难道生命能得到保障吗?”他用异样的眼光看着头曼。
这问法令众臣吃惊。但头曼没有发怒,而是反问:“右屠耆王觉得让谁去更合适呢?生命就更有保障呢?”
且蛰当然无法回答此类问题。急切之下道:“若如此,本王宁可尽帅右部控弦之士与月氏一战!”
头曼问:“你觉得有把握吗?右屠耆王可曾想过,我大匈奴一但有所举动,便可能同时面临东胡的夹攻,还可能惊动秦朝皇帝。再说,看目下中原的局势,我回到北假的机会随时可能出现,你说说,到时候重点顾哪头才好!”
且蛰回答:“大单于本是知道的,这些都还在探讨之中,愚王不敢轻言。但太子一旦入月氏为人质,我大匈奴必然投鼠忌器,被束缚了手脚,凡事还须看月氏的眼色,那将是何等的被动!”
头曼忽然提出一个要求:“月氏既然派使者索要人质,那就是有心与我为敌。想来,它是看出了我急于南返阴山的心思,故而乘机谋算一步。这样吧,既然右屠耆王有意与月氏一战,那太子可以不去山南,但你要先给本单于一举拿下月氏的保证!”
且蛰既然有言在先,此刻也只好硬着头皮应承:“行,只要太子不去作人质,月氏的事就全盘交给我吧!”
叻俟祜偷眼看冒顿,只见太子依然顺着眼,面无表情。看不出他在想什么,或则什么都没想。
头曼见且蛰不肯让步,态度便强硬起来:“那我这边就杀了月氏使者,你回去立刻发兵,我只等着你的好消息了!”
单于突然表现得如此决绝,令帐内一片哗然。且蛰没法理解头曼为何如此迫不及待,如此咄咄逼人,更不理解单于为何偏要派太子去作人质,甚至不惜拿匈奴的命运孤注一掷。他其实已经在做打败月氏的准备,但毕竟才开始。对月氏动武极有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后果尚不可预料,岂能轻率。说到底,他与单于没法平等对话,这争执必须设法收场。
且蛰正在为难,叻俟祜却开口了:“我虽然不完全赞同右屠耆王,但也有些想法。太子身系左部,去当人质了,东胡必然敏感,也来索要人质,到时候又该怎么办?”
头曼反问:“那你说咋办才好?”
叻俟祜说:“依我看,统统不去理会,看他们能把我大匈奴咋样了!”
头曼问:“你不去理会,他便合伙儿来攻,却如何对付?”
没曾想叻俟祜也反问:“月氏留着太子当人质,若照样来打我们,又该咋办?”
头曼烦了,问:“你咋知道月氏会那样出尔反尔呢?”
叻俟祜见状,心里想:“您咋就知道他们不会出尔反尔呢?”话到嘴边,没敢说出来。帐内变得寂静。既然已经形成一个情绪的死结,便没人再敢吭声了。
局面僵持着,除且蛰外,所有的人都在等待太子的态度,而冒顿依然是那副模样。
头曼终于打开窗户说亮话:“我的儿子里,已经成年的冒顿太子当然很重要,可他不去当人质,难道要让只才几岁的芷劬去当人质,众位长辈和兄长于心何忍!退一步说,就算本单于愿意送小儿子去,或者换了别的儿子去,月氏难道不觉得匈奴在蔑视他们吗?那不正是激怒了他们吗?”稍停,他又说:“也许,我的小儿子一旦抵达月氏,月氏王和大臣们会觉得是一种羞辱,羞辱了就要愤怒,愤怒了就要像屠宰一只小羊羔一样地杀死我那小王子。那么,匈奴就必须复仇,最终战争更是无法避免,这有什么益处呢?大伙儿想想,我们不是还有更多更大的事情要做吗?反攻秦朝需要腾出双手,而不仅仅是一只手,这双手咋样才能腾出来呢?”
头曼此时纵有千般理由,在场的官员也无法一致地赞同。但金帐的讲坛最终是属于单于的,他有绝对的权力,就有绝对的道理,没人能奢望改变他的意志。
且蛰得空去一一观察帐中的将领们,竟都闪避着,没有人敢与自己对视。他眼里射出利刃般的光芒,咬牙说:“我新近侦得,中原盗贼声势浩大,主力已经攻入函谷关。尽管结局未能知晓,但我只要不去惹秦朝的二世皇帝,谅他也无暇找我大匈奴的麻烦。也罢,请大单于先把河水边上那块肥美的羊尾巴油晾着,小王情愿押上这颗脑袋,带领人马有进无退,不日必将月氏王的头颅奉献于帐前,用它来为大单于敬酒。请大单于安心在余吾水等候佳音,太子也自小心提防东胡就是了!”
头曼愤怒了,睁开了狼一般的眼睛逼视,一直到且蛰低下头去。随即转向冒顿,问道:“太子呢,你还没说话呢,难道你的想法也与右屠耆王一样吗?”
一直沉默着的冒顿脑中如被板油凝滞,无论如何也弄不清父亲到底是什么用意,但也没有任何选择余地。等头曼问到自己,便下意识挺了一下身板,高声回话:“感谢右屠耆王和各位长辈、兄弟为我担忧,我必须听从阿爸大单于的派遣,即使献出生命,也理所应当。我是太子,大匈奴如若需要,我不赴汤蹈火,谁赴汤蹈火!”
“好,这才像我头曼的儿子,才不愧为大匈奴的太子!”头曼说着,朝帐外喝一声:“侥直那呢,侥直那在哪里?”
卫队长壮健麻利的身影立刻出现在帐前,大声说:“请大单于吩咐!”
头曼命令道:“你保护太子前往月氏,明日随同月氏使者一同出发,不得耽搁!”
侥直那领命:“是,明天保护冒顿太子出发。请大单于保重,也请大单于放心,末将在,则太子在,我将用生命保卫太子的安全!”
头曼用力点点头,起身走到侥直那面前,解下身上的佩刀,说:“本单于赐你这把佩刀,它已随我征战多年。相信你能不辱使命!”侥直那连忙单膝跪下,双手接了宝刀。
夜晚,草原上只有半个月亮,远山晦暗,近林幽冥,云扰光晕不可捉摸。
冒顿来到一条蜿蜒的小溪边,自小儿一起长大的伙伴从近旁的毡房那边走过来。冒顿下马,两个人牵了手,在一块光洁的鹅卵石上坐下来,相互偎依在一起。冒顿成人了,健壮勇武,是风雨不可动摇的山岳;女孩也已经长大,青春勃发,被月色笼罩着,朦胧中更显得楚楚动人。
溪水轻轻流动,在虫鸣的静谧中潺潺如同细碎的心声。没有语言,只有能感受到的异性温柔气息和心脏此起彼伏的跳动。积攒了一天的热气在草丛间上升,离开了阳光的夜晚把细微的寒意渗入草茎,给青春滴注点点的滋润与苦涩。
“做我的妻子吧,莶扶!”冒顿说,“假如你能承受我一去不回的伤痛!”
“好吧,这是我在心里想过了一千遍、一万遍的事情,愿祖先的灵魂保佑我心爱的人早日平安归来。”
“我十分爱你,但我不得不离开你,这就是草原上太子的人生。”
“我们可以不做太子,可是,你的确是太子,那我就是为太子去死也心甘情愿……”
冒顿拿手捂住了她的口:“不许你这么说!”
“那我用什么来表达我的爱呢?”
“现在就做我的妻子吧……”
云开了,月亮为情人扯开了皎洁的被。云聚了,给初夜一袭朦胧的柔美。沾满露珠的草甸是爱的坦陈,涌动的流水是甜蜜的誓言。
……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今夜的感受,是你,莶扶,让我懂得了草原上的男人所有的牵挂!”
“你让我成为了真正的女人,从此我的身心属于了你,一个有牵挂的男人必定能成为草原上跑得最快的骏马,飞得最高的雄鹰。我将日夜不停地为你祈祷!”
夜甜蜜而又酸楚,漫长而又短暂,当晨曦前来驱逐草原的夜和梦时,侥直那与月氏的使者、副使一起,远远出现在溪水流过去的地方。
阳光浅浅地浮过来,莶扶搂住冒顿不肯放开,泪水顺着脸颊流淌,沾湿了爱人的脖颈。冒顿轻轻地扯拉那两只用力绞结在一起的无力的手臂,站起身来,头也不回,走向自己的坐骑。
小王子芷劬梦见了单骑孤影远去了的大哥。辽歌大声地吵吵:“大哥,你去哪,大哥,你去哪?”
正在梳洗的夷莪连忙去看儿子,他正在说梦话呢。辽歌又在学舌,被夷莪用梳子打过去,立刻闭了嘴。
早起,且蛰就带着卫士们上路,要赶在冒顿前面回自己的驻地去。右屠耆王大帐座落在从燕然山南流的匈奴河畔,那一带本是匈奴势力的核心区域,单于庭旧地,后因势力衰弱并遭到秦国的威胁而向东北迁移到更远一些的姑衍山南。且蛰本应先向西再往南,惬意地走那条异常熟悉的草原之路,享受山间的水草和温馨。但他选择了直接向南逐渐有些偏西的路线。
顺姑衍山而下,行二、三百里便脱离山地草原,进入了高原的中心位置。这里是东、西部大山和南部阴山大幕的延伸交汇地带。东北部水量充沛的河流只管反向地流走;西部的水系从高高山岭上发源,飞快地倾泻到山下的草原,向北,向南、向西,毫无例外地遗弃了这片宽广的相对低地,任由其中分布着的许多浅显的洼地苦涩地干涸。
没有大山和深涧阻隔的大幕西缘台地上下,高高低低直直弯弯,到处都是若隐若现的道路。路有大有小,大的路带动小路通向更远的地方,就像大河汇集小河一样。
处处可见裸露的垄岗,满目荒凉。风暴经年累月地雕琢这里的地貌,亘古洪水冲刷遗留了极度夸张的创伤裂痕。稀疏难寻的荒漠植被,依照自然地理的残酷选择性作有限渲染,与大片的沙碛交织铺陈,贫瘠地描摹出高原腹心的底色。沿途能遇到水的残留和渗出,以及微小河沟的点滴滋养、微量降雨吝啬的恩赐。
且蛰接过卫士递过来的羊皮水囊,仰头喝上几口,递了回去。立马回望高远处的北方,那里河流汇集处,有鲜花和绿草点缀的蓝色北海。可是,他的目标是南面,只有耕地种植业发达的秦地能给予匈奴族群取之不尽的稳定给养和财富,北部森林草原的供给链则十分脆弱。
在白天的炎热和夜晚的寒冷中,又艰难地走过了三、四百里,沼泽和植被逐渐增多起来,显然是靠近蒲奴水西侧了。
一天过后,地势缓缓上升,山多起来,大概再行一、二百里,就到达夫羊句山狭了,且蛰打算在那里迎候冒顿。
夫羊句山狭位于涿邪山末梢。这里东接习惯称为“大幕”的两千里大漠,东南跨流沙、大幕交接地带与阴山西端的阳山遥相呼应。向西南穿过鞮汗山的谷地,就可以进入居延湿地了。流沙是中国古代对巴丹吉林沙漠、乌兰布和沙漠、腾格里沙漠的统称;居延泽的东、西两个湖泊,都是来自河西走廊的黑河的尾闾。黑河出酒泉东北山口流入半荒漠、荒漠地带,当时称为弱水。
随后到来的太子兼人质冒顿,将要顺着弱水进入那个北山的山口,就此把命运交到宿敌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