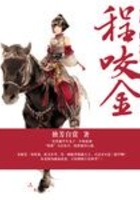一旁的师爷听着直皱眉:你现在光骂顶个屁用,赶紧想办法取回来啊,如此大声嚷嚷,传到上司耳朵里,官帽都得丢了。
师爷等秦德元骂的差不多了,在一旁劝道:“老爷,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咱们得先把大印赎回来,时间长了,容易生变。”
秦德元想想也是,此时不是生气的时候,命人将当票取下来,可这当票和昨天一样,粘的异常牢靠,手下人忙活了半天也没取下来,
师爷早料到会这样,吩咐道:“算了,别抠了。”随即向后一挥手,叫来何云和闫杰,让他俩将门卸下来。
两人极不情愿的来到书房前,心中暗暗抱怨:还来啊,我俩怎么说也算是抓差办案的,怎么改成出苦力的了。
县衙里,除了县令,就属师爷地位高,两人不敢违抗,轻车熟路的将门卸下来,一前一后的抬着门板往当铺走,一路上两人再次不断埋怨。
“怎么又是咱俩,昨天累的腰疼胳膊酸的,今个就不能换个人。”何云嘟囔道。
“县衙里就六名差人,除了正负班头,另外二位都快五十了,咱俩年纪轻轻的,咱不来谁来。”闫杰没好气道。
“也不知谁这么缺德,将当票贴在了书房门板上,害得大爷我天天出苦力。”
“你知足吧,这要是贴在了县衙的铁门上,累死咱俩也抬不动……”
这回县令特意写了一张文书,让何云、闫杰带给广盈当铺的掌柜,大意是以后再敢乱收东西,小心他的狗头。
何云和闫杰将县令的官印取回来后,秦德元看着两名衙役抬着的木门中间醒目的两块补丁,是欲哭无泪:这是哪个混蛋王八蛋,害的本官破财损物,等我抓到你必将棍棒伺候,然后押入大牢。
秦德元就这样憋着一肚子气,晚饭也没吃就上床睡觉了,一觉醒来,准备穿衣服的时候,发现昨晚放在枕边的衣服全都不见了,开始以为是掉在床下了,穿着短裤光着膀子在屋里找了一圈也没有,只好用被子裹住身体,喊来差人问有没有人进自己的房间,衙役看秦德元用被裹着身体,一大清早就气势汹汹的,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都说自己没有进过大人房间,秦德元气的火冒三丈:“真他娘的见鬼了,前天钥匙丢了,昨天大印没了,今天衣服又没了,还愣着干什么,出去给我找啊。”
秦德元抬手往外轰衙役,双手本来攥着裹在身上的被子,这一挥手,身上裹的被一下掉了下来,碰巧把穿的短裤也给带了下来,秦德元就这样一丝不挂的站在众人面前,众人一下都傻了眼,全都愣在那里。
秦德元低头一看,羞得满脸通红,立刻蹲下来,用被将自己整个蒙住,在里面大声喝骂道:“全都给我滚出去找衣服。”
大家憋住笑去找衣服,这回众人学聪明了,争先恐后的直奔书房,到了一看,果然没错,在房门的最上面又贴了一张当票。
时于德元穿着便装正在屋里骂:“真他娘的是一群饭桶,一个个养的肥头大耳的,全都是猪脑子,连点东西都看不住,我明明嘱咐要多加小心……”
秦德元正骂着,有人回禀说在书房的门上又发现了一张当票。
秦德元一听脸都气绿了,来到书房一看,真是欲哭无泪:这是哪个挨千刀的,敢和本官如此玩笑,我迟早要抓住这个刁民,处以大刑……
秦德元看着门上的当票,冲着身旁的何云和闫杰呵斥道:“别一个个像木头似的,去把门给我卸下来,把本官的衣服换回来,这回门也不用补了,直接丢给当铺就得了。”
二人一听心中直打鼓:他娘的就不能有点新意,这几天光抬门了,差点没累死,怎么今天还来啊。但又不敢违抗,只好愁眉苦脸的又抬着门去当铺了。
路上,何云埋怨道:“我算是看明白了,这贼不是跟老爷过不去,是和咱俩过不去,他打算活活把咱哥俩累死。”
闫杰喘着粗气道:“我已经想好了,一会儿回去就跟老爷告假,明天说什么也不抬这门了。”
“你要告假,我也跟着,这天天累傻小子呢。”何云有气无力道。
两人就这样一路埋怨着往当铺走。
这回换了一家当铺,因为赵飞前两次去的那家当铺关门了,只好另换一家。
这家当铺的掌柜一看有人抬着房门进来,后面还跟着县衙的班头,不敢怠慢,赶忙从柜台里出来,问明了原因,十分惊讶道:“几位差爷何苦这么费事,直接把当票揭下来不就可以了。”
班头冷笑一声:“你没看上面有两个补丁吗,前两次就是因为取不下来,所以才将门板给锯下一块的。”
“是吗?”掌柜有些不信,俯下身子,将当票的一角抠起,轻轻一拉,当票很轻松的下来了。
班头看着取下的当票,惊讶的瞠目结舌,前两次因为都是粘的异常牢靠,所以这次秦德元想都没想,就直接命人把房门给卸了下来,大家的想法也是如此,谁都没去碰当票。
抬门的何云和闫杰看如此容易就能取下当票,肠子都悔青了,不停的跺脚:早知道这样,何苦这么费事抬门过来,差点没被累死。
这几天,长岭县的县令秦德元是坐立不安,时刻堤防着再次丢东西,睡觉的时候将一切值钱的东西全都抱在怀里,又命衙役轮流在自己卧室前巡逻,担惊受怕的过了几天,刚刚庆幸终于不丢东西了,可县里又开始谣言四起,说县衙风水不好,不祥之地,含沙射影县衙内部有问题。
流言传来传去就传到秦德元耳朵里,秦德元是火冒三丈,右眼皮不自觉的跳了几下,发现最近有些时运不济,先是连续丢东西,现在又谣言四起,这不用猜,用屁股想都能知道——肯定有人在背后捣鬼,遂就命手下人追查谣言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