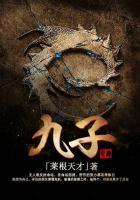突然间,一截嵌在污泥中的枯樟枝动了,分叉的枯枝颤颤微微的好似随风摇动,枝干中好像慢慢的长出了一根粗粗白白的...是手指!牧牧心中惊骇莫名,庸叔叔居然在自己身边呆了这么久,自己居然一点都感受不到他的气息,甚至连一点心机暗潮都没有,这是什么藏匿秘术?“走!”拂面一阵晚风吹来,盖在了伏在杂草堆里牧牧的身上,牧牧突然感觉全身冷嗖嗖的,元海差点都轮转息停。“不要慌!这是蟾襟衣!你放松全身,我带你走!”
邻东有蟾故名玥襟,形如秋蟹六肢,色作暗灰夹黄,肉质粗皮,唾可入药,皮乃无上品,有名蟾襟!
牧牧骤然记起了从前从青牛桌上,看到的灵物匾产篇里有这么一段描述。“这个就是能阻隔神念、气机探寻,掩盖自身的蟾襟衣?不是说钥襟已经捕绝了吗?”牧牧捻着身上比轻纱还薄的透明蟾襟,张着嘴惊讶的喃喃问道。
物以稀为贵!世上越是稀有的越是得不到的,世人就觉得越是珍贵,越是宝贵!就像是龙蝉,白革,青花,皿雾等等等等!一个物种的灭绝!缘起于世人无知无尽的索取!而这种无知无尽的索取来源,或许就是自古以来的攀比、炫耀!也就是说,世人因为虚荣或是需求导致了一个个物种的灭绝!或者有人可以辩解:适者生存,逆者淘汰!
沉这个脸的庸长心搂着牧牧施展分行厚土之法,沿着羊肠小道路边缓缓遁地而行:经过天牢宿卫暗中安排,自己分派袍卫从天牢中接出了牧牧后,袍卫引开了追迹宿卫,牧牧经桐茶道扮分差小厮尽量避走,到了岩石关下经凤宗离卫亲信安排出关,到达木金石崖碰自己亲手安排的副统卫,两人一路一前一后奔至早就约定好的孤肠道,副统卫尽量断后拖延追迹宿卫,自己先前布下的藏匿术阵才可发动遮掩、屏蔽牧牧外泄气机、神念,以及已经准备好的踪迹气息归引追迹宿卫另追他途。
“叔叔!那黑衣人没有什么事吧?”一脸紧张的牧牧偎依庸长心身后,抬头望着一脸肃容的庸长心,想着刚才那个随风化作尘埃的黑色人影。“受伤是难免的!撑的住就好!”沉着脸的庸长心一边掐诀遁行,一边观察着周围的情况,想起了刚才自己的老部下,轻轻的咧嘴说道。“那些宿卫都是谁?”牧牧想着黑色人影也记起了刚才那个凤袍中年人。
“叫卫老的是百年前龙屏关血战归来的老人,因为受伤缘故所以一直清任宿卫总统领闲差,他的儿子就是执法堂执法长老之一的卫河山。凤袍中年人是执法堂宿卫主事,功力精纯可惜是散修出身,更是因为脾气耿直得罪了人,一直不得晋升。所以,他刚才不愿多事才能放过老丘一马,老丘才能从容尘遁,不然凭借他的凤尾镜老丘怎么能跑的了呢。”庸长心手掐玄诀,思量一会,慢慢的向牧牧述说刚才的厉害关系:“再说!他也不敢亲手留下老丘的!”
“为什么?”牧牧睁着清澈眼睛,望着搂着自己的庸长心。“你啊!现在不要管这些乌七八糟的,要记住心智有碍修为!你是天生灵体,要在仙道上多下工夫,这样才能不被世俗所困,不为名利所累。”庸长心低下头语重心长的告诫牧牧。“还不是你挖的坑让我跳的...。”牧牧听着庸长心的告诫,撅了一下嘴,嘴里不清不楚的嘟喃着,斜着眼睛又生怕庸长心听到。
“等下过了孤肠道,我们去荔屋的禅心崖等些日子,然后我带你东去春礁岛!”沉着脸的庸长心看着牧牧一个人嘟喃的自言自语,也不去管他,一边说着自己的打算,一边掐诀施展分行厚土之法:“恩!”一声惊疑从庸长心的鼻子哼出:“他怎么在这里?”牧牧一惊!抬头朝前面看去,灰蒙蒙的什么也看不清楚,也不知道庸叔叔说的他是谁。
“长心!聊两句!”望着显出身形一脸不解望着自己的庸长心,赵彬子苦笑的朝庸长心摆了摆手,右手一张做了一个请势。“怎么回事?”庸长心望着眼前的老上司一脸欲说还休,慢慢的沉下脸来,原地一动不动哑着嗓子问道。“长心!把孩子交给我吧!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我就当没有发生过。”一道淡淡的声音无声无息的从身后响起,庸长心绷着肃脸艰难的缓缓回头,笑容满面的一个孤人就那么不清不楚的站在那里,脚穿老旧的凤棉布靴,双手背于身后,眯着眼睛微笑看着绷着肃脸缓缓回头的庸长心。
“怎么回事?”庸长心此时肃脸绷紧,一下子重新回头望着眼前自己的老上司,咬着牙因气急而颤抖的提高声音,厉声朝赵彬子重又问了这么一句。“不用为难小赵了!我的主意!”一脸为难的赵彬子望着,这个生死之交数百年的老哥们气急质问,一时也非常的为难,微微抬了抬手刚刚张嘴要出声,对面那个笑容满面的一个孤人就已经帮赵彬子解了围。
庸长心绷着脸慢慢向后转身,重新面对着那么一个笑容满面的孤人,低着头哑着声音措着词:“不是这样的啊!您怎么来了?”“孩子!交给我!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我就当没有发生过。”笑容满面的一个孤人微笑的重新又说了一遍,丝毫没有因为庸长心的忤逆,而动一丝一毫的怒气。绷着脸的庸长心很为难!非常为难!计划不是这样子的啊!当初不是这样说的啊!
“为什么?”庸长心没有没有正面回答,反而问了一句本不该在他这个年纪问的话。“你啊!私劫大牢!私纵天囚!可知何罪啊!你知道因为这件事会有多少人掉脑袋吗?家族会有多少人因为这件事而受诛连啊!老大不小了做事情还这么的没轻没重不知分寸!”笑容满面的一个孤人,淡淡的望着低着头的庸长心,毫无烟火气的教训着。
时间缓过,针灸人心!过一半响,微缓脸色的庸长心慢慢的抬起头来,平视着面前的家族柱石:“我不能把孩子交给您!”“那么你是要跟我火并咯?”笑容满面的一个孤人微微一笑,倾了一下头,饶有兴趣的眯眼望着不远处的庸长心。
“唉呀呀!老爷子说的什么话啊!就是给长心十个胆子!他也万万不敢跟老爷子对着干啊!长心啊!你也真是的!怎么能跟老爷子这么说话呢!老爷子啊!长心你也知道的啊!他这个小子啊就是倔牛一头!您大人大量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啊!”一听快要谈崩了,就要马上动手了,身为庸长心的好兄弟赵彬子,赶忙急轰轰的跑到庸长心面前,用力的顶了一下庸长心的肩膀,递了一个安静点的眼色给庸长心,转身朝笑容满面的一个孤人点头哈腰拼命说项。
弟兄嘛!不是暗里给你捅刀子,就是明面给你挡刀子!笑容满面的一个孤人微微一笑!却没有看挡在庸长心面前的赵彬子,眼神穿过了急忙劝项的赵彬子,直微笑的望着自己从小看大的庸长心:“我不说你应该都可以明白!孩子长大了应该有自己的选择!也应该有自己的主意!我啊!就不说你什么了!我就问问这个孩子的意思!”“不行!”一脸肃容的庸长心抬着头断然拒绝:宗门的手段他是知道的!肃着脸的庸长心回想这些天发生的事情突然间意识到!为什么当初宗门要发数封急送给自己?为什么偏偏是自己安排这些事情?是因为自己身在执法堂的便利?还是因为自己的性格?原来他们早就安排好了啊!宗门真的是择人善用啊!
笑容满面的一个孤人看着敢抬着头直视自己的庸长心,轻轻的点了点头,右手一挥右臂上布袍抖然一卷,站于赵彬子身后的庸长心顿时直震的翻出了十余丈外,落地应声凝气掐诀中一口血不可抑止的吐了出来。“叔叔!”一声稚嫩的声音促然响起,一道清瘦的身影从不远处的地里蹿出,身形急遁下扑向了咳血躬身的庸长心身畔,扶住了气血震荡的庸长心,紧张的一张俊脸望着痛苦的庸长心。
同一时间!
赵彬子脸色大变骇然回头,望着身后十余丈外被老爷子凤鸣罡风震的躬身吐血的庸长心,连忙冲上前去扣住了庸长心的手脉,防止庸长心急嗔一起止手不及徒增大祸,转过头撑开肩膀挡住了身后的庸长心,望着十多丈前已经冷下脸来的一个孤人,颤声说道:“老爷子!手下千万留情啊!长心千错万错可都是您的孙儿啊!”冷下脸来的一个孤人,望着赵彬子身后一脸紧张扶着庸长心的少年,嘴角轻轻一提,看也没有看护着庸长心的赵彬子,只是微微一笑的对着扶着庸长心的少年说道:“你就是那个凤宗的小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