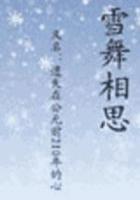风果然入夜就停了。院子里积了一层砂砾,安雅院中只有三个仆人,扫了好久才干净,院子里的花草算是毁了,必须得重新栽上新的。安雅叫佩儿出去转了一圈探了下各院的风声。碎叶城仅存的几百亩耕地损失惨重,安玉郎已经带着几人去看情况了;南苑羽氏和安琳闭门不出,父亲安如智已去往客舍拜访特使,尚未回府。
看来大家都忙碌得很呢。安雅闲闲地翻着史册,不由得想到自己初到碎叶时的场景。她很难想象当时惊慌失措的自己现在居然如此淡然地窝在厢房内据卷夜读,仿佛自幼就生活在这里一般熟悉。她已经记不得现世的日期,如果不是意外穿越,现在大约已经开学,开始美好的大学生活了吧?安雅喜欢这里,但内心中总存着万一的幻想,有一天一切都回到正轨,她还是那个朝气蓬勃的大学生,而不是现在这个年仅十五就要步步为营的安大小姐。
说起来她自己也许久没有时间坐下来这样天马行空的任由自己的思维乱飘了。想起来这段时间几乎没有见到羽氏和安琳,也有点纳闷。本来她已经做好了和这对母女针锋相对的准备,但这些日子她们却像避着她一般,一点也没有来烦她。或许是安玉郎做了什么吧?安雅想来想去,会来管她们三人之间恩怨的也就安玉郎一人了。
卫衡他们已经确认了离城日期,一个月之后八月初一。安雅又开始安玉郎给她安排的充实人生,每天累成狗。什么卫衡,安琳,安夫人,她统统没时间去想,每天满脑袋的拔刀术,账册,公函,史书,忙得像高考前夕一样。安玉郎虽然看起来温和可亲,在正事上却意外地严厉。其他的还好,读书是她的老本行,难不倒她。只有刀术一项,她从未学过,进展很慢,因此经常挨骂。
安玉郎自己用一把大漠男子常用的圆月弯刀,刀身不算轻,但他拔刀时却轻灵诡谲得像蝴蝶展翅一般。那把红牙在安玉郎手中更是快绝人寰,刀鞘收在袖中,刀出鞘时只能看到红色的一线,她看清楚时刀尖已经不偏不倚地指在木人偶的下颚,一个呼吸的时间,他就可以刺遍人身上所有的要害——眼睛,咽喉,心脏,腹部,手腕,小臂与大腿。而他要她学的,也是这样精妙的刺杀之术。
一月之期很快过去大半,她已经把冰锥式,铁锤式,蜂针式,藏锋式四种持刀方式都学了一遍,虽不如安玉郎快,但瞬间刺中木人偶其中一个要害是可以做到的。
到了实战的时候,安玉郎亲自做她的目标。安雅自认为练得不错,但无论她往哪里刺,安玉郎的折扇都早就等在那里里,象牙扇骨轻轻一格,她原本凌厉的攻势就失去了方向。
“蠢材!这样的刺杀术是在开玩笑吗?对手早就看破了你的刀路,不能一击得手死的就是你!”安玉郎大声呵斥。安雅咬着唇收回匕首,手腕已经隐隐发酸。安玉郎不满意地继续吼她:“左手掩护,右手拔刀,眼睛盯着目标,你左手是残废的?匕首刀刃短小,你这样力量的刺击怎能做到一击必杀?重来!”
安雅沉下腰,掌心向后以藏锋式握住匕首。方才她在左手中抓了一把沙土,此时趁安玉郎不备,她扬起沙子挥向安玉郎的眼睛,安玉郎不料她会有这一招,右手折扇打开,挡住了沙子,却阻隔了自己的视线。就是这个机会!她右手一翻,转为铁锤式,妖异的红光一闪,直冲安玉郎咽喉而去。电光火石间,她只觉得手腕一酸,已被安玉郎左手握住,匕首尖堪堪停在他咽喉前一寸之处。
还是失败了。安雅心中满是挫败。她等着安玉郎数落她,对方却松开她的手,轻轻赞了一声:“好。”
“不是又被你挡住了吗?”安雅郁闷地说,“好什么好,我自己都觉得自己笨。”
“不,如果你真起了杀意,刀还会更快一些。”安玉郎摇着折扇,总算是给了她一点笑容,“刚刚的沙子用得不错,近战时懂得利用周围的东西给自己制造机会,很好。”
这么多天难得得到他一句肯定,安雅不由得有些高兴。“我昨晚上回去也练了一会儿,手感比昨天又好些了。”
“高兴得太早了,你以为绝世杀手这么好练?要练到不用想,身体自然就能做出反应,才算是略有小成。”安玉郎又给她泼冷水。
“我又不想当绝世高手,能保命就行了呗……”安雅不服气,小声嘀咕。兄妹俩你一言我一句地拌着嘴,却被院门外一阵喧哗给打断了。
“我不管,放我进去见大哥!我要见大哥!”略带稚嫩的女声带着哭腔在院外高声嚷嚷,周围似是有仆妇在劝,女声声音拔高了几度,怒气横生:“贱婢,竟敢拦着本小姐,给我滚开!”外面传来打骂声和求饶声,安雅感觉自己的脑袋隐隐作痛,消停了许久的安二小姐,还是这么跋扈的性子啊。
“大少爷,是二小姐来了……”安玉郎的贴身侍女染香上前回禀,面露难色,“之前二小姐求见过很多次,少爷都不见,今天她怕是不见到您绝不罢休了。”安玉郎皱着眉头,十分不悦。安雅做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并不看安玉郎主仆,只是把玩着手中的红牙。安玉郎见安雅神色如常,沉吟了一下,淡然道,“那就请二小姐进来吧。”
不多时,染香就引了安琳前来。安雅许久不见安琳,发现她竟憔悴许多,一双妩媚飞扬的杏眼哭得核桃般红肿,衣服也不见了往日的光鲜亮丽,平日里牛奶般白里透红的皮肤也灰暗了下来,蜡黄蜡黄的,像是许久没有吃好休息好了。安琳见安雅若无其事地与安玉郎坐在胡杨树边的石凳上,眼中闪过一丝怨恨,好容易忍住了没有出口辱骂,只委委屈屈地给安玉郎行了个礼,叫了一声“大哥”,眼泪就又滚落下来,无论怎样都忍不住,竟呜呜地哭了起来。
“这么大的姑娘了,怎么还小孩子似的?”安玉郎无奈地用帕子给安琳擦眼泪。安琳可怜巴巴地捉着安玉郎的袖子,带着哭腔哑声说:“大哥,你救救琳儿,琳儿不想去东华国,琳儿不想入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