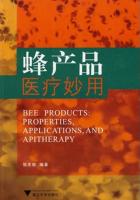刚刚看过电视,SH市一个姓鲍的学者讲《水浒传》书中的人物。这人讲得很细,很好。这本书我很久以前就看过,可没想这么多,看过热闹后就扔一边了,听他这么一讲,我才觉得这书有看头。躺在沙发上,闭着眼睛仔细一想,宋江怎么会有“及时雨”的绰号呢?送到旱田里的雨才是及时雨,送到“江”里的雨有什么用呢?像元朝人说的“这雨呵,又不是救旱苗,润枯草,洒开花萼”。排座次的时候,他怎么又叫呼保义了呢?李逵一定是“理亏”的谐音,世上会有李逵头脑这么简单的人吗!我没见过。林冲一定是从“林”中“冲”出的大鸟。在作者眼里,体制内是树林,宜于鸟类生存。林冲原本在林中生活得很好,不想发生了意外,被主流社会迫害,不得已才奋翅“冲”出“林子”,落草为寇,对抗主流社会。吴用呢,智多星怎么会“无用”呢?我真想不明白。
我忽然觉得,看小说就如同在打开大院的门。看好的小说,比如《红楼梦》,就像是在打开BJ故宫的大门,打开一道门,还有一道门,每道门里边还有很多边门、角门。这些门有的敞开着,能直视到深处,有的门虚掩着,需要读者用智慧推开。推开的门越多,对小说理解得越全面、越具体。《红楼梦》一书中,门多到了让读者数不过来的程度,所以,需要几代学者去研究、琢磨,帮我们看到那些半开半关的门后面是什么。因为研究方法、认知水平、探究程度的不同,不同的人看到的景象也不同。我以为作者设计的门太多了,多到了连他自己也顾不过来的地步,比如第七回“送宫花贾琏戏熙凤”,我就没找到“戏熙凤”的内容。还有“芙蓉女儿诔”中著名的那句话“毁诐奴之口,讨岂从宽,剖悍妇之心,忿犹未释”。谁是悍妇?我看过很多研究《红楼梦》的书,没有人能说清楚谁是悍妇。王蒙先生干脆说,“我不知道。”舒芜先生认为这几句话可能是作者写《红楼梦》之前,为别的什么文章写的,写芙蓉诔的时候,就直接用上了。以曹雪芹的创作态度,会有这么大的疏漏吗!我以为不会。曹公一定是在写作的过程中,为他喜爱的女仆被害致死心怀不平,为了享一时的快感才这样骂人的,骂过之后,又舍不得删除,就用上了,给后代读书人留下了无尽的猜想。想一想可能很简单,这“诐奴”与“悍妇”是指同一个人,为了写作上的区别,才这样说的。
那些个一推开大门,就能将院内的景色一览无余的小说,属快餐类,适于浅层阅读人的习性。为消磨时光,看看热闹,填补一时的虚空也就完了,让他讲一讲读后的体会,他一定讲不出。未经心灵过滤的东西,印象一定不深。
我二十一岁那年第一次看《红楼梦》,很快就被书中的气氛吸引,看到第八十一回时,突然感到那气氛没有了。好像张爱玲也有这感觉,我这么说真不是受她的影响。四十岁以后,我又看《红楼梦》,还有那种感觉,《红楼梦》一定不是一个人写的,后部分差得多了。
《红楼梦》要深度阅读,才能次第打开那一道道大小不一、开合不一的大门、小门,进入生命与情感领域的至高境界。没有人能打开《红楼梦》一书中作者设下的所有的门,也不要试图全部打开,只有作者一个人知道他留的那扇门后有什么。
我也爱看《红楼梦》,贾家大院里的女人太美了,太值得琢磨了。林黛玉过于率真,韵味不够深幽,她在《葬花词》中说“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她才十三四岁,正是花朵初绽的时节,怎么会想到身后事呢?我快到五十岁时,才有此感。我还不能理解“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她是贾家的直系亲属,系贵族小姐,怎么会有“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感觉呢?还“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有此感,这感觉真实吗?耐人寻味的是薛宝钗,有人说她狡诈、有心机,我真没看出来。她几乎有着女性的所有优点,美丽、和善、通达、富有(她的缺点是没有缺点)。我时常想,以宝姐姐的修养,能看上不求上进,又“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的贾宝玉吗!
我弄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学者抛下自己的专业不干,********沉浸在大观园里,穷其一生研究《红楼梦》呢?不就是本小说吗?用得着下这么大力气吗!我闲着没事,到打折的书店买了几本研究《红楼梦》的书。看过之后,我才知道《红楼梦》一书的博大与深远。闭灯以后,躺在床上,还在想大观园里的人。我有些喜欢上了穿着“蜜合色的棉袄,玫瑰紫二色金银线的坎肩儿,葱黄绫子棉裙”。又“罕言寡语”,“安分随时”的薛家姑娘。宝姐姐的芳香长久地弥漫在我的魂间,有种恋爱般的感觉。这才忽然大悟,那些常年沉浸在大观园里的学者一定也是这样。他们在享受同那些美丽又有教养的妇人、姑娘在一起时的快感。那感觉是常人体会不到的,我称为甜蜜的凄凉;痛苦的温馨;愉快的惆怅。直是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
冰心先生就说自己看不进去《红楼梦》,她是女人,她体会不到那份快感。那快感是男人体悟到了之后,用心写给男人看的,因为文笔精湛,诗意盎然,而耐人寻味。作者知道有人看不懂,才说“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贾宝玉为什么不喜欢几无瑕疵的宝姐姐与花袭人,却喜欢毛病很多的黛玉、晴雯呢?有一天,我问黄秋丛。他回答说,“因为宝姐姐、花袭人没有黛玉、晴雯真诚。黛玉、晴雯一个是宝玉至爱的恋人,一个是最好的朋友,她们被关爱自己的奶奶、母亲害死了,悲天悯人的贾宝玉掩面救不得,这才愤而出走。”
伟大的曹雪芹一定深爱着林黛玉、薛宝钗。在他眼里一个是“金”,一个是“玉”,哪个也割舍不下。他用尽心血,写下了这一让后代读书人永远也说不完、道不尽的“悲金悼玉的《红楼梦》”。
我曾试图走进林黛玉与薛宝钗的内心世界,写一篇关于林薛精神领域的论文,评职称的时候用得上。
我四十岁生日那天,请几个同学小饮,席间我说了这想法。蚊子说:“还有时间研究那东西?有几个人爱看。”我告诉他是为了评职称凑个数。
于溪存说:“这种论文好写,写好写不好也没有个标准,看上去顺溜就行。”他想了想又说:“要写好这两个人,一是看她们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还要看她们说话做事时身边还有什么人,这是个细活。”
黄秋丛说:“这两个人你写不好,她们的精神世界同她们的相貌、家世关系很大。那些个从未美丽过的人是不会走进林黛玉、薛宝钗两个大美人的精神世界的。”
他是说我不是美人,不会真正了解美人,我虽然不爱听,也知道有道理。
读书时,班上的女同学欧水融就是我心中的薛宝钗。现在欧水融五十岁了,玫瑰绽放后的痕迹还清新可见。认识她以后的二十多年间,我每次在书上看到薛宝钗的名字,就会不自觉地联想到欧水融。读书时的欧水融不但人长得好,性情也温婉,对谁都很和气。她美到了我不敢动心的程度,她是油画上的女人,“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我看到她看黄秋丛时那意味深长的目光了。黄秋丛与于溪存是班里两个美男子,我觉得黄秋丛更有味道。一个美貌又有味道的美人才是真美人,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高度统一。
我了解黄秋丛,尽管他刻意隐瞒自己的心思,我还是能够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他燥动不安的心。他人长得好,家境也过得去。我看到他的眼睛时常不自觉地看欧水融、莫扶荷。
我那时觉得李锦下与莫扶荷最可靠,告诉黄秋丛找老婆就应该找她们那样的人。女人长得太漂亮,就成了扼守要道的高地,在后援不足的情况下抢占高地,容易失守。具体点说双方都在透支未来。
他不听我的话,自以为风流倜傥就一定会有好结果,一心一意要找个品貌出众的人。他那时总是穿着上下几乎一样粗细的水桶一样的长裤子,头发和蚊子一样,一看就是精心梳理过的。他告诉我,买不起电梳子,就把家里的炉钩子烧热了烫头发(那时候,家里做饭、取暖要生炉子,炉钩子是钩煤灰用的)。他走路时,双膀不自然地晃着。我对他说,“别晃了,都什么岁数了?”他听了,瞪着眼睛厉声说:“我能改过来吗!”
他好像娶谁都不在话下,他个性太强,不大注重别人的情感,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他被宠坏了。
我可没有幻想,主要是不敢有,不能有。我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整个家族没有一个当干部的,长相又过于大众,没有一样能拿得出手的硬件。我虽然看好了班里的几个女同学,可不敢行动,怕被人家拒绝自取其辱。从这些女同学看我的眼神里,我就知道没戏,她们不是我能享用的,连花可陶都不用正眼看我。我告诫自己不要对她们动心,免受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