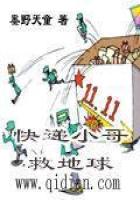春节的前两天,纪委全体同仁在会议室开联欢会,能唱能跳的都窜上台展示风采。书记和几个常委(纪委常委)满面春风地进来了,我知道他们这是做做样子,不会真感兴趣的,坐一会就会借故或一声不响地走开。年终岁尾领导还有更重要的工作。我知道这屋子里的人没有谁敢让书记唱一曲,还会因为他的存在感到紧张。
我想让场面缓和一下,就给书记写了张纸条,让他为大家唱一段。我看到他看那张纸条时的表情了,先是微笑了一下,又有些无奈地摇了一下头。我心想他要是不理我,站起来就走,我就当众叫住他,让他给大家唱一段,看他怎么收场。他没有走,且很大方地站了起来,读了我的纸条,然后说我唱歌五音不全,很难听,但是老白让我唱,我就给大家唱一段。他走上前台,拿过话筒,大声地、坦然地唱了一段《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他唱得不算好,可也绝不难听,我知道他一定唱过很多遍这首歌。”
“你什么时候当上科长的?”我问他。
“四十六岁,当时我差不多是纪委年龄最大的副科长了,排队也该轮到我了。”他回答说。
在机关里当小干部,比如科级排队就行,当大干部要看运气,没有人相信人品与才干,重要的是要跟对人。
领导可不好巴结,万不要以为送点礼就能得到关照,人家要不要还是回事呢!你永远也猜不透领导心里想什么。
我大学毕业那年,为了能进机关工作,父亲让我找他的一个正在局长岗位上的老朋友帮忙。我小的时候就认识那人,叫他穆叔叔,我原以为他会很热情地接待我这个晚辈。
那是个秋天的傍晚,妈妈让我提上一兜水果,我很坦然地敲开了穆家的房门。穆叔听完我的来意以后,一声没吱,面无表情地打开电视机,和家人一道看上了电视连续剧。全家人一起看了两集电视剧,谁也没理我,好像没这个人。
读书的时候,老师讲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老师说,万不可学他,他可不是文人的榜样,他不当官了,只能回家种地,他只会读书不会种地。他说“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他早起晚归在地里干活,结果是草比苗长得好。他吃饭都成了问题,经常要饭吃。唐代诗人王维说他“一惭之不忍,屡乞而多惭”。他一时兴起,没能忍住“一惭”,辞官不做,造成日后“屡乞多惭”的惨状。我想起了那一课,告诫自己不要一时兴起,站起来就走,不要走陶先辈的路,那是条死路。
直到他们看完了电视剧,要休息了,我那位穆叔才对我冷冷地说了句:“我知道了,你走吧。”
现在想来,如果那天晚上,我不是如乌龟般地蜷缩在沙发的一角,陪他们看完两集电视剧,而是愤怒地站起来走开,今天我可能和刘云一样早就失业了。我庆幸那天晚上忍住了“一惭”。
老白的故事在市委大楼里流传,人们在讲述这些故事的时候,讲者和听者都现出了惊奇的神色。像似在讲、在听一段古老的传奇。
市委大楼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楼里的人都自觉遵守。********如果在电梯里(升降式的),别人就不上去,等下趟或上另一部电梯。如果谁上电梯时,没注意到********在电梯里,低头向里走,书记秘书(他的岗位在电梯口)会礼貌地伸出手拦你一下,提示你回避。
老白上电梯时,从不看电梯里有什么人,有一次书记秘书试图阻拦他,********看到了,赶忙说:“别拦他,让他上来。”
《史记》上说,“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被老白没深没浅地戗几句,可不值呀!
中国历史悠久,供借鉴的成功与失败的故事太多了。这些故事成了前进的负担。不要对年轻人说生活有多复杂,告诉他们其实很简单。
我对老白充满敬意。人如果不能弯下腰,实实在在当孙子,还不如挺起胸,显男儿本色。
我原本不相信这世上还有没被污染的灵魂,我真不明白,老白这么做是真情的自然流露,还是要以这种另类的方式为自己赢得尊严?
冷静的时候,我想老白用这样简单直白的方式解决问题,面上的问题好像解决了,实际上问题一定埋下了,哪个领导能真心欣赏他呢!我敢肯定的是,在这个连领导座位与出场次序都要按等级排列的世界上,老白身为游戏中人,不守游戏规则,注定要被清除游戏队伍。他是不会为什么事请客、送礼的。他活在自己的意念中,不矫情,不做作。看似坦荡、洒脱,实际上他很孤独。
我知道率真的可贵,也知道忍一时风平浪静的道理,永远仰着头走路,不低头看脚下,怎么行哪!
《红楼梦》的开篇讲一个甄(真)家,一个贾(假)家。甄家遭了灾,结局很惨。贾家依旧繁荣(虚假繁荣也是繁荣)。为什么真不如假呢?作者为什么要这么写呢?他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散卖的商品一旦放进了包装盒,价格就会上涨。包装不是伪装,是提升品味。文化就应该是人的包装盒。
如果《红楼梦》一书,代表了中国文学作品的最高成就,那么书中的人物性格与命运就应该极具中国特色,有警示意义。
薛宝钗与花袭人是天性与世俗社会完美结合的一对,这种人物的最终结局就算不好,也不会太坏。
黛玉与晴雯是书中另一对有着率真性格的组合,这对率真组合没有善终,年龄很小就都归了天。
可见率真性格是不能容于世的。曹雪芹前辈在告诉我们,人要与世俗妥协才有出路,姑娘过于率真是危险的(他没写男人率真会怎么样)。
同老白接触时间长了,也就慢慢的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他的影响,每当我遇到闷心事的时候,一想到老白就想发作。时间久了,我竟能即兴发作,不用想老白了。
前几天,我们单位组织科长退休了,组织科四十多岁的副科长老赵有望顶上去,可在班子会上,一把手突然提出让办公室入党还不到一年的小沈当组织科长。这小沈是个富家子,还不到三十岁,刚来一年就入了党。按惯例这种事领导事先应该同班子成员私下打个招呼,看来她根本没把我们几个人放在眼里。我的机会来了,我率先发言,如果等到有人赞同就晚了。
我否决的理由非常充分,入党不到一年当组织科长不符合组织要求,另一个班子成员也提出了异议,还有一个保留意见。一把手的提议没有通过,有些气急败坏,我提的老赵,她很不耐烦地说“先放一放吧”。我知道这一放,不知道放到哪一年。
问:这种人是怎么上来的?
回答:经领导推荐,组织部门考核,市委常委会讨论决定。
问:机关里这种官儿多吗?
回答:很多。
又问:这么严格的选官制度怎么还会有问题?
我的回答是——推荐制无法保证被推荐人的操守、才干。人太复杂了,谁也不知道这人明天有了权会怎么做。再有,中国社会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跨越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跨越是要有思想基础的,就是说大众的境界也要跨越。境界是不能跨越的,要缓慢提升。人的境界没有提升,制度有了跨越,一定会出问题。有人自豪地说:“我们用三十年时间走了人家一百年走的路。”问题就在这,我们走快了,精神与物质没有同步发展。
科举上来的官是凭自身能力考上的,所以民众信服。大众信服带头人才会跟着走,如果不信服就会有麻烦,带头人要经常停下来说服大众,还要时时回过头防止民变。今天的招聘、招标就是这种理性的回归。如果“官”都是凭自身努力考上的,官民矛盾就会减轻,国民才会喜欢读书。推荐制的结果是有推荐权的人被团团包围,不得安生,结果不难想象。
同学周自横的女儿结婚,结婚前二十多天周自横在街上看到我了,叫住我,告诉了我他女儿结婚的日子,因为时间长,我给忘了。此后周自横见到我,把头转了过去,有意不理我。我见状,猛地提起了丹田气,大叫一声:“周自横,你怎么把脸转过去了?不就是因为你闺女结婚我没去吗!你提前二十多天告诉我,我能记住吗!你还不理我了,能全怪我吗!”慌得周自横连忙道歉。
我借着酒兴,把这场景讲给了黄虫子听,原以为他会表示赞同,夸奖我两句。谁知这家伙听完后,竟厉声质问我:“你别装傻了,你就是没把周自横当回事,市委秘书长孩子结婚,提前四十天告诉你,你能忘吗?”
“那不能。”我连忙承认,我要是不及时承认,这小子还不知说出什么难听的话来,他可不给我留面子。
说到秘书长,我又想起一件事来,为了堵黄虫子的嘴,也为了缓解一下酒桌上的气氛,我又讲了段故事。
几年前,我在市委机关党委纪检组当副组长的时候,单位接到群众举报,说是机关印刷厂一年前改制的时候有问题。简单地说机关印刷厂由国有改民营的时候,价值作低了,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举报的人拿出证据说当时主持转制的吴秘书长有问题,这个时候吴秘书长刚刚退休。纪检书记让我和市纪检委的同志一同找吴秘书长来纪检组谈一谈情况。我打电话通知了吴秘书长。
吴秘书长算是我的老上级,我和他虽然在一个大楼里办公,可很少打交道,有时候在走廊里碰到面,也只是在实在避之不及时,双方才勉强打个招呼,看得出他是出于礼貌才回应我的。我是个小人物,人家根本不会认识我。市委秘书长管的部门多了,市委保密局,机要局,档案局,机关党委(现在叫机关工委了),还有食堂,车队等部门。虽然现在退了休,和我也不是一个档次的。
让我找他来谈情况,我有点忐忑,又有些兴奋。真想不到,吴秘书长一进纪检组的门,就很谦恭地握住我的手问:“临窗,找我什么事?”
我惊奇他竟知道我的名字,我看到他的谦恭中流露出了明显看得到的惊恐。想不到我曾经尊敬、羡慕并竭力巴结的上司,竟然这么虚弱。他接下来的问话更让我惊奇。
“你家粟粟现在怎么样?”
啊,他还知道我老婆叫粟粟!
我这才相信办公室老姜曾跟我说过的一段话,“你别以为大领导在走廊上抬着眼睛向前走,没注意到你,你经过他身旁时什么表情他全看到了。”
吴秘书长的事最后以查无实据了结。
我始终不知道他是早就认识我,还是那天我打电话找他来谈情况后,他现找人打听我的。
我沿着这思绪向意识的深处走,想弄明白。
突然,一个响雷在我头上炸开,骤雨跟着就下来了,河边的闲人四下乱跑。我东张西望,不知道该躲到哪里避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