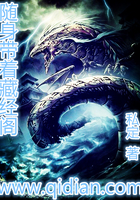起身一个人默默出去,回望一眼,母亲也正担心地看过来,他轻轻点头,示意自己没事,只想看一看在千年中活下来的血骨堡。血骨功对他来说没有什么用处,也许现在先散散心反而对他更好。
武轶霄聚精会神地聆听展隐天将上古功法一一传授讲解,甄逸世也时不时叹服地点点头。何弦志微微抓住她的手,这位父亲对自己的儿子绝对信任,一路上也只有他从未对他做过什么干扰。
沈忆琴便也回过头,这里是血骨堡,他去不了哪里。
见他出来,那些人便都对他点头,有些人放手里的活,拍一拍手,太多问题想要问他:“千年后人族一位羽武者都没有吗?真的吗?”
何离剑暗暗叹息,无法回答。问他的人是一个光膀子大汉,看到如此神色已经知道答案,略显失望。
却有一个小男孩直勾勾瞅着他,不敢靠近:“哥哥,你真是魔武者吗?”
何离剑没来由心中一缩,让自己露出一丝微笑,对方不过一个小孩子,自己何必挂着一张不会笑的脸。从七岁开始自己就是一直看着绝望的脸轻视的脸厌恶的脸狰狞的脸长大的,直到十年后才远离那些让他憎恨的脸。
淡淡一笑,点了一头,依旧是说不出话。
小男孩见他微笑,似乎生出一些勇气,小心往前踏出一步,直勾勾看着他,羡慕无比:“我可看看吗?”
何离剑一愣,不知道他要看什么。
旁边一名少妇连忙过来将小男孩拉回去,对何离剑点头:“小孩子不懂事。”
小孩子当然不懂事,魔武者对人族来说乃是异端,对魔族来说乃是禁忌。
“没事。”何离剑微微摇头,看一眼这名女子,褴褛的衣衫一定是几代人都穿过的。
禁不住问:“血颜为什么叫血颜,难道人族古姓中有血姓吗?”
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大概血颜从见面开始就给他留下无法磨灭的印象,从第一眼把他吓得后退,羞得满脸通红,到一路上对众人的厌恶和冰冷,再到刚才对自己的厌恶。她好像与这些人有些不同,人人都因为他是魔武者而敬畏好奇,只有她是厌恶的。
事实上没来这里之前她对自己还有一点敬意,准确说是对魔武者有一些敬意。因为自己似乎几次说了几句让她不开心的话,所以慢慢开始厌恶起自己来。可能因此她也开始厌恶魔武者了吧,毕竟魔武者刚诞生的时候羽武者们也是时刻提防,谁知道这个异端究竟是不是真的选择了人族呢?
这些人对自己敬畏其实是因为魔武者,而不是因为自己,他很清楚。而敬畏魔武者也是因为第一位魔武者是真心为了人族,这份敬畏来自于第一位魔武者,不是来自于他这位魔武者。
所以说白了,这些人排除掉因为第一位魔武者的敬畏之后,对他其实是满满的提防和警惕,他其实比起屋里的众人还不受欢迎。不论是自己的父母,还是武轶霄,还是甄逸世,哪怕他们在血骨门面前弱得让人轻视,但他们终究是人族,是这些人的族人。
而魔武者,既非人族,也非魔族,既是人族,也是魔族。面对似人非人,似魔非魔的武者,换成任何人都不会放下警惕,甚至是敌意。
如此一来他也理解血颜对自己的态度,但一直不明白这名少女的名字怎么这么怪。
少妇咦的一声,没想到他会主动说话,还是提出问题的,更没想到他不问血骨堡和这块大地的相关之事,却是血颜的名字,稍微一愣。略一停顿,秀眉微凝:“她自己改的名字,她本名叫薛烟。”
“薛烟?”何离剑惊讶,多好的名字,为什么改成阴森的血颜两个字?
少妇生怕他问更多问题似的,拉着小男孩就走开,何离剑也默默走开。
举首环视,高达里许的城墙将这块方圆七八里的地方围起来,城墙上焦黑焦黑的,期间镶满了繁星一样的森森白骨,宛若一个紧闭的地狱,让里面的人无法逃脱出去。
围墙之内,此一座彼一座的石屋相互依靠,相互守护。黑色是这块大地特有的黑石,那黑石本身就带有魔气,融化在镶在上面的白骨散发出来的浓重魔气中,一间一间牢不可破的监牢似的。
他漫无目的地乱走,任由双脚将自己带到哪里去。
路上不时有人惊讶地停下手中的活,迟疑地看着他,想要开口却又犹豫不决。有的人则对他微微点头,目露敬畏。他们似乎每一天都很忙,不是在打磨兵刃,就是在苦练血骨功法,这里每一条都是战场。
对他们来说是玄泰大陆遗忘了他们,甚至算是抛弃了他们,千年里他们将玄泰大陆上的人称为外面的人,都是外人。五人的到来都是外来者,尤其是他这个魔武者。
不知不觉走了许久,才发现身后跟了几个小孩子,一个个睁着大眼睛害怕地看着他,却又忍不住好奇想要看清楚一点,靠近一点。看他们带着稚气的脸有些脏兮兮的,那是被父亲在地上扔来扔去造成的,有些脸皮和手脚都划破了,那也是父亲教授武道的时候摔出来的。
何离剑一怔,停下脚步,这几个小孩子立即吓得直打哆嗦,挤成一团,个个绷着小脸瞪住他。
何离剑苦笑,心中酸酸的,轻声道:“你们现在是古武者还是玄武者?”
这句话有玩笑的成分,他们当然是古武者,哪有七八岁就能成为玄武者的?这几个小孩子都不敢答话,忽而当中一个小女孩转身就跑,不住叫着:“爹,爹。”
剩余小孩子们也都呼啦一声转身就跑,不住跟着叫起来:“爹,娘。”
没有一个会哭,但其实他们心里很害怕,明明害怕却按不住好奇鼓起勇气偷偷跟在后面。
何离剑愣愣地看着他们小兔子一般的身影眨眼钻进各处躲藏起来,心中一阵空落落。
旁边一人抱着一根胫骨,这胫骨被他打磨得光溜溜,瞪着眼睛看着他一直不动,似乎因为他主动与小孩子们说话放松了一些神经,吞一吞口水,开口问:“那是什么剑?”
何离剑起身:“魔泣剑。”
“唔。”这人皱着眉头,揣摩剑名的意思,点一下头,极为羡慕,哪怕那是无柄的剑,又尝试说了一句话,“没有剑柄吗?”
何离剑轻声苦笑,将魔泣剑从腰间抽出来,在手里掂一掂:“本来是未完成的剑,所以没有剑柄。”
想起他们历经千年一把剑都没有剩下,将魔泣剑递过去。
那人略一犹豫,咬咬牙,终于狠心将手抬起来,接过这把剑。指尖触及那无柄的长剑,微微一抖,目中微光闪现,哆嗦声音:“原来这就是剑,这便是真正的剑。”
指尖激动地顺着魔泣剑洁白的剑身抚过,目中大放异彩,不住道:“奇怪的感觉,这就是钢铁吗?”
何离剑神色微暗:“钢铁也不过如此,依旧不敌魔族。”
他们就是因为魔族而连一把断剑都没有留下,在千年里尽数被毁掉了。
这人闻言抬头看他一眼,似乎发现其实魔武者也没有什么与众不同,叹息道:“你说得对,血骨门还不是一把利器都没有残留,全被这些异族的利爪魔牙毁掉了。”
嘿嘿一笑,用力拍一拍怀中的那根胫骨,胫骨粗大,齐眉高,被他磨得油亮油亮:“既然如此就用它们的。”
何离剑淡然而笑,目露钦佩:“你们真了不起。”
这人慢慢放松了警惕,笑道:“我们要真了不起也不会落得如此下场,但只要魔族不灭,还能活着我们还是厚着脸皮继续活下去。”
忽而指尖一抖,奇道:“但凡刀剑都是利器,怎么这剑都不锋利呢?”
魔泣剑并未完成,连锋刃都没开,否则按照他那样的摸法五根手指头早就断掉了。何离剑没开口,他又抓着魔泣剑左看右看:“不嫌弃的话我给你装上个把手吧,反正你们进来了也出不去了,只有我们能给你装上这东西。”
何离剑目光黯然,刚要开口,却再也说不出我们一定能出去这句话。神情恍然之间,这人当他是答应了,回身进屋。
不出片刻抓着半截骨头出来,扬一扬:“我上次用断的。”
拍一拍怀里的那根胫骨:“这是现在用的。”
笑一笑,就地坐下来,埋头一阵捣鼓。将魔泣剑光秃秃的剑茎插入半截骨头之中,咚咚咚地在一块光溜溜的黑石上猛然一顿狂砸。眯着眼睛不住打量骨头与剑茎的方位与接合,不时进行调整,咚咚咚之声听着有一种异样的动听。
何离剑也坐下来,不做声响看着他为自己装上剑柄。盂洁瑶本来要给他找人装上剑柄,但事后种种突发接连而来,两人根本无暇顾及,一直至今。也许真的像他说的那样,众人进来了可能就永远出不去了。
既然如此,就让他帮自己装上血骨堡特有的剑柄吧,自己本来也对这些没有什么要求,因为自己本就一无所有,哪怕连剑茎都没有的长剑他也不嫌弃。
看着他娴熟地将半截骨头慢慢地,一点点地敲进去,不住调节,专心致志,两人再没有其他话,你专心做事,我静心在旁边看着,似乎感觉原本焦急烦躁的心也慢慢静下来。
脑子便又开始自己动了,凝眉心中暗暗道:“无我心境,如何才能进入无我心境,进入了无我心境之后又要如何回归自我。”
一时间又像这几天里一样,皱眉不展,魂不守舍。
听得咚咚咚的声音没了,他举着魔泣剑,抓着半截骨头所成的剑柄,笑道:“成了。”
何离剑回过神,那半截骨头不知道是魔物哪个部位的,大小适中,不过略长,足够双手握着还多三寸,奇道:“这块骨头是哪块?”
这人咧嘴而笑:“小牙。”
拍拍自己的那根骨棍:“这根也没完成,才做到一半,我要把魔牙一根一根地全部装上去,到时候一棍子下去那感觉可爽了。”
何离剑愕然,这些人的兵刃稀奇古怪,用途更是让人心中战栗,全都是本着造成最大杀伤力而去,目露感激和敬佩:“多谢,你们太了不起。”
这人一挥手,笑了,掂量掂量魔泣剑,看着他:“现在称手很多了,我可以试一下吗?”
何离剑笑了,不知道为什么跟他聊了几句脑子清醒很多,点头。
这人站起来,将骨棍扔在一边,骨棍在焦黑的地面上发出当啷当啷的声音,他厌恶地一脚踢开。显然,使用魔物的骸骨作为武器其实他们心里很厌恶,只要是跟魔物有关的他们其实都很厌恶。
而他们住在因为魔气而成的黑石与魔物骸骨的血骨堡中,住在黑石与骸骨的石屋中,其实心里一直都不痛快吧,只是逼不得已罢了。
这人挥舞了两下,并未用上玄力,叹道:“手感真舒服,人族果然还是适用钢铁打造的兵刃,利爪魔牙才是魔族的。”
何离剑也慨然,这就是四方院为什么在千年里一直倾注所有心血打造好剑的原因,血骨门如果有了他们打造的宝剑肯定不会去碰魔物的骸骨。
“可惜。”这人指头摸着没开封的剑刃,面露惋惜,“可惜没开锋。”
何离剑抬起手:“它比较特别,来。”
这人不解地将魔泣剑还给他:“特别?”
何离剑指头在未开锋的剑刃上一划,速度奇快无比,在如此速度之下指头立即被磨出一道血痕。一滴鲜血滴落,刚刚触及那未开锋的剑刃立即嗤的一声,宛若滴落清水中的墨水,顷刻将那清水染得变色一样,魔泣剑刹那一片通红,烧得通红似的。
嗡的一声,通红的魔泣剑散发出灼热的气息,原本未开锋的剑刃竟然锋利无比。何离剑抬起袖子,魔泣剑在袖子上凭空轻轻一划,半只袖子无声落在地上。
这人惊得连连后退,瞪大眼睛直勾勾看着通红的魔泣剑,声音变形:“怎么回事?”
何离剑一抖魔泣剑,在剑锋上轻轻一拨,发出嗡嗡的轻吟,苦笑:“它只会因为魔族之血苏醒,我的血它也认为是魔族的。”
这人微微发抖,惊恐地看着魔泣剑,看它慢慢由通红渐渐变暗,剑锋也慢慢变钝起来。最终恢复原本的洁白和无锋的模样,安安静静的,失去了刚才的凌人气势。
“魔……魔泣剑……。”这人颤声道,想起自己刚才就为它装上剑柄,反而不敢靠近。
何离剑对他感激不尽,轻轻挥一挥,手掌不大不小刚好握得很舒服:“多谢。”
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身边围着几个人,个个与这人一样瞪着眼睛,不敢说话。刚才那几个小孩子也都又围过来,一双双大眼睛看戏法一样直勾勾盯着魔泣剑。
有一个小孩一开始的害怕终于消失,现在有大人们在身边,终于敢开口:“哥哥,再来一次好不好,我没看清楚。”
“嘘。”身边的人应该是他父亲,瞪他一眼。
就在此时,却听得城头瞭望台上的人惊呼:“候坚石,怎么了?”
众人纷纷抬头看去,何离剑也禁不住望去,只见瞭望台的人已经纵身往城墙外面落下去。脸色一变,也闪身朝城头掠过去,身后那人也一把抄起被他踢开的骨棍,一声不吭紧追在后面。
落在城头的时候瞭望台的人已经背着一个瘦得跟猴子一样的人掠上来,将他放在焦黑的城头,惊道:“候坚石,快说话,展御风呢?你他妈怎么一个人回来?”
何离剑记得展隐天说过他的儿子展御风已经去追踪魔族少女的动向,带着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眼前的人了。脸色大变,也沉声道:“你们遇到她了?”
蓦地,听到身后一个熟悉的声音又惊又怒,喝道:“全让开。”
血颜恼怒地拨开跟着何离剑来的那人,一把推开何离剑,伸手就将这个瘦如猴子的人拎起来,杏眼怒瞪:“快说,不准死,展御风呢?你竟敢将他抛下?”
将他背上来的那人掰开血颜的手:“血颜,够了,让他喘口气。”
血颜又惊又怒,娇躯微微颤抖,插在腰间的那根魔爪显得小蛮腰更加纤细诱人。
这瘦如猴子的人一身鲜血,将背他上来的人染得一张宽厚的背部通红,有气无力:“我们被埋伏了。”
“他呢?”血颜怒得冲这个可怜的人的脸大吼,秀脸上那三道血痕此刻仿佛燃烧起来一样,再不说清楚一点就要被她烧死了。
瘦如猴子的人已经很努力让自己把话说出来,乏力让声音颤抖:“是八生魔,在红妆坡。”
血颜袅娜身影一花,他没说完已经不见了,飘飘渺渺顺着那面白骨所成的斜坡掠下去,眨眼消失。
“慢着,血颜。”跟何离剑来的那人与瞭望台的人齐声惊呼。
跟何离剑来的人怒道:“一听到八生魔就失去理智了,混账。”
身影一闪,火速往血骨堡中去。
何离剑也站起来,望着血颜消失的方向:“八生魔?”
倏地,人影也荡然无踪,消失在白骨所成的斜坡尽头。瞭望台的人见他也追去,神色安定不少,暗暗松一口气。既然有魔武者跟去的话那就放心了,但其实这位魔武者是什么样的魔武者,只有何离剑心里最清楚,恐怕要让他们失望了。
展隐天噌地跳起来,满脸横肉不住抖着:“红妆坡?”
给何离剑装上剑柄的人也面露怒色:“他们中了埋伏,候坚石重伤归来,不过幸好魔武者也跟去了。”
说罢自己也不敢肯定,还是又惊又怒地低下头,充满不安:“问题就在月圆之前他们可能不能赶回来了,红妆坡距离太远,魔武者在的话可能不会有事,哪怕无法几时回来也没问题吧。”
沈忆琴惊得纵身要掠出去,却被展隐天伸手拦住,喝道:“慢着,谁都不准出去。”
沈忆琴拨开他的手,怒道:“谁敢拦我。”
展隐天双眼一瞪,将武轶霄人等也瞪得愣住,这些千年里与魔物死战的血骨门后人怎么突然怂起来了?
展隐天冷道:“谁敢出去,我血骨堡可不会保他。”
甄逸世一直就在意他们说的月圆,也让三人冷静下来:“何谓月圆?”
给何离剑装上剑柄的人吸了一口凉气,看展隐天一眼,声音变得低沉起来:“月圆之日,血骨堡任何人不得进出,月圆之夜,血雨腥风。”
何弦志僵着脸要出去,展隐天倏然出手,猝不及防之下竟然无法反应过来,当即软倒。沈忆琴大吃一惊,本能地闪出腰间长剑,却被武轶霄抬手按住,沉声道:“冷静。”
举目看往屋外:“把话说清楚。”
展隐天扶着软绵绵的何弦志坐下,鼻子冷哼一声:“这是为你好,既然是魔武者他们应该没事,你们跟去是要附送几条人命吗?杀一送四是不是?我不知道外面最贵的东西是什么,但在我这里,人命有时候是最贱的,但有时候也是最贵的。”
挂着冷森森的冷笑,扫一眼武轶霄、甄逸世、沈忆琴:“人命在魔族面前是最贱的,对我血骨堡来说是最贵的,少一个人就少一分希望,不只是你们有儿子,老子儿子也在那,只能祈求他们能活下来了。”
目中露出极度厌恶:“真是受不了你们外面的人,要本事没本事,要脑子没脑子,只会像动物一样全靠本能办事。”
给何离剑装上剑柄的人这才微微平静,将月圆之事说了出来:“明天就是月圆之日,所谓月圆……。”
众人听得惊诧不已,目中露出惧色。
“剑儿。”沈忆琴几乎要晕倒,奋力挣开武轶霄的手。
展隐天冷冷道:“你要去就去吧,你不去的话他反而可能更轻松,去吧,增添他的麻烦和压力,去,成为他的累赘,好母亲就是要成为儿子累赘,好好地害死他,自己再跟着一起死。”
武轶霄沉着脸,挡在沈忆琴面前,摇摇头,坚决不让开,担忧地回望一眼屋外。
沈忆琴颤声道:“你不是人,你儿子也在那。”
展隐天冷笑:“对,只有你们是人,我们才不是人,人都死了,我不会为了救自己的儿子害死血骨堡所有人。”
拂袖而去,头也不回。
给何离剑装上剑柄的人面露歉意:“如果在以前他第一个就冲出去了,但他已经死了三个儿子,这是最后一个,为了救那三个儿子他连自己妻子都死了,血骨堡也死了二十人,我们不是动物,一下子生不出那么多人来弥补。”
说罢,也转身离去。
这就是残酷的现实,感情在战场上是没有任何作用的,硬说要有就是让更多的人死去。所以他们选择冷酷无情,只为了不让更多人死去。为了救三个儿子死了二十人,加上自己的妻子,这个结果让他不能不冷酷。
血骨堡中幸存的人越少,就意味着相对来说魔物越强大,魔物越强大,血骨堡中一个人都活不下来。为了维持这种自己与敌人的强弱平衡,有时候牺牲一个人两个人是被逼无奈,就算是亲儿子也必须瞪着眼睛看他死在面前。
因为这块被封印的大地上,他们是唯一的人族,他们死一个就少一个,没有其他人来弥补了。妻子和二十个人的代价让他冷酷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