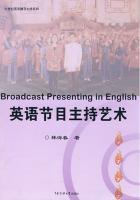“麟王殿下女扮男装确有欺君之嫌,可只要明理之人稍稍一想,也知此事并非麟王殿下一人之过。麟王殿下贵为我天信国嫡皇子,却在昆阳城做了五年质子,单是这份牺牲,足以抵过一切,如今怎可再将所有过错皆推到麟王殿下身上!有功之人却要受罚,这又是什么道理?”
信元川见他为信苍曲不平,不禁轻笑一声,“老将军这话可就不对了,麟既身为女子,如何还能以嫡皇子称之。”
信苍曲英眉一挑,绯瞳转向信元川,笑吟吟的道:“是啊川王兄,本上不是嫡皇子,我天信国只你一位皇子。”
闻得此言,信元川瞬间意识到自己说错了什么。
“所以像那种去他国做质子的事,也非你不可。”信苍曲神色淡然,“本上可算是替你去昆阳城做了五年的质子。”
信元川眸中隐现锋芒,直视着那双绯瞳,两人的目光隔空相撞,似在无形中过了好几个回合。
“真是精彩。”昆吾迥诺轻邪的声音响起,“原以为这样的事只会发生在我昆吾,想不到天信国……”
他冰眸闪了闪,目光扫过信苍曲又移向信元川,这一举动足以表达他没有说下去的话。
几个月前,昆吾国大皇子、三皇子、四皇子、六皇子联合起来对付昆吾迥王,并蓄谋兴兵造反,最终事败垂成,无一得赦,由此足见昆吾国内部的矛盾。而此事在当时几乎轰动了整个辛洲,殿上的人岂有不知。
他说原以为这样的事只会发生在昆吾国,想不到天信国———也是一样。
信元川、信苍曲表面上虽看似和睦,可说出的每一句话,看向对方的每一个眼神却无不以毁灭对方为目的。
“迥王殿下此言何意?”所谓贼人胆虚,信元川敏锐的目光投向昆吾迥诺,心里狐疑的猜测着:难道他发现了什么?
又转念一想,不可能!那件事他自认天衣无缝。
看着他闪烁不定的目光,信苍曲更确定了一件事。
“呵呵……”昆吾迥诺笑笑,“只是想起了一些往事,心生感叹罢了,并无他意。”
纪冲风幽淡的目光不经意的轻瞥了信元川一眼,眼底的利锋几不可见,仿佛在提醒着信元川什么。
信元川心头一沉,顿时明白自己又做错了。
天信国主高坐上位,一边拧眉深思,一边俯瞰下方几人,状似漫不经心,却又好像殿上所有人的一举一动都在他掌控之中,而此刻,却由不得他不思忖起另一件事了。
“不过本王倒是觉得麟王殿下所言甚是在理,吾弟狸渊至今尚在贵国国都,依理贵国也应派出一位皇子入昆阳城为质,而贵国为了保护唯一的皇子———川王殿下,却将女扮男装的麟王殿下送入我昆阳城为质,如此欺我昆吾,当年和谈意义何在?”昆吾迥诺手一动,袖中的白玉扇滑落掌中,他不看任何人,目光落在白玉扇上,指尖轻轻触抚着扇骨,看起来似是无意,可却明显示意:或天信国给出一个合理的说法,或武力解决。
“荒谬。”信元川没想到这位邪君迥王如此利齿能牙,竟比昆吾狸渊还难对付,一声冷笑,“当年送麟入昆阳城为质时,无人知其女扮男装,何来欺人之说?而贵国狸王殿下与麟同为两国嫡皇子,为表诚意,我天信方将麟送入昆阳城为质,如此又何来让女扮男装的麟王替本王为质一说?”
昆吾迥诺依然没看他,把玩着手中的白玉扇,那般漠然无视的态度与信苍曲简直一般无二,不由令信元川怒火更盛。
“这些话,川王殿下还是留着跟天下人解释吧。”
即便信元川所言皆为事实,可天下人却不知,而天信麟王的处境却世人尽知,试想若此事传扬出去,天下人势必会认为天信国为了保护唯一的皇子信元川,让嫡公主信苍曲女扮男装,并赐名信麟,册封为麟王,替其入昆阳城为质。且还有个天师预言横在世人心中,信苍曲命煞克亲,乃败国妖星,所以天信国如此做,明面上是将嫡皇子送入昆阳城为质以示诚意,实则却不排除另一份算计———让信苍曲入昆阳城,那么她的命途必也会同昆吾国连在一起!如此若她能在昆阳城待一辈子,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而信元川此刻可以站在这里同昆吾迥诺理辩,却不可能逐一向天下人解释,所以天下人那般认为的,那便是事实。
天信国主眼波一动,扫了昆吾迥诺一眼,心知昆吾迥诺所言皆为实理,而昆吾国若想以此为借口拿住天信国,天信国定将永无可能再翻身,不过听昆吾迥诺话里话外都没将话说死,似乎还有商量的余地,他心里便也做到了有数。
“公道自在人心,本王问心无愧,何须解释。”信元川也知情势不利,底气不由稍显不足,但却依然振振有词。
昆吾迥诺淡淡一笑,话已点到,不与他逞口舌之能,只是一双冰眸却望向了上方的天信国主。
那道冰冷的目光即便平静无波,也永远那么犀利,让人无法忽视。
“咳咳……”天信国主咳了两声,终于开口:“川儿。”
“父皇。”信元川躬身应道。
本以为他的父皇会帮他说话,谁知天信国主却道:“跪下。”
信元川抬头看着天信国主,一脸惊讶与不解。
“跪下!”见他未跪,天信国主面沉如水,又重复一遍。
信元川陡然一震,终撩袍跪在阶下。
天信国主如此对他,还真是少有的事。这么多年来,他的心思从未能出天信国主左右,所以那一刻,他心中是真的畏惧了。
便是信苍曲也不禁有些看不明白,这样的态度一向都是对她才会有的。
“不是跪朕。”天信国主声音冷漠。
信元川眉头一皱,立即明白了父亲的意思。只是,要他跪昆吾迥诺,那还不如杀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