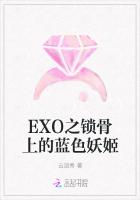拿了银票,明明只是几张纸,但绿罗总觉得怀里沉甸甸的。妓馆那种地方,她一个姑娘家明目张胆地去总不太合适,便稍稍变了一下男装,还把紫衣给叫上了。紫衣对这事出奇热心,二人趁着夜色,叩开了妓馆的后门。
“又是你们。”说这话的龟奴却没有不耐烦,毕竟紫衣上次出手阔绰。
掂了掂手里的银子,龟奴放她们二人进了门:“等着,我把那娘儿们叫过来。”
“慢!”紫衣沉声道,“我们来赎人,银子管够,把老鸨子叫过来。”
听到银子管够这种话,那龟奴本能的眼睛发光。
这次的待遇就不同了,小厢房,有座椅,还被奉上两盏茶。
“姑娘真好呀~”绿罗又一次赞叹。
紫衣点头:“是啊,要是能一辈子跟着姑娘,那我就满足了。”
绿罗噗嗤笑出声:“说什么呢,你还不嫁人啦?”
“嫁人?”紫衣露出轻鄙的神情,“就吴大这种?”
“这种人毕竟是少数嘛,女子终究要嫁人的,还能一辈子当个嫁不出去的老姑娘呀。”绿罗笑笑,“更何况紫衣姐这般貌美,将来还指不定便宜了哪个小子呢。”
原本只是玩笑话,紫衣的脸色却一下子沉了下去。
好男人或许有,但她不相信自己能那么幸运,还不如一直在慧济堂做事,有一份能养活自己也有意义的活儿干,总比围着个贱男人成天以泪洗面强。
紫衣摇头:“我是不打算嫁人的,若将来有一天你能寻到归宿,盼你能和和美美就好。”
绿罗俏脸一红,以手捂面:“紫衣姐说什么呀,还得等几年呢。”
这才是一个正常女子的反应啊,紫衣默默感慨,神情带着几分沧桑。
说说笑笑间,时间仿佛过了很久。
她们有些坐不住的时候,老鸨花姐扭着腰肢走了进来,媚气入骨地笑:“二位不用再等了,菊娘在我这儿吃好喝好,是不想被赎走的。她刚让我给你们说别再来了,今儿呢也就不见了吧。”
哐当,有重物砸地的声音响起。
三人寻声看去,吴庸怀里的包袱敞开,里面有些许银两,还有不少吃穿用具。他经常来看菊娘,也恰巧听到了花姐的话。吴庸反应过来后大叫:“不可能!你骗人!”
门后头突然涌出几个龟奴,推搡吴庸道:“花姐说什么就是什么,这儿还有你撒野的份儿?快滚!”
吴庸往前冲,伸手去扯花姐的衣袖,嘶吼:“我要见我娘!我要见我娘!”
目眦欲裂,眼睛红得仿佛要滴出血来。
花姐给方才开门的那个龟奴使了眼色,那龟奴顺着墙根溜了。紫衣看了绿罗一眼,绿罗点头,上前去帮吴庸,乘势大叫着把水搅浑。紫衣紧跟那龟奴,拐了几拐,来到一个偏僻的厢房前,那龟奴轻敲几下,低声道:“官人,这娘们儿的儿子闹僵起来了,您快些,小人赶紧善后,保证您没有后顾之忧呢。”
里面传来不耐烦的,气喘吁吁的声音:“等着!爷还没完事儿!”
听到这种****的喘息声,紫衣紧紧攥住拳头,只觉得全身的血液都在往头顶冲。但此刻最需要的就是冷静,他们势单力薄,如何才能救了菊娘?
那龟奴好说歹说,里面的恩客才承诺尽快。
龟奴默默退下来,经过紫衣藏身的小角落时,被紫衣一使劲给拽了进来。
“闭嘴!有你的好处!”
龟奴本是要叫的,但看着厚厚一沓银票,见钱眼开的本能让他忙不迭点头:“给钱,给钱就行!”
“守着这里,别让那人离开,再给我一匹快马,这钱就是你的了。”紫衣甩了甩银票道,“足够你挥霍下半辈子!”
一切就绪,紫衣爽快地分出一半给他:“我很快就回来。”
“好嘞好嘞!”那龟奴点头哈腰,兴奋满足之情溢于言表。
快马加鞭地往宋宅赶,她得尽快让宋凌知晓。
但紫衣刚学马术,还不算熟练,又赶路心切,看到前面一辆富丽堂皇的马车想要绕道,却不小心蹭了下灯笼。
“站住!”
一声厉喝后,一名侍卫模样的男子旋身上前拉住紫衣马的缰绳,强制让马停住。
居然这般不凑巧地冲撞了贵人。紫衣立刻下马赔罪,希望能快点儿结束这场不期而来的纷争。
“你是紫衣?”
紫衣抬头,感觉眼前这名贵气逼人的男子分外熟悉,她连忙垂下脑袋道:“奴婢莽撞,但实在人命关天,还望贵人谅解,放奴婢离去。”不把事儿说得重些,万一太耽误事儿怎么办?
男子的脸上果然有了情绪,声音中也带着一丝轻易无法捕捉的急切:“你刚说人命关天,是宋东家出了事?”
认识紫衣必然是通过宋凌,这点紫衣还是有所觉悟的。
她暗忖了一下,低声道:“是。”
男子微微一笑:“告诉我,我可以帮你。”
面对这种诱导,对男人充满防备的紫衣委婉地拒绝道:“慧济堂的事需得先行禀报东家,奴婢不敢擅专。”
男子从马车上走了下来,笑:“你知道你们东家有一个师兄吗?你应该也知道这里距西宅比较近,西宅里面住的是西阁前辈,我出现在这里是要去找师父请教功法。还有什么疑问的,你可以直接说。”
紫衣这才敢打量箫景敛,看看他的行头,再看看他的派头,自然信了他的话,忙再次行礼:“参见廉王殿下。”
“这就是了,人命关天必定紧急,告诉我,我可以帮你。”
再次听到这句话,紫衣犹豫了。
念及菊娘还深陷在妓馆不知死活,而绿罗与吴庸更是吉凶难料,她胸腔里突然腾起一股热血,抬头道:“我家姑娘无碍,是慧济堂的工匠出了事,您也要帮?”
听闻宋凌无事之后,箫景敛着实松了口气,看向紫衣的眼神多了一丝兴味。还真是宋凌身边的丫头,都有那么几分狡黠,这是在激他吗?
“原本就是自家事。”箫景敛道,“不急于一时,你先上来,将事情告知与我,我会派人去通知宋凌,如何?”
紫衣想了想,虽说慧济堂有点小钱,但现在毕竟不在国公府里住着,算得上人微言轻。而这些妓馆长久经营于兴阳府,盘根错节,除非真正的强龙,恐怕还难以压制住这地头蛇。
她上了马车,将事情原委悉数告知,最后缀上一句:“姑娘待我们如同家人,听说吴庸之事,很是难过。”
蛇打七寸的道理箫景敛怎会不懂?
算了,跟一个小姑娘计较些什么?箫景敛笑了笑,他能多管这一次闲事,无非是与宋凌相关,紫衣太希望菊娘被救,自然要多多提及宋凌。妓院,妓院。他总是出没于这种地方,上达天听,或许于人于己都有利。
那抹笑容变得苦涩。
解释完一切,紫衣低头,视线丝毫不敢触及箫景敛腰以上的部位。虽然她对现实婚嫁嗤之以鼻,那是因为怕,但国公府多年的下人生活,已经让她的行为举止十分符合一名高规格的古代丫鬟。面对一位亲王,满腔热血渐渐熄灭之后,她的神情里带着些微惶恐。
宋凌听到箫景敛的侍卫禀报时,箫景敛他们刚好到了妓馆门口。
这么一尊大佛走的必然是正门,老鸨花姐满面春风地迎接,盯着箫景敛腰间价值连城的玉佩,笑得嘴角都要咧到后脑勺了。
“哎呦,这位贵客今儿可算找到好地方了,保证伺候得您服服帖帖!”倒也算有分寸,并没有不知好歹地倒贴上去。
箫景敛转了下扇子,风流倜傥的范儿立刻涌出,他拿扇尖指了下紫衣道:“你这场子还要不要,全看你能不能把她伺候妥帖了。”
花姐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还能被一半大小子给唬住了?
虽然这小子全身上下无一不是珍品,但兴阳这种人多了去了,顶多就是有几个钱,能成什么大事?
她面容依旧谄媚,但却没有丝毫慌张,直到她看清紫衣的脸,甜腻的声音蓦地有些颤:“你怎么在这里?”那一行人不是都被打出去了吗?
紫衣气愤道:“我应该在哪里?!”
“呵呵呵……”花姐回过神来,妩媚地笑道,“我们这里不等传唤的姑娘都应该在房里等着客人呐,姑娘这样出现在大堂,还乔装打扮地迎客,我真没见过。”
被这么一说,紫衣登时面红耳赤,羞得恨不得逃走,又想扑上去撕了老鸨的嘴。
果然是术业有专攻,一个内宅丫鬟如何能跟成天靠嘴皮子过活的老鸨拌嘴呢?箫景敛也懒得废话,直接道:“把菊娘交出来。”
花姐笑道:“这位贵人说的是什么?我怎生听不太明白?”
“那就让你看个明白。”
紫衣带路,一众侍卫紧跟,箫景敛坐到一个绣凳上翘起腿,“啪”地一声打开折扇拦住花姐,声音里辨不出喜怒地道:“这个角度好,你就在这儿等着瞧吧。”
周围蓄起了一圈儿围观群众,大多数面带兴奋。
不花钱看好戏啊,來妓院寻欢的人,又有哪个是怕事儿的?
“这个月都是第四起了,我说花姐,你们这儿是不是风水不好啊?”一个脑满肠肥,满面淫笑,一看就是妓馆常客的男子调笑道。
别看面儿上箫景敛只是轻轻地挡着,但花姐却是寸步难行。
她急道:“说什么风凉话!没看到老娘这儿遭贼了吗?赶紧报官去啊!”说罢她恶狠狠地瞪着箫景敛,放狠话,“我告诉你小子,有本事的报上名号,明日我就让人砸了你家门!”
突然飞来一块腰牌砸中了花姐的额头,砸得她眼冒金星。
箫景敛好整以暇地轻笑:“睁大狗眼开清楚了,明日我让府丁好生招待。”
还没等花姐将腰牌上的字看清,紫衣从楼上飞奔了下来,在花姐跟前站定,扬起手臂给了花姐结结实实的一个耳光。紫衣牙关紧咬,两腮坚硬如铁,一双美目此刻充满了愤恨,泛着血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