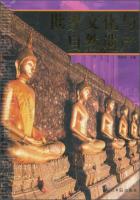好一个难心的冬天
乔女醒过来了。“妈呀!妈呀!”她听到了稚嫩的呼唤。
她慢慢睁开眼睛。丁五爷的三个孽障围坐在她的身边,嘤嘤地哭泣着,脸上挂满了泪珠。见她醒过来,娃娃们连声问:“妈!你咋了?你咋了?”
她没有回答,呆滞的目光在空荡荡的屋子里扫了一圈,又落在三个脏得像叫花子一样的娃娃身上,嘴角掠过一丝凄凉的笑。她明白,随着那几声枪响,她的好日子已经结束了。从今往后,她将领着这几个没娘的孩子走一条独木桥。
“醒来了吗?”一个熟悉的声音。乔女强撑着坐了起来,用手理了理散乱的头发。羊报轻手轻脚地进来,伸手摸了摸乔女的额头:“哦,不烧了。”乔女腾出一点儿炕角:“你坐,你坐。”
“可把人吓坏了。整整两天啊,迷迷糊糊,不吃不喝,嘴里还说胡话,把娃娃们吓得直哭。”羊报说着望了望三个孩子,“娃们已经懂事了。他们整天守着你,没有离开过一步,怕你撇下他们走了哩。”乔女鼻子酸酸的,感到一阵栖惶。
“醒了就好,醒了就好。”羊报说,“这几个娃娃还要靠你拉扯呢。”乔女说:“可是我一个女人家……”
羊报掀开褂子,露出结实的胸肌,硬铮铮地说:“有啥上不去的山,有啥过不了的河,你就说。有我羊报在,啥啥都在哩。”几许欣慰挂在了乔女苍白的脸上。
按照对待地主恶霸的政策,乔女一家应该是被扫地出门的。考虑到孤儿寡母的实际困难,土改工作组把靠近河边的几间场房子留给了他们。羊报叫了张屠家来帮乔女搬家。羊报拉了一辆架子车,把粮食和锅碗瓢盆什么的都放在上面。张屠家要把一张磨盘杠上,乔女说:“算了吧,不要了。”张屠家说:“这东西,嘿,说不定以后还能派上用场哩。”他双臂抡圆,紧紧地抱住磨盘,喊一声“起”,这两百多斤重的家伙,已经放到了他的背上。他跟在羊报的架子车后面,满头大汗地向河边走去。乔女抱着被子和毡子,孩子们抱着衣服和杂物,吭嘛吭味地走向他们的新家。后面,尾随着丁家大院的老黄狗。跟着跟着,那狗发现方向不对,掉头跑远了。
几天时间,娘儿几个就把破旧的场房子收拾得像个样儿了。娃娃们和泥,乔女当泥水匠,把墙上的裂缝一处处泥严、堵死、抹平,又找了一些旧报纸,糊上了卧房的窗户。后来,农会又给他们分了一些农具,以及一张缺了腿的桌子、两把人坐上去咯吱响的椅子,这个家也就安顿下来了。
这时已经到了孩子们上学的时候了,乔女的心里犯起了嘀咕。玉贵已经六岁了,应该让娃去报名了,再迟,就要耽误娃的事情了。可是大贵这个孩子怎么办?他已经九岁了,而且已经上到了三年级,如果不让娃继续学习,娃就只能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跟着自己受罪了。可是让他去上学,庄稼又让谁来种呢?
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她只能狠下心不让大贵去上学了。但她还是征求了大贵的意见:“快要开学了,你是上呢,还是不上?”
“不上了。”大贵坚决地说,小小的眼睛里闪着泪光,“我要种庄稼。”
乔女哽咽了:“孩子,你还小啊!”
“我快十岁了,我能干活了。”大贵说,“我要供两个弟弟上学。”泪水涌上了乔女的眼眶:“孩子,妈对不起你。妈实在是没有办法啊!”
但是小的两个,她是下了决心让他们上学的,哪怕砸锅卖铁哩。她找了十几块零碎布头,连夜给玉贵缝制了一个书包。又买了墨盒买了笔,买了本子买了书,打发娃儿高高兴兴地上学去了。见玉贵报了名,三贵也嚷嚷起来:“我也要上学!”乔女扑嘛笑了:“好,明年等你六岁了,妈也送你去念书。”
孤儿寡母的生活开始走上了道儿。
刚立冬,一场暴风雪就来到了荒凉渡。先是整整阴了几天,然后便纷纷扬扬地下起了这个冬天的第一场雪。雪越下越大,而且根本没有停下来的迹象。几天几夜的鹅毛大雪封住了方圆上百里的河川和山峦,村村寨寨全被雪盖住了。目力所及,是一片白色的世界。黄河对岸传来了嘶哑的低鸣:北风来了。拳头大的雪片打着旋儿,疯狂地飞舞着,排山倒海地扑向荒凉渡。每到夜晚,从冰封的河面上刮来的暴风雪就像鬼号一样,刺进庄稼人的心里:
“呜——”
“呜——”
好一个难过的冬天。
乔女娘儿几个缩在破旧的场房子里,白天不敢出门,晚上冷得无法入睡。风从草泥屋顶的缝隙里钻进来,肆无忌惮地窜着,使这座简易的土屋变成了冰窖。他们太穷了,买不起煤,生不起炉子,唯一的取暖办法就是填炕。那还是深秋时节,乔女领着三个孩子,到荒野和坟地里,用扫帚将已经枯黄的野草连着根和黄土一起扫下来,然后装进筐子里,大贵在前面抬,她在后面抬,近则二三里,远则三五里,一筐一筐地抬到家里。那两个小的,也都不示弱,一人背一小袋草土回来,弄得浑身上下都是土,成了土人儿。庄稼人把这种东西叫做填炕的。这就够他们烧一冬的炕了。但是那可恶的暴风雪,简直是无孔不人啊,它吼叫着从草泥屋顶大大小小的缝隙里钻进来,吱吱地乱窜着。已经到了半夜,小弟兄三个还冷得睡不着。弟兄仨盖着一条单薄的被子,三贵嗷嗷地哭,玉贵直喊冷。大贵没有出声,却也翻来覆去地挪动着。
“唉。”乔女轻轻叹了一口气。她悄悄下了炕,走了出去。炕洞在屋外。她爬到炕洞前,将炕灰拨了拨,把炕火拨得旺一些。黑漆漆的夜空中,风雪还在肆虐,她感到刺骨的寒冷,打了一个寒战。望着炕洞里微弱的火苗,她的眼泪簌簌地流了下来。“嘭嘭!”“嘭嘭嘭!”
乔女听到了敲门的声音。那声音很轻,但在这黑沉沉的雪夜里,听起来却是那样刺耳。
“谁呀?”她问了一声。
“我。”轻得像蚊子叫。
她披了衣服,三步并作两步向门口跑去。门开了,一个高大的雪人立在面前。她立即扑进了他的怀里,放声号哭起来。
雪人用胡子拉碴的嘴封住了她的嘴:“我冻坏了,快进屋。”羊报老羊皮袄上的雪已经冻住了,眉毛和胡楂子上都结了冰。他的身后,是满满的一架子车炭。乔女用困惑的目光望着他。
“我这是跑了几十里路,进煤山买的。”羊报浓眉下面那双大而长的眸子,在暗夜里闪着光。
羊报把炭拉进了场房子。乔女赶忙找出炉子,很快生上火。不一会儿,熊熊的炉火便映红了墙壁和屋顶。寒风被驱赶出去,土屋里充满了暖融融的气息。孩子们高兴得叫了起来。
乔女取了一筐洋芋,埋到炉膛里。一会儿工夫,洋芋便烤得又黄又酥又沙。婢一个个地刨出来,扔到炕席子上,几个娃儿们笑着闹着抢洋芋吃,小小的土屋里一下子有了人气。天已经不早了,她问羊报:“你回呀不?”“你说呢?”“我咋知道。”“你看着办。”“你不怕我的成分?”“怕我就不来了。”
她感激地看了他一眼,泪花在眼眶里打着转儿。她把小屋收拾干净,生了火,让羊报去睡。
雪越下越大了,北风依然狂舞着。在这荒远西部的一个小小山村里,在这黄河岸边的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里,在暴风雪的呼啸声中,年轻的地主婆和贫下中农钻进一个被窝里了。她紧紧地贴在羊报的身上,嘤嘤地哭泣着,泪水打湿了男人的胸脯。她的两只手死死地箍着羊报的腰,唯恐失去了这人世间仅有的依靠。男人一双粗糙的大手在她的光身子上使劲地抚摸着,揉搓着,悄声地问:“疼不疼?”
“不疼不疼,”她连声地回答着,“再使劲些。”男人把她扳平了,在小油灯微弱的灯光下欣赏她俏丽的面容。她用迷离的目光望着男人短短的髭须和健壮的胸肌,叉开了腿,轻声呼唤:“快些呀,哥哥。”
一支粗大的硬物插进了乔女的下身。男人刚刚晃动了几下,她就嗷嗷地叫了起来。
“不要喊不要喊。”“就要喊就要喊。”
一波高过一波的热浪淹没了寒夜中的孤男寡女。乔女伸出舌头,一遍一遍地舔着羊报宽阔的胸脯,嘴里呢喃着:“冤家!冤家!”久旷的男人则雄风再起,一次又一次地进人女人的身体。在巨大夜幕的掩盖下,一对男女,正在演绎着一出人间悲喜剧。
几个回合之后,两人都乏了,汗津津地拥抱在一起,互相吮吸着舌头。乔女用湿润的眼睛幽怨地看着羊报:“全是为了你!要不是你这个冤家,还有那三个孽障,我还有啥守头呢?我早就走了。”羊报咏味地笑了起来。“你笑啥?”女人问。
“我呀,”羊报亲着女人的脸蛋,“笑你傻!”一只小巧的拳头落在了男人的肩膀上。
羊报把女人再一次搂进怀里,亮闪闪的目光望着年轻的寡妇:“再过两年就好了。再过上一两年,政策松些了,我手里再攒几个钱,咱们就结婚呀,正正当当做夫妻。”
一丝幸福的红晕泛上乔女的面孔。她那黑黑的眸子望着红红的炉火,充满了向往。
“明年夏天,我们的筏子要走宁夏、下包头,你跟咱们去吧。”“我去干啥呢?”“给筏子客们做饭呀。”
“哥,你真好。”女人说着,又把男人扳到了自己身上。土屋外面,暴风雪还在肆虐着。
巷口儿
荒凉渡这个地方,在过去的一些年头里,甚至算得上是一个比较热闹的地方。这是由它的地理位置造成的。出了兰州城往西,走上几十里,就没有大路了——公路在河对岸。绵延的悬崖陡立在黄河岸边,悬崖下面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沿着河道向西延伸;再走几十里,就又到了另一个开阔的地方。而荒凉渡就在大路的尽头、小路的起点上。它背山面水,气势雄险。在以羊皮筏子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年代里,这里自然而然地成了筏子客们打尖歇脚的地方。由于黄河水流湍急,羊皮筏子只能顺水而下。各地的水手们把货物卸到兰州城以后,还得把沉重的羊皮筏子扛在肩上,一路汗流浃背地扛回家,到了荒凉渡,已经是人困马乏了。于是这里便有了一些卖凉面卖酿皮的摊子,一些简陋的茶座,当然都一律设在凉棚或者树荫下面。如果是夏秋时节,娃娃们还会提了红红的沙果子,摆成堆儿,当水手们扛着筏子走近时,便一齐像青蛙似的喊了起来:“两毛一堆!两毛一堆!”
新中国成立以后,普遍使用了胶轮大车,甚至有了汽车,羊皮筏子便少了,荒凉渡的那一点点繁华也就风光不再了。设在路边的茶馆饭铺因为没有了筏子客们的光顾,也就渐次关门大吉,娃娃们拾了跌果也无处可卖了。于是荒凉渡的中心便从大路边转移到了村子深处一巷口儿。
祐谓巷口儿,就是村庄里面几条小巷的汇聚点,犹如过去城镇中间的大十字。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里成了庄稼人谝传、晒太阳、捉虱子以及传递各种信息的场所。有意思的是,这还大致地分为了早场和晚场。这里的庄稼人早上不吃馍而吃饭。早饭一律是糜面或豆面搅成的散饭。饭里面和着煮烂的土豆,沙沙的煞是好吃。菜呢,都是人冬时腌制的白菜,这里称做“熟菜”。碗是粗瓷黑大碗或者干脆就是小号的砂锅。大约太阳刚刚冒头的时候,穿着破旧的黑棉祅或者油渍斑斑的老羊皮袄的西部汉子们就一个个端着热气腾腾的散饭,聚集到巷口儿上,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一边低头吃饭。饭吃完了,早上的谝传会也就结束了。这时候,一辆辆铁轱辘车或者木轱辘车,便哐啷啷地驶出村巷,车把式的鞭子在半空中盘旋着,不时发出清脆的响声;一群群羊咩咩地叫着离开羊圈,奔向山坡和河滩,在巷子里掀起一股夹杂着尿臊味的尘土。一天的生活开始了。
晚上的聚谈会要比早上热闹得多,也激烈得多。再简单不过的晚餐——糜面疙瘩或者荞面搅团——吃过之后,乡民们便三三两两地从自家的土门楼子里走出来,在巷口儿扎成堆。先是有人宣讲最新的见闻:兰州城里出了一个不孝子,把瞎眼的母亲背到铁桥上,扔进了黄河;某某村的一家新媳妇,刚过门三个月就生下了一个胖儿子;某某地方的小叔子偷了嫂子,被亲哥哥把那玩意儿给割了;一百里之外的黄河上出现了一条龙,那是龙王爷显灵了……然后就又互相交流信息:最近的麦子一斗卖到多少元,清油和猪肉的价格是多少;今年的西瓜卖不动,原因是天气太凉了,果子却卖了个好价钱。如果是刚进过城的呢,就要讲一讲今天秦声家——他们把剧团叫做“家”——挂了什么戏,主要演员是谁,而文化家又挂了什么戏,从西安搬来了谁谁谁。更有那到外面参加了婚礼吃了酒宴回来的角色,则要细细地讲述一遍人家摆了什么席面,上了什么菜,一道一道地“端”出来,馋得一些听众吸溜吸溜地咽口水。山民们把自己经历的几乎每一件好事、喜事,都要拿出来在这里炫耀一番。这一圈儿讲完了,新鲜货色没有了,就又把陈年老账翻出来——都是讲了一万遍的题目:左宗棠打兰州,马仲英上新疆,刘尔忻重修五泉山,省政府活埋李旅长……及至毎个人演讲了一遍,都把自己知道的那一点点事情贡献给大家后,激烈的争论就开始了:“你狗曰的胡说哩,左宗棠啥时候打过兰州?那是打河州哩。”“去去去,不知道不要显能!”每一件事情,毎一个细节,都要争论得面红耳赤,比几十年后大学生们在电视上的辩论还要认真。到了最后,天已经不早了,三星已移到头顶了,庄稼人忽然想起明天还要下地,而这些劳什子和自己一点点关系都没有,于是便哈哈一笑,回家睡觉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