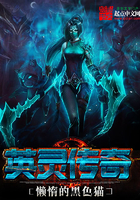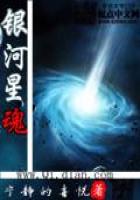第二节
本村人见面,好生亲热。免不了互道温凉,介绍点儿家长里短。判官离家时,六子他们几个还只是半桩后生,如今竟然也到太原府来闯江湖了。判官问过年龄,六子十七,大未子和二楞头也才十九。判官就摇摇头,道:
“十七十八力不全。脚行那苦,怕你们顶不下来!”
三个人就拍胸脯,攥拳头。六子说:
“行不行,还不兴试一试?挣不了这份钱,顶多不过回去扛长工罢咧!”
判官踌躇一会儿,说:
“试试也行,反正头天入脚行都要考工……”
“考工?考什么哩?”
“扛麻袋呗!”
三人又都拍胸脯。判官沉吟一会儿,道:
“那我就做主招了你们。你们几个带钱了吗?要带着,一人给我两毛。按说本村自家,我不兴扣克你们,不过这是个规矩。我呢,不白花你们的,教你们两句紧要的话!”
六子他们三个结伴下太原,拢共带着两块多钱盘缠。打尖住店,花去一块,下余一块四毛钱。六子把那一整块银元递给判官,判官狼叼食似的一把抓了,紧紧攥着,说:
“头天考工,晌午不管饭。不知道的,空着肚子,下午那营生就顶不下来。考脱了,算白给人家干多半天,连夜饭都吃不上!你们几个备点干粮。”
一块银元在掌心里暖热了,判官苦了脸面又说:
“这一块钱我一时也找不开,干脆再告你们两句更紧要的!”他瞅瞅四下里,低了嗓门,“干到天黑,有人呼喊‘吃蒸馍’,你们都提防着点儿。夜饭是要吃蒸馍,到底能不能吃上,看你们过了过不了那一关!”
判官在人市儿上又招揽了几个人,北路口音,傻大黑粗的精兵好汉。六子他们也买好了干粮,大饼子,一人分了俩,掖在腰间。一行人随了判官去上工,六子他们有点紧张,脊梁那儿冷森森的。北路汉子反倒踏实,挺挺地走路,只偶尔瞥一眼,像是和这厢较劲儿。
到了工地,判官把一行人领到账房先生跟前,登了花名册。其他招工的跑腿儿也各个领来些汉子,六子约略数过,差不多二十人。站台上是卸下车皮的麻袋,城墙似的码着。倚了麻袋垛子,是一些破衣烂衫、乌头鬼面的人,眼神木木地朝这厢看,约略有四五十号。寻思这是些什么人,扭头去问判官,判官已然不见了。
呆怔中间,耳边厢猛地一声怪响,狼嚎鬼叫似的。打个激灵想起来,这叫“嚎气”,夜来客栈老板介绍过的。早晨六点,上午九点,正午十二点,下午六点,一天几嚎气,每嚎一分钟。嚎气的机关设在城中心南肖墙电灯公司,太原城周边十八里十八步,处处听得清楚。嚎气声里,站台上走来三条汉子,走到麻袋垛近边,嚎气声刚好停了。当中一条大汉,约摸四十来岁,肩上披一条搭膊,头上戴一顶制帽,三道帽箍。那大汉眯眼看看新招的苦力,叉着腿说话:
“听着!今天的活计,盐包上垛。气力营生,一人一包,谁也别偷懒。扛到下午嚎气收工,吃蒸馍领工钱!——我是大头儿;这二位是二头儿。你们认下!——我先扛头一趟啦!”
大头儿说着,左手从麻袋垛子上夹起一只麻袋,转个身右手又夹了一只。夹定两只麻袋不挪步儿,两个二头儿又架起一只麻袋给他放上肩膀。大头儿身负三只麻袋,脚步沉沉地擦着地皮,从站台走到横木垛架那儿,有三百多步。
六子心里想,五六百斤重,这大头儿也真有点力气。二楞头在一边小声嘟哝:“夹我怕是夹不了,三包扛还是扛得动。”
六子戳了他一肘子,再看那厢,是两个二头儿开始扛包。头一个,左手夹一包,右肩扛一包,就那么斜挂着去上垛;第二个,扛得俏皮,两包都上肩,两肩都只扛一只麻袋角儿,一路小碎步,两只麻袋水上漂似的在半天里移动。
六子心里有了点底儿,照二头儿这两下唬不住人。后来,在脚行立住地步,知道大头儿玩的那叫“独镇三关”,二头儿那两下叫“双擒二虎”或者“二郎担山”。据老脚行说,早年有个大头儿能夹两包、扛两包,身负四只麻袋上码板。叫什么名堂,说不来。账房先生知道,那叫“力杀四门”。
大头二头扛过头一趟,麻袋垛子上倚着的汉子们“呼啦”一下站起身,一人扛一只麻袋去上垛。新来的还都愣着,大头儿喝一声:
“还等什么?”
大家立即一窝蜂抢上,有背的有扛的。六子他们在村里打场扛过粮包,不知这盐包可扛得?用一股大力上肩,竟是一闪,约摸二百来斤,不很吃劲。往来几趟,新来的随了老脚行,渐渐走成一只圆环,扛包半圈,空身半圈,两头不断线。擦汗的当儿发现,大头儿早已不见,两个二头儿一前一后和众人一般扛包。少扛一半趟,也是在那头整垛。
站台这厢的袋码子从一头拆垛,由上而下,渐渐留下最底一层。二头儿蓦地喊一声:
“旱地拔葱啦!”
老脚行们就一个个猫下腰去,独自扛一包咸盐上肩。大未子身矮力壮,扛一包上肩,没费什么力。六子先将盐包搁上膝头,再使力,也能上了肩。二楞头身笨,手抱了一只盐包死活舞弄不到肩上去,又害怕挡了别人的道儿,就那么抱着二百来斤的麻袋去上垛,倒也没落下。从垛上空身返回,就见有三四个新来的站在麻袋跟前发愣,老脚行们冷冰冰地说三道四:
“甭瞅啦!再瞅也成不了一朵花儿!”
“闪开!干不了一边去!”
“后生,吃不了这碗饭,别处发财去吧!”
几个人汗道儿横斜的,脸灰灰地走了。还不到正午,眼见这“旱地拔葱”就拔去了三四个人。
中午嚎过气,脚行工房有人担了饭来。老脚行们一时歇了用饭,每人半碗菜,蒸馍倒是管饱吃。六子他们仨也歇了,怀里摸出饼子来啃。大未子的干粮让汗水浸得稀软,二楞头因为抱麻袋,两半拉饼子都揉成渣沫糊在腰肚四周。两人哪敢抛撒,都细细打扫进肚里去。几个北路汉子没防住这一招儿,干咽唾沫,眼神惶惶的,中间宽肩厚背的一条后生,像是打头儿的,到饭担子跟前言说什么,二头儿只是摇头。又听得似要派人外边去买干粮,二头儿却站起身来吆喝了:
“抽烟解溲快着点儿,要干活啦!”
伙夫担了半筐剩馒头走远,北路汉子嘴唇干干的咬牙咬得腮帮子暴筋。六子口渴,只嚼下去一只大饼,有心给北路家分那一只剩饼过去,不知如何开口,踌躇的当儿,下午动工了。
下午,站台这厢城墙似的盐垛搬去不到三分之一,那边的盐垛已经一人多高,搭上了码板。两道码板,一上一下。众人鱼贯上板,讲究步子齐整,老脚行们就喘嘶嘶地喊起号子来:
气要匀,步要稳,
步步登高往上顶!
走一步,颤一颤,
八抬大轿金不换!
果然是一步一颤。六子头回上码板就服了那节奏,似乎比走平路还轻巧。也有不服点路的,脚步踩反,三摇两晃,连人带包闪下码板。所幸盐垛还不高,没伤了人。有几个腿抖得再也不敢上码板,白干多半日也只好走人了。
干到半下午,盐垛起了一房高。头回来吃这碗饭的剩下不到十个人。同一拨招来的北路汉子剩了俩。走空板下来,二楞头嘀咕:
“日他的,二百斤的东西还扛得人腿软了!”
大未子也说:
“黑夜蒸馍还管吃,我吃狗日的二十个!”
六子捏捏腰里的大饼,狠狠心说:
“算吧!北路家没吃干粮还干着哩!不怕人家笑话咱的骨头!”
两位见六子硬气,不再吭声儿,倾了头只管扛包。盂县大山里下来的,还真能输了骨头不成?
老脚行们却全然没事,喊号子喊出花花词儿来:
窑里姐儿,脸子红,
花上两毛闻一闻!
窑里姐儿,奶子翘,
花上两毛靠一靠!
还有些词儿,更花哨,听得六子腮帮子那儿嗖嗖地直冒冷气儿。心说这是些什么人,大明白日地吼喊这一堆腌臜。稍一走神儿,一步不小心踏空了码板,小腿擦着板沿滑下去。亏是脚手灵动,膝盖头朝里拐,“咚”一声跪住了。挡了后边,老脚行们骂骂咧咧的。六子一头冷汗,哪还计较挨骂,收摄心神,再不敢胡思乱想。
新干脚行的中间更有不曾吃食的,直杠杠五六个钟点下来,脚步已挪动不灵,上了码板不由统统腿肚儿发颤了。老脚行们看在眼里,扛包的节奏偏又快了几分。上板下板,嘴里都催,脚下专踩前头的脚后跟儿。连号子也变了“快板”:
走不动嘛,
跑上点儿;
腿发软嘛,
颤上点儿;
鬼催着嘛,
狼撵上啦;
牛头马面,
紧跟上啦!
扛包的圈子转成一股小旋风,又有两位给甩出了圈外,扶了膝盖在那儿干呕唾沫,脸胜墙皮。还有一个,连人带包从码板上颤下来,半天挣扎不起。这么着急赶有半点来钟,六子就有点支架不住,听得大未子二楞头的喘息声也像套绳勒住了牛。看看日头,心说是时候了,怀里摸出最后那只大饼,扯成三片,一人递过去一片。娃娃巴掌似的一片饼,一口叼进半片。六子猛听耳边热辣辣喊声:“伙计!”抬头看,是宽肩厚背那位北路大汉一双喷火的眼睛。到这份儿上,还说什么,啃成月牙形的少半片饼递了过去。
……终于熬到嚎气,大头儿又出现在站台上。大家刚想直一直腰脊,听得大头儿呼叫:
“每人最后来三包,吃蒸馍啦!”
大未子和二楞头都咧嘴要笑,六子蓦地想起判官叮嘱过的紧要话来。低声关照二位几句,三人都操上了十分心思。临了这三包,不再由个人扛包,却是由两人架包,一人帮包,扛包的只要蹭进肩膀去就成。这儿蹭肩,帮包那人就喊一声:
“吃蒸馍啦!”
扛包的接了包,应一声:
“吃蒸馍啰!”
一路小跑去上垛。
几个老脚行上去扛包,未见新奇。紧接着一位新手近前,只见两个架包的扯了麻袋四角一悠,盐包荡起一人多高,帮包的双手凌空劈下来,喊一声“吃蒸馍啦”,那盐包就活活将一个人闷倒在地。那人从麻袋底下往外挣,扭腰咧嘴的,老脚行们轰然吼起来:
“吃蒸馍啰!”
那人从麻袋底捡了一条命回来,缩了脖子再不敢二次“吃蒸馍”。早嚎气扛到晚嚎气,晚间的蒸馍到底吃不成。两行清泪就顺鼻凹无声无息淌落下来。
轮六子扛包时,见那架包的将麻袋悠上半空,六子就趁势儿使双手托了包底。帮包的边吼喊边使力劈下,下边已然撑满。顺利接下包来,六子便兴奋地应一声:
“吃蒸馍啰!”
大未子身矬,六子担心他托不着包底。谁知大未子就地一蹿身,蹦起足有三尺高,在帮包的那一声吼喊里,硬是单臂从半天里夹下那只盐包来。他却忘了应声儿,六子就在高垛上替他吼:
“吃蒸馍啰!”
二楞头着实是笨,双手托了膝盖铺展了腰,就地摆了一只“板凳”。麻包从半天里砸下来,六子心说坏了,二楞头非当堂出彩不可。“咕咚”一声,二楞头的腰身只向下蹲了几分,竟是没事。直起腰还没忘应呼“吃蒸馍”,牛吼一般。
那北路大汉也真不瓤,被麻袋砸个趔趄,冲前去七八步,到底站稳了。上码板的时候,这汉子沙着嗓子,吼了两句二人台:
小妹妹垴头瞭哥哥,
哥哥在太原府吃蒸馍!
吃蒸馍啰——
当天,二十来个试工的新手,沙里澄金。只剩下四个人。
六子他们,从此入了脚行……
我们家乡一带,早年间出来闯江湖的盂县人,大致有如下几个去向。
一是下平山,学生意。县境北端,过了滹沱河,往东插下去二十来里就是河北平山。各色店铺,河北人做东家,负责经营的掌柜多是盂县人。识得几个字,会打算盘,又有人引荐,孩子们就去当学徒。提茶壶、倒夜壶,十年二十年,熬成大师兄二掌柜,分得柜上一半分红利,可算到头。
一是走西口,刮野鬼。历来传说口外吃马肉、喝马血,番邦地面,可也小簸箕儿撮银元,遍地牛羊,弯腰捡钱。我们那一带,有从口外整驮子驮了银元回来的,有脚步探得远走到大库伦现名乌兰巴托成了侨民的,更多的则是有去无还,尸埋异域,野鬼漂泊。
一是下太原,卖苦力。自打督军阎锡山坐镇太原,铺了窄轨铁道,创办电灯公司兵工局,太原渐有发展,新兴行业大量吸收无地农民。盂县山民下得大苦,扛得大件,多在脚行卖苦水。
直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钢厂、电厂、车站、粮库,凡装卸搬运苦力行道里,盂县人依然占多数。盂县人干脚行的何以多,无从考究。或者本土乡情引荐传带是个原因,好比平遥人拉洋车的多,长子家剃头的多。我父亲也有他独特的一番道理:
“咱那一带的人,生就的骡马骨头,能受!不干脚行干什么?”
我在部队时,有次卸车扛过八袋面。复员后给父亲学说,老头子鼻孔里喷气,压根儿不拿正眼来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