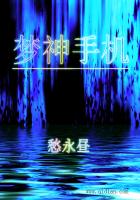第一节
六子在人市儿上逛荡的时候,一眼扫见了判官。那主儿斜披一件夹袄,腆着战鼓似的大肚,正迤逦歪斜朝人市儿走来。六子忙指给大未子和二楞头看,三个人就一齐在马路牙子上立了,抻长脖子龇了牙笑,迎神似的恭候判官来认他们。伙计仨到太原府来找营生卖苦水,无头苍蝇乱扑,竟扑见了本村的熟人。判官早几年就离开村里到太原来闯江湖,他家里没了亲人,便也没个书信回去。有传言他被抓了兵的,有传言他在马路上沿街乞讨的。今儿看他夹袄黑整整的,肚皮圆滚滚的,想必混得不坏。
六子他们却不知道,判官染上了料面,已经成了一个料子鬼。
判官初到太原,由于没人引荐,找不到什么正经营生,日日在人市儿上招摇。搬家、刷墙、打井、挖沟,干点子零工糊口。正赶上“七七事变”,国军四下抓兵,他还真个当过几个月大兵。记得是热天时候,判官和几个打临时的给南郊一家财主打井。歇晌抽烟的当儿,大路上斜刺里走来两个当兵的。还以为是问路的,当兵的却凶凶地喝问:
“干什么的?”
打井的立即回答:
“给人家打井的。”
“国难当头,打个什么井?”
判官多嘴说:
“水井。”
“叭!”火辣辣就挨了一耳光。
赏过耳光,当兵的说:
“走!都跟我们走!”
几个打井的就乖乖地跟人家走。走进兵营,不由分说撕去衣裤,一人换一套军装,连长训话说:
“从此,大家就都是国军弟兄了。当兵吃粮,吃粮当兵。好好干吧!”
吃了几个月军粮,判官终究不安心,纠合当初几个打井的逃跑。两个人翻出营墙,两个人还在墙里,就让发觉了。禁闭了一宿,第二天处置逃兵。连长说:
“要是打仗,统统枪毙!现时嘛,一人四十军棍!”
这打军棍却有讲究。下手轻而听着重,这是一招好活儿;打得慢而数得急,另是一招好活儿。判官平生吃过这么一回痛揍,一辈子记得清楚。掌刑的弟兄,五军棍中总有两三棍出头,棍头儿垫地,皮肉轻省且不说,数数儿的也数得巧。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是这样一种节奏。四十棍下来,少挨十来棍。
打过军棍,掌刑的牵了他们来叫连长验伤。连长见他几个都能行走,笑一笑,摆摆手,免验了。几个人随后脱军装,换便服,屁股都是血淋糊拉的。老兵们都夸赞掌刑的弟兄仗义,棍伤看着重,好得快。随后,弟兄们攒钱为他几个凑盘缠,三块两块的。排长五块,独独连长一人拿了二十块。连长最后赏他们一人一口料面来吸,说是抗痛,省了走出营房一瘸一拐难看。——判官竟是从此种下了吸料面的根儿。
弟兄们送他几个到营门口。连长一个个拍过他们的肩膀,说:
“你们几位都不是当兵的料,各奔前程吧!毕竟弟兄一场,送你们一句话:无论如何,可不兴给日本人做事啊!”
判官一时觉得眼眶子发热,急忙转身离去。多年之后回想,那个转身是标准的队列姿势“向后转”。
判官二次返上太原,太原已经被日本人占了。
兜里有几块现大洋撑腰,屁股上十字横斜的棍花儿也壮胆,判官在太原府大街上横着走了好几天。明园子、暗窑子,东北佬开的赌场、朝鲜二鬼子开的料子馆,直出直进——只是不沾日本人。大洋抖搂精光,判官还是判官,又立到人市儿上卖块儿。打了些时零工,行道混熟了,到底入了脚行。脚行每日扛大个儿,一刀一枪亮真招儿,判官却吃不下那苦来。亏是领班的大头儿见识过他的屁股,觉得此人有点来头,不好轻易辞退他,临了委他一个招工的跑腿儿,每日到人市儿上去招工,招工一名赚洋两角,招足五名,工钱一块。伙食之外,少不得还能来两口白面儿。
这天,六子他们几个在人市儿上瞅见他的时候,判官陡然觉得脸颊上热热的,一定神也瞅见了他仨。
父亲年届七旬,总爱三番五次叙述他早年的经历。他叙述的多半是成功的事例,亦即“过五关”部分。足见任何叙述都是一种选择。当然也可以说,他是属于乐观主义者一类人。
父亲说,他后来在脚行能够立足并且十八岁就当上大工头,多亏那天碰上了判官料子鬼,要不然头一天考工就考不下来。
判官是我们本村张姓,我的祖父辈。据说,他祖父抽大烟,鬼眉怪眼的,村人送号叫“鬼架”。他父亲习沿家风,也抽,典房卖地砍坟松,形容更不如鬼,村人又送号“鬼坯”。到判官,家贫如洗,已无可典卖,吞糠咽菜的,却是虎彪彪一条汉子,他爹要卖他妈——乡下所谓卖“活人妻”——被判官一顿臭揍反锁在屋。儿子治服了鬼坯爹,村人便送号叫了“判官”。判官爷不幸后来染上了料面,令人叹惜。是环境毁灭人呢,抑或是人有自毁的因子?
也许,一切皆可归于偶然。
父亲打工找活儿,偶然撞上了判官;
判官打工,却偶然撞上了抓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