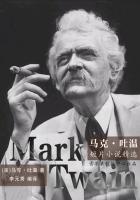大约十分钟后,霍挺领进来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珠光宝气,人很丰满,穿着连衣裙,小腹部有些突出,可以感觉她在有意地憋气,吸自已的肚子。我以为她是国泰花园的负责人,就笑脸相迎着,态度非常谦恭殷勤,她问我什么回答什么,还同她碰杯喝楼兰干红酒。女人吸细细的绿猫香烟,夹在指缝里,会朝空中吐烟圈儿,喝了大杯酒后,开始说自已的内心空虚,形单影只,非常孤独,很需要有人陪着聊聊天,随便聊什么都行。我看她凄凄迷迷的眼神儿,知道她把我当男三陪了。硬着头皮瞎聊一通,然后借口上卫生间,想溜之乎也。女人看出我是个生手,说,“你是头次干这个吧?你好紧张哦,紧张什么嘛!怕我吃了你?”
我语无伦次,说,“哪里哪里,很好很好!”
女人笑了笑,抬腕子看看小坤表,说,“头回生二回熟,今天就算咱们认识了,你陪了我一个半小时,我意思一下!”说着从小坤包里抽出两张百元票子,又给了我一张名片,然后伸手拍拍我的脸,扭着腰肢走了。
女人叫游曼,是南方一家公司在本城的总代理。我对她印象不错。二百元小费,不费吹灰之力到手,送雪百真,我得苦上十天半月才能挣上。我觉得这营生不错,隔些天又去,问霍挺,游曼女士在不在?在的话,我还愿意陪她聊天。霍挺说,游女士不常来,现在有一个要陪的,是个南洋婆,出手很阔绰,就是年纪稍大点。说着又把我带进那间包厢,里面已经坐着那个富婆,很瘦,头发稀疏,露出头皮,眼睛很大,雷公嘴,像只秃鹫。我坐下后,她使劲嚼口香糖,眼睛直勾勾看我。这富婆不爱说话,我发现她喝了不少酒,对谈话毫无兴趣,两眼把我盯够了,才说,“先生不戳(错),走吧,累(你)跟我上楼去哪!”
我知道上楼是怎么回事。跟这样一个又老又瘦的扁平胸富婆上床我可没有兴趣。我没有跟上楼,在舞厅里等一会儿,希望有游曼那样的女士来找我。但时辰不到,真正的夜生活还没有开始,舞厅里空寂无人。霍挺过来了,说那个老小姐在客房里正生气,暴跳如雷呢,霍挺说,“你现在上去还来得及,就说你碰到一个熟人,耽误了一会儿。”
我说“算了吧,她太老了,比我妈年龄还大,如果是游曼,我还愿意考虑。”
霍挺笑了笑,说,“你本末倒置了,是客人挑你,不是你挑客人!”
我说,“你总得给我介绍个合适点儿的,不能让我边陪边恶心想吐!”
霍挺说,“你以为这是谈恋爱呢,你既然是为钱来的,就得无条件地上去,她们就是你的武则天,你的慈禧太后!”
我说,“看来这钱也不好挣,我还是个童身呢,献身也不能献给这么个楼兰干尸!”
霍挺说,“你这么讲究,以后就不要再来了,得罪了客人,我也不好交代!”
我听金毛说过,他有一哥们,六年前就干起这营生,还练了道家功,房中术十分了得,把富婆们搞得销魂荡魄,自已却一点不射精,元气精华丝毫无损。富婆们给他的钱有几百万了。后来,我知道了霍挺也是干这个的,而且还知道,服务生们服务的对象不仅仅是富婆,还有好男色的男爷们。
兆里赛布喜欢看路边的招工栏,从国泰花园门口上了公共汽车,下车就碰到两个招工栏,他们看得非常仔细,上面那些花花绿绿的纸片,让他们眼睛发亮。我说这上面的差使,都是苦差使,报酬低微,东折西扣,剩下的能把自已的肚子填饱都不错了,你们就是打工也不能打这样的工。
赛布已经成家了,老婆叫海树,是马莲窝子后刘家的闺女。兆里的对象叫灵兰,在镇上学裁缝,有俄罗斯血统。赛布说兆里的心气高,找的对象也心气高,人长得很漂亮,兆里不混出个人样,她不跟他结婚。
兆里说,“灵兰很支持我进城,说树挪死人挪活,好男人就该出门闯世界,不是她鼓劲,我还下不了出走的决心,马莲窝子再不好,毕竟乡土难离,不是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狗窝吗!”
我说,“兆里你是个农民,怎么想起开饭馆了?你以前学过厨吗?”
兆里说学过,在山上烧石灰的时候,认识了南山风景区百顺饭馆的店主王百顺,石灰窖停了,就跟王百顺帮厨学艺。后来还到县城的百顺店打过几个月工。红案白案,烹炒炖蒸,都学会了。关健在,他喜欢这门手艺。这好像是家传,兆里说,死在河西老家的爷爷,年轻时就是厨师,老子杨智,在部队服役期间,当的就是炊事班班长。祖孙三代,或多或少,都跟厨案有缘。
说话间就上了龟甲山。龟甲山是个平缓丘陵,绵延十几公里,远看像个巨大的龟壳,南端有座峰丘高耸上去,像扬起的龟头。这荒丘一直是城里人埋死人的地方,里面还有几十个砖厂。有个叫王赤垣的民营企业家,响应市政府改造荒山的号召,斥资数亿元,在山上建生态园,植树造林,还修了几千亩地面积的高尔夫球场和西游记乐园。现在这荒山秃岭二期绿化工程已经完成,生态园向游人开放了。
我带兆里赛布从便道上山,一路都是果林葡萄园,远远的一座佛祖如来的巨大铜像,立在丘坡之上,高达几十米,旁边观世音菩萨、唐僧师徒、诸神诸佛、罗汉金刚,分列左右,被花果树木映衬着,云蒸霞蔚,仿佛进了西方极乐世界。兆里赛布傻看着,嘴里啧啧称奇不止。又看一片栅栏里,圈着许多驼乌、火鸡、珍珠鸡、鹅、野鸭子、鸳鸯,还有骆驼,小象,两人更是大呼小叫,兴奋不已。再往前走,就是大片高尔夫球场,绿油油绵延了好几面山坡,原来的乱坟和砖厂,都被拆迁,球场旁边,依山建了许多高级别墅,一色的欧式洋楼,带花园和小型露天泳池。王赤垣果然是大手笔,只几年功夫,真把龟甲山改造成了花果山。
我就让兆里赛布猜猜王赤垣的来历,两人猜不出,我说,“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会相信,王赤垣十一年前还是个盲流,从陇西跑出来,下火车时身上只有十二块钱,只好靠拾破烂为生,一年后积攒了几千元,租了个小门面,专卖酸菜面,就发起来了。现在光酒店就有八个,还有个几百摊位的商贸城,兼做房地产,是首府十大民营企业家之一了。你们两个好好干,说不定将来也是杨赤垣,赛赤垣了!”
两个人就咧了嘴笑,兆里说,“王赤垣这样的盲流,全中国恐怕也没有几个,他是命里有财运,天生的贵人相。朱洪武还当过叫花子呢,汉刘邦早年是个卖草鞋的,真龙天子转世,我们这样的草民怎么敢跟贵人相比。学王赤垣,我是想都不敢想,我最大的念想,也就是开家小饭馆,就这点念想,还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呢!”
边说话,就到了龟甲山峰顶。顶上有个八角亭子,匾额上有“揽秀亭”三个金字。站在亭子里,整个城市尽收眼底,烟云浩漭,无数楼宇林立着,四顾望不到边际。大街小巷车辆穿行,行人细小如蚁。兆里赛布站在风里,凭栏远眺,说这城市他们的爹是来过的,不过,是从东边来,往西边去,穿城而过,连半天也没有停留。听杨智,赛麦堆讲,穿城的时候正是夜里,黑灯瞎火,城市什么样子,根本没有印象。那时候是逃荒,又是岁寒天,只急着往西边赶路,哪里有心思留心看街景?
三十六年前,戴明理写过的那群逃难者,穿城而过的那条路,现在变成了高速公路,一直向看不到尽头的苍野延伸,伸到兆里赛布出发的那片穷乡僻壤。那些逃荒者已经老了,走不动了,现在他们的儿女逆其道而行之,又到这城市来了。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命运呢?只有天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