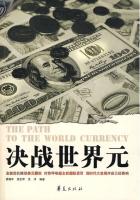薜承此话一出,张水祥心里微一‘咯噔’,暗道:这奴才竟敢将皇上的掌上明珠淳静公主抬出来说事,难不成真的是淳静公主那厢出了什么乱子?
思绪略转,又暗自思索:不对啊!若是淳静公主那里有事,理应由其亲母锦嫔娘娘遣人前来才是,怎会轮到他玉琼宫里的人前来通传?想来必定有诈。
一瞬间的功夫,张水祥的心思己经转了数道:“哼,休得抬出淳静公主来吓唬我。若公主有事,怎不见静萍轩的人前来通传?”虽然这样说话,但其说话的底气却也低了许多。
“好啊,你还不信本公公之言,看来你是真真的活的不耐烦了!”薜承极具气势的对张水祥喝道:“我们做奴才的,哪有资格过问主子们的事情。此事无论是谁宫里的人通传,淳静公主的事却是顶顶重要的。敢问你可是吃了熊心豹子胆,竟然敢耽误淳静公主的事情。哼!”
薜承头颅上扬,极为不屑的斜眼看着张水祥,语气里隐隐还露出一丝幸灾乐祸,大有一种欲陷张水祥于不义的感觉。
见薜承不大的三角小眼里竟然还有着一抹笑意,张水祥心里开始不安起来,暗自嘀咕道:难不成淳静公主真的有事?看来此事还是谨慎为妙,若真是误了主子们的大事,此等罪责可是担待不起的。
想了又想,张水祥腰板硬直双手反剪于后,碍于小太临小槐子在旁,自己这总管太监可不能失了威信,便假意咳了咳清清喉咙,对薜承言道:“你且跟我安静的入内。可记好了,若是你无中生有,扰了皇上此时的雅性,皇上怪罪下来你可是吃不了兜着走!哼!”言毕,从鼻腔里重重的哼了一声,以壮自己声势。
薜承也不与他计较,只阴阴的冷笑道:“你可走快些了,否则还指不定是谁吃不了兜着走呢!”
二人言语针锋相对之时,己行至主殿外。正在殿外伺候的顾嬷嬷,见张水祥竟然领着玉琼宫里的管事太临薜承前来,气不打一处来,急步上前压低声调暗责道:“你脑子进水了?今日皇上好不容易驾临喜瑶宫,你怎能让玉琼宫的人前来搅和!”
张水祥苦着脸凑过头去,附在顾嬷嬷耳边悄语几句,双手微微一摊,表示自己也是无奈之举。顾嬷嬷听罢,脸上神色也是变了又变,经过好一番思想斗争左右思虑,暗想此事确实不敢胡乱作主。这把赌注可是下不得的,皇上对年仅五岁的淳静公主极为宠爱,自己这等当奴才的再有天大的胆子,也是不敢把淳静公主的事情拿来作赌注的。
心里虽是这样想法,却也是非常的不甘心,只得转身狠狠的瞪了一眼张水祥身后的薜承一眼,极不情愿的向寝殿内走去。
不多时,殿内便传来皇上上扬的说话声:“叫薜承进来说话。”
“是!”薜承尖声一应,很是得意的看了张水祥一眼,哈着腰快步进入寝殿。
“说吧,淳静怎么了?”皇上淡声询道,却不看向薜承,而是面对棋盘,手里拈着一枚黑子,目光在棋盘里游走,好似在想下一步该如何落子。
薜承恭敬的跪下回话:“回皇上,适才锦嫔娘娘领着淳静公主,来玉琼宫里与蕊妃娘娘闲聊家常。聊的甚为高兴,却不料淳静公主突然大哭起来。”
“哦?”皇上闻言并未落子,而是将手里的黑子扔在了一旁的白玉棋盒里,转过身来看着跪将在地的薜承,询道:“既是聊的好好得,淳静又怎会大哭起来?”
“奴才们也是不明白,锦嫔娘娘与蕊妃娘娘好一阵劝,才问清原由。原来是淳静公主以为来了玉琼宫里能看见皇上,怎料坐了许久,却不见圣驾踪影,便忍不住大哭起来。”薜承埋头伏跪言道。
一旁的喜妃闻言,直气的切齿暗恨:狗奴才,满口皆是刁钻之言。竟然拿公主说起事来。
虽是气郁不堪,但喜妃脸面上却是露出关切的神态,柔声对皇上言道:“想来公主是想念皇上了。明日一早皇上定要在百忙中,抽出些时间去看看公主才是。”言下之意,自是不言而喻。
薜承闻言却猛的叩首,急急的对皇上言道:“我们娘娘说,原本以为公主哭一下也就没事了。可是公主越哭越是厉害,后来哭的急了,竟然又喘起来了。娘娘急了,传了太医来,太医也是束手无策。说是公主是哭的太过厉害之故。唯有止了哭泣,才能有所缓解。娘娘这才命奴才一路小跑着来到喜瑶宫里,恭请皇上移驾。”
“哦?怎么又喘起来了?”皇上一听急了。
原来淳静公主自幼体弱患有哮喘症,前些时日犯过一次,经太医精密诊疗才刚刚有所好转,若此次再是犯病,恐怕又会拖上许久,吃上许多苦头。爱女心切的皇上,听闻淳静公主身子有恙,也顾不得许多。急忙翻身下榻,急声对薜承喝道:“摆驾玉琼宫。”
“是!”薜承拖长嗓音,高声应道,语调里无不洋溢着胜利的欢欣。
喜妃脸色铁青,看着满盘残局,指尖原本轻拈的白子,被紧紧的揣在手心,五指关节处更是因为太过用力握拳,而泛起隐隐的白色。
皇上大步走到寝殿门口,突然想起被冷落的喜妃,便止住了脚步,回首对其略显歉意的言道:“爱妃先自歇息。朕去看看,若淳静无大碍,朕再回来下完一盘棋局。”
喜妃尽量保持平静,努力的扯动双颊肌肉,拉出一个极为勉强的笑颜,声线略微颤抖的应道:“公主的身子要紧,臣妾在此候着皇上。”
见喜妃如此识大体,皇上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即转身阔步离去。
殿外传来总管太临李忠庆,拖长嗓音的高呼声:“皇上摆驾玉琼宫!”
片刻之后,顾嬷嬷急步进入寝殿内,只见喜妃面色苍白,愣愣的坐在棋盘跟前,凤目内滴滴珠泪无声滑落,双肩也随之轻微耸动起来。
顾嬷嬷是喜妃的奶娘,看着喜妃长大,跟着喜妃进宫,虽是奴婢的身份,但在内心深处却将喜妃当作亲生女儿看待。此时见喜妃如此伤心,也很是心痛,急忙上前轻声安慰道:“娘娘,你可要怜惜着自个儿的身子......”
话还未说完,喜妃便伤心的靠在顾嬷嬷的身上,越发抽泣的厉害起来,同时嗡声言道:“这个贱女人欺人太甚!几次三番将皇上截了过去,今日竟然还敢找上门来哄走皇上。她是真真的不把本宫放在眼里!”
“娘娘莫要伤神,适才皇上也说了,若是公主无碍,便会回来与您下完这局棋的。”顾嬷嬷轻轻的拍着喜妃后背,小心安慰着,犹如当年喜妃年幼时,受了委屈在自己怀里哭泣的情景一般。
喜妃哭了片刻,很快便止住了哭泣,从顾嬷嬷怀里抽身而出,冷冷的看着眼前的残局,伸出青葱般的玉指,从棋盘上呼啦啦的划过。顿时棋局大乱,黑子白子挤作一团,再无章法布局可言,同时嘴里切齿的挤出几个字来:“哼!贱人,你做初一我做十五!这使绊子的功夫谁又不会呢。咱们走着瞧!”脸上露出浓浓的阴霾之色。
“娘娘!”顾嬷嬷看着满桌的黑白乱子,有些担心的轻唤道:“这棋局......”
“收了吧。难不成你以为那个贱人费尽心机,将皇上哄了过去,还会好心让皇上回来不成?”喜妃从怀里掏出一抹丝绢,神态自若的拭了拭两腮的泪痕,淡声说话。那神态,好似适才的痛哭失态与自己毫无关系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