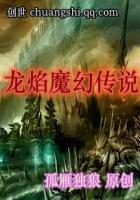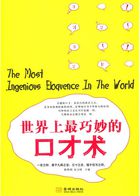虽只是一杯酒,众人却觉得比喝平常七八杯还过瘾,直叫如此美酒只喝一杯太过可惜,于是杨坚一声大吼,叫过几个家丁,要他们按照段熠风的方法再去多弄几个灶台多煮些酒来。段熠风则告诉家丁竹子打通后可作出酒管子,要他们把自己那根铁管换出来收好,到时给送回自己住的院中去。家丁领命而去,一下子增设了十几个灶台,然后依照段熠风的方法便开始煮酒。有了新加入的十几口锅,蒸酒的速度自然大大提高,也就半个小时过后,蒸出的酒便被源源不断地送了过来,众人第一次喝这种蒸馏后的高度酒,自然要过足了酒瘾才行,于是酒不断送过来,然后被众大口喝下,送得越快,众人便喝得越快,也就十几分钟,一群自称海量的汉子在连喝几杯后,就一个个都开始有些晕晕乎乎了,看着一个个都脚步开始打飘的人群,段熠风笑着一个人走出了大厅。
来到厨房,对于新架起的十几口蒸锅段熠风看都没看一眼,直接来到自己架的那口大锅前,看着下铁管方缸中已有半缸酒了,就问是蒸第几道了,从家丁口中得知是第三次蒸馏后,段熠风先弄了点试试,觉得差不多有六十多度,要家丁多蒸几坛这样的送自己小院中去,然后抱着酒缸便往大厅方向而去。来到大厅,见众人都还在吃着喝着高谈论阔着,于是大声说道:“诸位,这有一坛更好的酒,诸位可要试试?”听说还有更好的酒,一群酒鬼哪有不喝的道理,一个个叫着且快快拿来满上,而其中叫得最大声的就属包不期了,于是段熠风先为他倒了一杯,包不期端起酒杯一迎头一口喝尽,段熠风正要问他这酒怎么样,却听包不期大喊一声:“好酒。”然后人就到地上去了。段熠风一杯酒将包不期放倒在地,旁人却无人感到惊讶,反而一个个都笑包不期酒量不行。段熠风找到笑得最大声的,给他酒杯也倒满,这人也是一口便将酒干掉了,豪爽得可谓一塌糊涂,当然,醉倒那也叫一个毫不犹豫。段熠风接连两杯将两人放倒在地,这时总算引起了其他人注意,王轨问道:“此酒有何名堂,竟一喝就醉?”段熠风没理会王轨的问话,而是大喝一声:“拿碗来!”旁边侍候的家丁赶快去拿了碗过来,段熠风选了其中三只大碗摆小几之上,将酒倒满,端起一碗一口喝下,张开嘴哈了口气,觉得不过瘾,再端起一碗喝下,大叫一声:“爽!”再端起第三碗,与众人示意,然后一口干掉,将碗一扔,唱道……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成古愁。”
老子虽没什么诗情,不过三碗烈酒下肚,武松喝了都能过岗打老虎,老子唱一下李白的《将进酒》又有何难,至于盗古用人诗词一说,现在李白还没生出来呢,能算是古人吗?况且老子来到这个世界是来创造奇迹的,而不是来被改造。段熠风如是想到。
唱完了《将进酒》,段熠风再拿起酒缸要为众人倒酒,众人被诗仙豪气感染,再不多言,段熠风要人将碗一字排开后,一手提着酒缸一路洒将过去,堪堪将下几只大碗倒满,作个请的手势,有豪爽的便上前端一碗一口饮尽,于是便又有几人倒地不起,至于那种躲于人后不上前者,段熠风见便会叫一声:国公,谁谁言无酒。便是王轨一介文弱书生样,在他不肯上前时,段熠风一句话,也只能无奈上前端过一碗喝了,不过他之前喝得不多,这一碗喝却是没事,只是头有些发晕而已。段熠风上前正待劝酒,王轨伸掌一拒,道:“莫来。”段熠风只好一笑将他放过。
十几人同堂喝酒,被段熠风一口气放倒了十一人,在场喝过酒还能站着的便只有杨坚、花无常、王轨加上段熠风四人了。杨坚命下人将醉倒之人扶去客舍歇息,让下人们都退下了,对段熠风道:“诗好酒好人妙。先生愿助坚否?”段熠风摇头,道:“作个交易怎么样?”杨坚道:“如何交易?”段熠风道:“我要钱。”杨坚道:“先生若愿助我,何愁富贵不得?”段熠风道:“我喜欢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不喜欢管别人闲事,要我做事,明码标价,做一次结一次。”杨坚笑道:“先生果真妙人也。却不知先生可做何事,要价几何?”段熠风道:“不到万不得已,不杀人,却可富贵一生。”杨坚道:“如此甚好,先生先去歇息,明日一早随我上殿面圣。”这还有什么好说,段熠风一边大摇大摆往大厅外走去,一边说道:“马上送些钱过来,我急用。”出了大厅,他也不能人带路,自己就回了居住的小院。
回到自己住所,见望月还在等他回来,问她吃饭没有,得到肯定答复后,段熠风将望月带入了自己房间。在望月的服侍下,段熠风洗好了脸和脚,也就是在这时,外面下人传报杨府的管家过来了。段熠风和望月来到小院的待客大厅,只见杨府的管家拿着一个包裹在门前等待,段熠风二人走上前去,管家先是躬身行了一礼,然后说道:“这是国公命小的给先生送过来的。”说完躬着身双手将包裹往前递。段熠风接过,只觉入手沉重,便将包裹打开,只见包裹中乃是两串铜钱和几大锭黄金,便问道:“不是说黄金只是玩物吗?”管家答道:“黄金确实乃是玩物,只不过却是贵人们玩物。”管家话一说完,段熠风便回味过来了,就像二十一世纪一样,黄金不能当钱使,却很值钱是一个道理。将包裹递给身后的望月,又对管家道:“将卖身契还给她,将她送走。”说完,也不管两人反应如何,直接就进屋去了。
段熠风进屋后不久,没想到望月也跟着进来了,段熠风坐在椅子上,望月来到他的身前,将段熠风刚才给她的包裹话旁边的桌子上,行了个礼便要出去,段熠风道:“如果我是你,我就会带着这包东西离得远远的,甚至离开周国境内。”已走到门前的望月听到段熠风的话后,停下脚步转过身来,不解地看着段熠风。段熠风又道:“在我向他要钱的时候,他就明白我要这钱是给干嘛的了,所以你不用怀疑他会拿你怎么样,但是你不拿着这钱走得远些,以后会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望月默默地回到桌前,重新拿起桌上的包裹,嘴张了几下,想说什么却又没说出来,段熠风看着她欲言又止的样子,道:“想问我是怎么看出来的?”望月点点没有说话,段熠风接着说道:“忘记以前的事情,那么你将会活得很好,可如果你还惦记着以前的身份,那么你很难得以寿终,我虽然不了解这个世界,但我很了解人,所以听我的话,走得远远的。”望月道:“如若望月可以忘记之前的事,不知可否留在先生身边服侍先生?”见段熠风摇头,望月忙又道:“望月是真心的。”段熠风道:“看得出来,不过正因为你是真心的,所以我不会让你留下来。”望月低头不语,段熠风叹息地道:“去吧,放下以前的身份,好好过一个平常人的生活,如果你能活得很好,也不枉我来这个世界走上一遭。”
送走了杨坚特意派过来试探自己的奸细,段熠风看了一眼主屋方向,一笑后返回卧室,拿起自己的背包检查了一遍,没发现什么异常,也就是说没人动过里面的东西。将包裹扔到床里边,三下五除二将自己剥得只剩下一条内裤,往床上一倒,开始睡觉。
一夜无话,翌日清晨,段熠风又被一阵敲门声吵醒,抬头往窗外看了一眼,发现天都还没亮,不禁低声咒骂了一句,但想到今日要跟杨坚一起去面什么圣,就算此时因昨夜喝多了酒,头还有些不清醒,那也得起床。答应了外面敲门的人一声,艰难地从床上爬起,一边拿过昨日早间换下来已洗好的自己原来的衣服穿上,一边想着明朝时一首很有名的诗: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原乐,睡到人间饭熟时。莞尔一笑,暗道:“干什么都行,就是不能当官。”穿好衣服来到屋外,杨府下人早已将洗漱的水备好,好好地清洗了一番后,回到屋内背上背包便出门而去。
来到屋外,杨坚已是坐在马车上等候多时,见段熠风出来,便招呼他上车。段熠风也不与他客气,一步跨上马车,钻入车内,坐好后,马车启动,往皇宫大内方向而去。而马车之中,杨坚双目看往段熠风下身,道:“在下见先生独身在外,日常生活无人料理很不方便,便好意送先生一个美婢,先生为何不留着享用,却白白将她送走,这是何缘故?难不成先生有隐疾在身?”看着史上最有名的妻管严人物一脸淫/荡之色,段熠风冷哼一声,道:“国公夫人治家严谨,国公府门风纯正,段熠风身为国公府的客人,岂敢恣意胡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