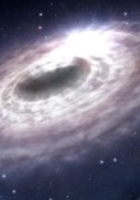一个声音叹惋的道:"春芽子,你就别在那里怒天尤人了,谁让人家是当官的,你是当差的,要怪就怪你自己干吗不出生在名门望族,偏要出生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户。"
沙哑的声音惴惴的道:"****,李阿狗,你凭什么资格来说我是庄稼户,你的老爹还不是个烧黑炭的。"
几个家伙正七嘴八舌的低声嚷闹着,迎面又走来了二十来名秃鹰帮汉子,领头的一个捂嘴打着呵欠,讷讷的道:"终于熬到下半夜了,该你们去享受一下了。"
吵哑的声音惴惴向道:"妈的,别以为你们的头儿会拍香主的马屁就处处以劳模自居,咱哥儿们也不含糊,都是吃粮卖力的小卒子,干吗那么尖酸刻薄。"
白霜鹰暗忖:看情形,现在正值巡夜岗哨换班的时间,返回的路上困难重重,万一不留神露了行踪的话,可就前功尽弃了,还是找个地停留一阵子,等巡夜弟子交班完毕后再回返。
一念至此,他游目四顾,准备搜寻一处安逸的角落来藏身。扫了一遍附近的环境,没发现有合意的地方。
他怏然的摇了摇头,这时,那些巡夜的弟子已经远去,他长松一口气,从暗角里闪身出来,正准备飘身转移,一只眼睛不经意的发现到这栋矮矮的石墙瓦房上方横排着五扇专门用于透风的窄窗,其中有一扇窗还是开着的。
仔细一观察,窗户离地面约有五米高,窗口很狭窄,但只要不是大胖子就能钻得进去。白霜鹰惬意的一笑,把手里的长剑竖直的别在背腰的武装带上,搓了搓手,弹身拔离地面,五米的高度对他来说是小菜一碟。他身子在五米的空中翻平,头部对准那扇窗口,旋即就火箭般的疾射了进去。
射进窗户后,他的背部紧紧的贴在里面的墙壁上,双目如电的探视着房内的动静状况。借助房内另一端窗户射进来的几缕昏暗的光晕,白霜鹰发现这间房屋很宽阔,里面除了成堆成山的纸箱和麻袋之外,就是偶尔传来几声老鼠的尖叫和窜蹦时弄出的声响,还有就是一股股霉气硬往鼻孔里扑。
白霜鹰松弛了一下神经,纵身跃到地面上。他原地静立,歇息了一下后就小心翼翼的,轻手轻脚的朝四下搜视了起来。
这间宽大的房屋里到处堆码着纸箱和麻袋,显然是一间陈放物资的仓库。
白霜鹰摸到亮光稠密的地方,借黯淡的微光看到几个麻袋已被老鼠啃得大框小眼的,白花花的米粒和黄澄澄的谷子正从这些窟窿里流得满地都是,几只胖乎乎老鼠正叽叽喳喳尖叫着,扑兹扑兹的吞噬个不停。
现如今,外面的许多贫民百姓都揭不开锅了,这些枭霸豪强的军粮竟多得把耗子都给喂肥了。
此外,屋里还堆叠着一大捆一大捆的军服背褥,一大纸箱一大纸箱的胶鞋皮靴,多得足以供应得起万把人的队伍。
是的,这便是秃鹰帮益阳堂的军需仓库。
血魔帮敛财聚富,穷兵黩武,干戈连绵,战事不断,可仍有成百上千的灾荒流民踊跃的,自告奋勇的前来投效。是的,这年岁里,天灾人祸,官府无道,贫苦老百姓是饿殍遍野,衣食无靠,与其坐以待毙,白白饿死,倒还不如铤而走险投向血魔帮的阵营,管它是邪魔歪道还是明门正派,只要能吃饱穿暖,能让自个儿的生命多苟活一天是一天。平心而论,古往今来,贫民百姓就图这么个简单的目标,至于信仰、抱负、志向,那简直就是扯淡,欺人之谈。
白霜鹰在仓库里逗留了少许时光,估计到巡夜的弟子已经换完班了,他正要抽身离去,忽然,眼前用帆布盖压着一大山物品引起了他的注意。
出于猎奇的心态,他想看个究竟,于是就上去一把将帆布掀开一角,赫然露出一件件木箱子来。
白霜鹰摸了摸光头,拔出长剑撬开一个木箱子,哇!里面塞满了黑漆漆的球状物体。他好奇的拿出一个黑球捧在手里跑到光线好一点的地方准备看看究竟是什么新鲜的玩儿。
只见,这黑球有一个红苹果那么大,或者更大一些,通体是黑漆漆的,散发一股浓郁得呛鼻的异味。
白霜鹰愕然一怔,咦!这不就是那威力巨大,杀伤力强劲的火雷弹吗?据说这火雷弹是戍边部队装备的重型火器,压箱底的法宝。戍边部队就是凭着这种神兵利器多次击溃善骑善射,骁勇彪悍的契丹兵。
白霜鹰激愤的掀开帆布仔细一看,满装火雷弹的木箱足足有上百件,这可能只是一部分,尚没发现的可能更多。
白霜鹰惴栗的怔了怔,睹忖:这玩艺儿厉害很,是防御城堡的上佳之远,若影子军队要正面强攻益阳堂的话,只要这东西一出,影子军队的那些兵娃子怕会要血肉横飞,尸骨无存了。为了防患于未燃,最好的方法就是要把这些东西干净彻底的毁掉,可是现在又不是恰当的时机。白霜鹰习惯的用手去抚摸后脑勺,后脑勺现在是光秃秃的了。悒愣了片刻,他决定先不轻举妄动,记牢这间仓库的位置,再从长计议。
他把打开的箱子照原样盖好,再把掀开的帆布恢复成原来的样子,随后轻捷的启开一扇窗户飘身泻了出去。
返回的路上,白霜鹰把身法展到极致,一路如仙境飘来的风烟似的躲过一个接一个岗哨,像呼吸一样简单的避开一双又一双的眼睛,不出一刻钟就回到了教练场上,松了一口气,正欲穿越教练场返回左侧的寝室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