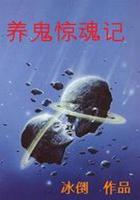那个年代,人的思想早就开始开放,但火葬场这种地儿怎么也放不起来。回到屋子,我不敢把那白布留在身上,最后丢在了桌子上头,心里一直想着事儿。
这几天本来就天气闷热,我该不是下午中了署所以花了眼?
那老头光说是半夜,又没说个确切的点。
这天我一直等到晚上十二点,场区里早就没了人影。我这两间屋子不大,一眼就能看个通透。外屋的白布就那么放在桌上,或许是心里作用,我只觉得这屋子都有些不对头,具体哪儿不对又说不上来。
要说一直等,我等了三四个小时,偏偏到了半夜十二点过,迷迷糊糊之中莫名的一股一股浓烈的睡意传来,半坐在床边居然就那么睡着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做了一个梦,再次出现在眼前的是一处走廊通道,我吓了一跳,这不是烧死人的那条走廊么?我怎么又回了这地方。此时的这走廊一片安静,我发现我站的位置正好就是这地儿最后的一段,而再往前头就是火化炉。
周围一片冰冷,就像是整个走廊的温度都极低一般。更让我害怕的是,此时,在梦里头我似乎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的身子,一步步的顺着这走廊就往前走。
过道里头的灯全都开始一闪一闪,我冷的直打哆嗦,像是这周围有什么东西在看着我一般。
终于,到了这走廊的尽头,火化炉的铁门关着。
“咚咚“的声音就从这炉子里头传出来。”
而此时,一旁老旧控制台上指针还在晃,分明是这炉子里正在烧。我骇了一跳,因为这时候,炉子铁门的声音极大,每响一次,那生锈的闸门就在抖。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里头拼命的挣扎,一个劲的锤门一般。
我吓的响扭头就跑,但根本控制不住自己的身子,整个人麻木了一样的离那铁门越来越近。就在最后,走廊的灯光闪的越来越快,我只觉得自己身子开始浑身发痛。就在这时,一阵吼声从那铁门里传来,那声音显得很是狰狞,有些像人,又有些像是动物。
就在这时候,那叫声一停,连带着里头撞铁门的声音也消失了一般。
昏暗的灯光下,只有我一个人站在这尽头的位置,就看着这生锈的铁闸门,一点一点的,像是要打开一般。
我浑身冰冷,突然,一股针扎的感觉从我胸口传来.
从床上猛的就从床上坐了起来,已经满头大汗,一看屋子的钟,这时候已经快半夜三点。刚才的梦把我骇了一跳,愣着坐了两分钟,梦里头的那吼声似乎都还在我耳边。
我猛的站了起来,那布条还放在外屋的桌上,住处显得一切正常。
我心头狠骂了两句,怎么就做了个这种噩梦?大热天的脑壳晕乎,心安理得就不怕,别自己吓自己。
洗完脸之后,我还是从箱子里拿了点米,把桌上的白布一拿,出门之后,黑漆漆的场区一片安静。晚上的冷风一吹,整个人都清醒了不少。
宿舍小楼外头是个进院,左右载着两排树,我心里安慰了自己半天,还是找了出路边,把这白布往地上一放,就冲着泥巴旁边撒了把米,堂堂大学生来干这种事儿,大晚上的我还生怕不够,把兜里装的米都放在这布条周围,这才一咕噜的回了屋。
当晚我睡得很轻。不知道什么时候,只是隐隐的听到外面的进院里似乎有脚步声。有一回打开大门开了一眼,空荡荡的树中间的路,哪里有什么人?
而我丢的白布和米还在那路边上,根本就没出什么事儿。我下意识的松了口气,回了屋子继续睡觉。
到了第二天天亮,由于睡眠不好浑身没劲。我收拾好衣服夹着公文包刚出大门,就看着三三两两的人围在树子的路边。
我赶紧走过去看,周围的都是宿舍的职工,大清早的还在有一句每一句的议论着。
”咋就死在这里了?快去找人,把这东西给清理了。“
一个妇女穿着碎花群,说的话很是难听,
“我咋知道,大早上一出门就碰到个这种玩意,这不一整天都晦气,也不晓得是哪个龟儿子。”
我心头一惊,这地方可不正是我昨晚上放布条的位置,而此时,这路边哪里还有什么布条?一只花猫死在这儿,而这只花猫,不就是老魏抱着的那一只么?我只觉得背心的都有些发凉,这猫等着眼睛,根本就不知道死之前经过了什么,浑身都沾着米,周围的泥地里,到处都是抓痕,泥巴散的到处都是。旁边两三个人看着脸上都有些害怕。就在那放布条的地方,只剩下一滩似乎烧过的灰烬。
“小胡科员,是您咧?”
那大姐笑呵呵的打了声招呼,“您还好吧,我咋看着您脸色有些不对。”
我声音都有些哆嗦,不敢再去看,只是“哦”了一声。赶紧顺着道朝着办公楼的方向走。
远远的几个男女还在身后骂。
“这胡科员才来半年,什么时候学会端架子了?”
“可别这么说,人家可是大学生分配,机关的人都那样。他还好,你没看其他几个。就说那姓李的,走个路脑壳都能翘到天上去。多说几句还给你小鞋穿。”
那大姐话音一转,继续开了口,
“你说这到底是谁这么缺德?把猫弄死了丢在这儿,真是天杀的祖宗丧德的货。”
远远的我就当没听到,脚底下走的飞快。
之后的生活倒是没再出什么奇怪的事儿,但这一回就已经把我骇破了胆子,不管我自己怎么在心理安慰自己,说这是巧合,巧合,读了这么多年书,可别又栽在这些歪风邪气上。
我又开始了在火葬场上班的日子,天天蹲在办公室,一转眼几个月就过去了。也是找了个时间去周围的乡里买了点补药之类的,寻个由头送给那魏老头,嘴里头说是感谢他。这老头笑呵呵的把我科员长科员短的叫,他好喝酒,带着我下了火葬场里为数不多的小馆子。
几杯酒下肚,魏老头嘴里也就“开了门。”
“我说小胡啊,这办公室里头的金五角(一种酒),也就你能提出来给我这糟老头子整咧,别说,这玩意还真带劲。”
我扭头瞟了瞟桌子边上的金边箱子,仰头也是闷了一口,辣的喉咙直痛,“魏叔,这儿还有半箱,全是我去顺出来的,等会你都给带回去。”
看我有些犹豫,这老头拿着酒杯子就开了口,
“小胡,你这毕业出来也不容易,怎么想的,就来了我们这儿?“我则是一句话比一句假,
”都是为国家做贡献,当不得那些。“
当晚一直喝到十点来钟,小馆子里头就只剩这我们这一桌,魏老头脸上都带了红,我脑壳也整的有些晕。就在这时候,这老头的声音小了下来,
”小胡,有些事你还是不知道的为好,那天那具尸体运进来的时候,粘了不该粘的东西,那尸体有问题。你们下屋进炉房,已经有不干净的东西盯上了你。那只猫我养了这么多年,因为它当时也在那里头,所以我用它代你去消了这场邪。“
我心头一抖,魏老头喝的醉醺醺的,偏偏说出来的话让我眼睛都瞪了起来。
”小胡,火葬场这种烧死人的地方,说白了就是送死人最后一段。有些东西,是看不得的。“
到了后头,这老头应该是喝多了酒,越说越邪乎,我听的浑身不自在,口干的一整杯酒就闷了下去,差点呛了出来。
就在这时候,突然,这看似醉了的老头瞟了眼这小馆子的门外,那外头是条大路,这个点了早就漆黑一片。这老头眼睛直勾勾的盯着外头,我也跟着去看,突然,魏老头一把把脑壳扭了回来。
”娃子,别往外看。“
我心头一惊,老魏的语气显得有些低沉,眼角的余光瞟着外头。这个点的大路上空荡荡一片,除了边上的树木和绿化带的草丛,哪里有什么东西?
过了好一会儿,老魏才拉着我继续喝酒。一直喝到十二点,之前老板一直不好意思来催,看我把老魏扶着出门,我肚子火烧一样扭头就想吐,正好从兜里掏钱。
老板是个中年妇女,笑嘿嘿的走到门口送,
“胡科员,别给咧,给您记单位账上咧。”
我愣是把钱塞了过去,这老板娘才看着一手提着酒纸箱,一手扶着魏老头越走越走。等到没了影,老板娘脸色立马垮了下来,把钱往兜里一塞。
“呸,报账都不会,还带邋遢老头耽搁了老娘半夜。那魏老头神神叨叨的,往我这儿一座,一晚上搞的老娘生意都不好。”
这就是我刚到火葬场之后的一件怪事。在此之前我打死都想不到居然能碰到这种事儿。一直在这地方又工作了半年,之后倒是顺顺当当,没再碰到什么邪乎的场景。
但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