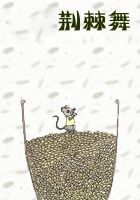转眼之间,中秋节就到了。在革命的年代,传统节日就像被一棵伐倒的大树一样,虽然枝干全不见了,但根可不容易刨干净。何况,大家说了那么多遍的“忆苦思甜”,也得多少给人一点儿真甜头吧!为此,集训队的食堂极其难得地烤了一批月饼。没有莲蓉,没有香油,只是最简单的枣泥馅。但是,对于这种甜得烧心、干得噎喉、沉得坠胃的月饼,它们的硬度更让人记忆深刻。
“我给你们讲一个笑话,”宋大洋挥手让现场安静了下来,然后神态俨然说了起来,“有一年,我们农场做了一批月饼,比这个还难吃,最后大部分都没有卖掉。过了一年又到了中秋节,大师傅又从库房中把它们端了出来,居然还没有长毛。大伙儿当然不满意了,说不浪费粮食也就罢了,为什么每个价格还高了五分钱?人家回答得倒是振振有词:‘今年提价,是因为把一年的仓储费加上去了!’”
“这个,倒符合政治经济学的原理:成本决定价格。”一片哄笑中,冯晓白冷静地说了一句。他是全队中最刻苦的学员,平常看书也多,什么《资本论》、《反杜林主义》都认真读过,还细细做了笔记。
宋大洋平常对他总是礼让三分,可是今天却不服了:“照你这么说,废品的价格最高。谁都不买,它一年年下来不就层层加码了?”
眼见两人争了起来,薛新雨赶紧插口打断,“冯哥说得也有道理啊,文物就是越旧越值钱。你们不知道,过去一张错版的邮票,当时谁也不要,如今可要换一头牛呢!”
尽管巧妙地偷换了概念,但薛新雨自己心里依然觉得这件事实在荒唐。但究竟哪里不对,他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薛新雨很快就发现,甜不但留在舌头上,更弥漫在很多人的心头,尤其是老一代的棋手们。这两天,他们破天荒地接到了参加国庆招待会的邀请函,这可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非但如此,这天,薛平湖收到了政协送来的一张戏票,请他周日去文化宫观看一场新出炉的样板戏的首映式。当然,它很快就落到了薛新雨的手中了。
这天一大早,薛新雨就忙乎开了。他穿上了干净的衬衣,套上了父亲自己平常都舍不得穿的灰涤卡中山装,脚踏全家仅有的一双皮鞋,神气活现地出了门。对于他的好运气,大伙儿心里羡慕,嘴上却忍不住要奚落一番:
“真是驴粪蛋子表面光!打扮得这么立整,又不要你去登台表演?”
“谁说的?等回来给你们唱一曲‘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保管震得你们大小便失禁!”
薛新雨丢下了一句脏话,兴冲冲地下了山。还没走多远,他突然听到后面有人叫自己的名字,回头一看原来是舒梅。她小脸红扑扑的,身上还背了一个大包。原来,最近天变凉了,她要将夏天的衣物送回家去,顺便将御寒的毛衣带回来。薛新雨当然二话没说,就将那个包放在了自己的肩上。
班车到站后,他们又换了两遍公交车,最后舒梅带着他来到了一个很气派的四合院中。据说,她家住在这里已经超过了上百年。可是,如今搬进来了很多外来户,而主人反而被挤到了一个背阴的小厢房中去了。
一进门,薛新雨就忙着敲煤烧火。舒梅虽然年纪小,但很会做饭,不过一个时辰,就将两大碗炸酱面端上了桌。薛新雨见她一脸满足的神情,虽然心里有一丝难过,但还是竭力装出了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问她国庆放假准备怎么过。舒梅说不过多放一天而已,准备洗洗衣服就行了。薛新雨说自己和室友已经商量好了,打算去水库野营,如果舒梅愿意的话,可以一起去。舒梅犹豫着说:“你们都是男队员,带上我恐怕不方便吧?”薛新雨拍着胸膛说:“没问题,我们该摸鱼的下水,该捉蛇的钻洞,该砍柴的上山,正好缺一个看守大营的。你只管坐在那里看东西,保管一个指头也不用动。”
饭后,舒梅收拾自己的衣物。薛新雨没事干,就随便翻书看,很失望地发现舒家的书虽然不少,但全是俄文原版的大部头,连本连环画也没有。原来,舒梅的母亲曾是建国后公派的第一批留学生,自然成了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的崇拜者。舒梅说家中原来的藏书有一屋子,可惜全烧了。又说咱们集训队中喜欢读书的人真多,尤其是陆鸣,非但“老三篇”背得管瓜烂熟,还能吊几句古典诗词。薛新雨听了刺心,赶忙打住说时间不早了,早点儿送他去车站,免得抹黑走山道。
送舒梅到车站之后,薛新雨独自来到了文化宫。他发现,今天的文化宫就像是各种冷色调的大聚会。来宾无论贵贱高矮胖瘦老幼,全逃不出蓝黑灰绿的色谱,偶尔也能见到一两个穿艳服的人,那也是友好国家的外交官或少数民族同胞。薛新雨乘兴而来,可是真到了门口却胆怯了,因为就在片刻之间,他竟然发现了好几个在纪录片上才见识过的人物,顿时心脏开始“突突”。好不容易挨了进去,像没头苍蝇乱钻了一阵,薛新雨才知道前台那些摆满了鲜花果品的桌子与己无关。他的座位在最右边的出口处,旁边还紧挨这一个厕所。从这个角度看舞台中央,无论电影还是话剧,都等同于皮影戏。薛新雨落座后,抬眼一看,更加大惊失色,因为坐在左侧的人竟然不是别人,而是史幽红!看来,“有关方面”的考虑非常周到,绝不会偏袒“南薛北史”任何一方;而薛平湖和史瑞虎虽然势如水火,在偏爱孩子方面却同出一辙。
史幽红昨晚就离开了东华观,今天是从家中直接赶来的。薛新雨见了她,就像老鼠面对一块来路不明的奶酪,既想入非非又想逃之夭夭。在这个除了演员没人会化妆的时代,史幽红的审美观竟然退化到了蚕宝宝的水平:一条丝巾细心衬在领口,一根丝带精心系起发辫,一双丝袜小心藏进裤腿。可即使如此,在这个偏僻的角落中,她依然是一朵开放在午夜的兰花。突然见了薛新雨,史幽红似乎也很意外,不过嘴角马上就撅起来了,似乎薛新雨是那个不时散发异味的厕所的一个构件。
节目开始了,舞台上一时龙吟虎啸,一时如泣如诉,一时血雨腥风,一时欢歌笑语,真是精彩纷呈。可是薛新雨头脑中却一片空白,像个傀儡一样,别人鼓掌他就拍手,别人欢笑他就咧嘴,别人流泪他就皱眉。演出结束了,尽管史幽红不乐意,可两人还得结伴一起回去,因为天色已经晚了,而回程的班车也只有最后一趟了。
车辆开动之后,史幽红从包中拿出了一个饭盒,打开看了一会儿,才从中挑了一个豆包塞给薛新雨。薛新雨已经饿坏了,也没说什么客气话,因为这一个星期中,已经是第三遭“吃软饭”了。
“你们女队员真有本事,总能搞到好吃的。我来了好几天了,都不知道厨房的门是朝哪边开的!”
“因为你没有方向感呗!”史幽红听了,只是不咸不淡地回了一句。
一路上,史幽红的目光都飘在窗外,而薛新雨也目不斜视,直直盯着前面司机的脊背,似乎人家干过什么缺德的坏事。到了班车终点,天完全黑了。至此,薛新雨的尴尬才缓解了一点儿,因为走山路不必并排而行;而史幽红更是暗中庆幸,以前她从未这么晚回来过,身边有一个男子相伴总让人安心一点儿,尽管这个男子本身不太让人放心。
两人一前一后走在路上,听着虫鸣啁啾,枯叶飒飒。天地之间全是一片墨色,浓一点儿的是山,淡一点儿的是川,完整的是石,参差的是树,点滴的就是飞鸟或者飞虫。偶尔一两点光亮,也化不开这种无边的混沌。突然,薛新雨开口问了一句。
“史姐姐,你觉得——你觉得围棋像什么?”
史幽红本来对他的第一印象就糟糕透顶,而如此良夜,这个小色狼兼大呆瓜又提出了一个如此无趣的问题,嫌厌之心更加浓烈,忍不住想说:“围棋不就是抢地盘吗?除了像军阀土匪黑社会,还能像什么呢?”可是话到口边,却突然变成了一句反问:“那你觉得呢?”
薛新雨见她肯开口搭话,心里高兴异常,赶忙把自己的想象和盘托出:“我觉得像天上的星空。你看,北极星就像‘天元’一样占据中央位置,众星都围着它转;围棋有四个星位,正对得上古代星象中的‘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北斗七星弯弯曲曲,看上去多像一把诡异的‘妖刀’!银河倾泻而下,好似‘大雪崩’的定式;而彗星长长的尾巴,是一路打下去的‘征子’;如果恰巧有一颗流星飞过来,那就更妙了,对于这个慌不择路的孤子,干脆任其一路狂奔,它自个儿就会把自个儿耗死了!”
秋季的星空是一年中最寂寥的,而中秋之后,下弦月要到半夜才升出来。所以,此时的夜空显得分外明净清澈。听他一通乱扯,史幽红忍不住也来了兴致:
“你发痴啊?围棋可不像你形容得那么天马行空,也没有那么宁静和平。每一颗星距离都成千上万光年,好不容易走近了,杀气也早消磨在路上了。在我眼中,围棋就是种蘑菇的游戏。你种白的,他种黑的,还可以使坏拔掉对方的。到了收工的时候,大家一起数一数究竟谁的多。”
“太有趣了,这个比喻真是又简洁,又形象,我怎么没有想到呢?”薛新雨赞叹道,欢喜的声调中掩饰不住夸大的成分。见他如此谦卑,史幽红本已矜持到了嗓子眼的心突然没了支撑,开始做自由落体运动。
“你的棋也很——很不错,两年前的我,还不一定就能下赢现在的你呢!不过,你以后不要再叫我姐姐了。一是我不爱听,二是让大人听到了,还以为我们史家以大压小欺负你们薛家呢!”
说完这几句话,史幽红没有再发出什么声息,但笑意却洋溢了出来。薛新雨的耳朵听到了,眼睛也看到了,可是鼻子却出毛病了,竟然闻到了丝丝江南才有的桂花香。可是,他的绮思不过浮现了片刻而已。等到遥遥望见了山门,史幽红转过头来,脸色突然转喜为嗔:
“想要讨好我可没有那么容易!我早就明白了,上次那盘棋,你是故意输给我的。可是这样一来,我就更瞧不起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