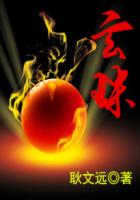“我梦到你现在过得不好,梦里我一直哭,一直哭。”
许多年后,听到颜子健这句话的那一刻,我的眼泪迸了出来。眼泪一旦断了线就开始不听话,心被撕裂成一块块,鲜血淋漓,整个世界灰茫茫一片。周围人不清楚这个女人为何在新年里眼泪鼻涕口水一起流,头埋在身体里,跌在地板上语不成句,恨不得埋进地底下,像个白痴。
“是许愿吧,看这虔诚劲儿,多有素质和情操。”
“被暗器击中了吧,你看看她抱着头呢,大家小心。”
“是不是要生产了……”
他们不知道,电话那头的那个男人,我们走过了金融危机,走过了禽流感,走过了四季变换,走过了时间荒野,走过了锦瑟年华……脑袋里的片断蜂拥着跑火车,未来没有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时间的手轻轻划过,过往全成了水彩画上虚幻的背景。2003年,我们还是天之骄子,带着“社会主义一块砖,哪儿需要往哪儿搬”的热血和豪迈的梦想从四面闯入彼此生命。打打闹闹但是最接近幸福的日子里,从绿意盎然的春走到白雪皑皑的冬,从校外一条街走到车水马龙的CBD,没有人怀疑我们会牵着手一起走到老;1999年,他在东北的某个小镇埋头苦读,我在南方水乡街头大快朵颐,身边围绕的是彼此的青梅竹马,我们只是13亿人中最基本的关系——祖国同胞;1989年,我们都是祖国的花骨朵,没有忧愁,万千宠爱于一身,每天唱着“娃哈哈”把自己打扮成花仙子,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交给警察叔叔,做梦一觉起来变身黑猫警长抓住偷土豆的小偷,维护森林安全,互不知道世界的那头有那么一个人等着自己,蓄势待发。此去经年,我们互相走出彼此生命,他身边站着的是温良淑德的小护士,我选择了本性醇厚善良的医生方玮,多么默契又讽刺……那些最干净的梦想和鲜活蹦跳的豪情在时间的黑洞中消失殆尽,曾经的感天动地被收回,《人鬼情未了》里现实的躯体与山姆穿膛而过,挣扎无谓,定在当场,我们最终成了滚滚人潮中无干系灰蒙蒙的一张脸。
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熙熙攘攘的人群正在倒数,笑容灿若星辰:8、7、6、5、4、3、2、1……烟花划亮夜空,一个劲地响在耳侧,跟不要钱似的。恍惚中,我仿佛又看到某一年太阳下颜子健笑得纯白的脸,“你要对我负责”字字铿锵。水草还夹在头发上,明亮得晃人眼球;后山上阳子的手势青春无敌,“快点,要被我老妈追上了就死翘翘了”;课堂上冬彦妮提醒我背九九乘法口诀表,老班的粉笔头被我一把接住后,黑板擦盖在我镇定自若的脸上;人声鼎沸的大院里,黑白电视机里白素贞和许仙生离死别,春一航讲大话,澄明清澈,“我们永远不要分开,长大了我要保护你们一辈子,把你们仨都娶回家当娘子。”英勇无畏的模样不比董存瑞差半分,似乎他是在舍生取义。
“老板娘,有大脸雪糕吗?”阳子在小卖部里喊得豪气,老板娘说有,“好嘞,给我们来4支冰棍……”
春一航殷勤吆喝:“来来来,去我家看《黑猫警长》吧?我批准。”“好啊,好啊。”我和阳子拍手叫好。“一人让我亲一口……”
秋小木问冬彦妮:“你喜欢吃果丹皮还是酸梅粉?”手里紧攥着花花绿绿一手的分票。冬彦妮说:“果丹皮。”秋小木说:“好,那我们就吃酸梅粉吧……”
长镜头越来越远,越来越远。那时候,我们不怕跌倒、不怕丢脸、不怕挨骂,更不怕天下无不散之筵席;盼着放学,盼着长大,盼着过年,买新衣服新鞋子穿着睡觉彻夜欢喜;吃西瓜每块都咬一口然后“俱”为己有;骑着比自己高一倍的自行车无人驾驶般在街上左冲右突;背着“炸药包”蹦跶着小碎步上学校;个子参差不齐的小伙伴异口同声地树立同一个种太阳的伟大愿望:“种出来的太阳一颗挂在南极,一颗挂在北冰洋,一颗挂在冬天,一颗挂在晚上……”稚嫩的日子在耳边如风拂过,过了就过了,一切都那么简单、干净、纯粹。
一年就这么玩完了,Game over。其实完的又岂止是一年。2012年,末日没有降临,80后已经从青春下游出走。谨以此文献给努力过、奋斗中、轰然老去的80后。青春走过我们,留下了什么?又带走了我们多少宝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