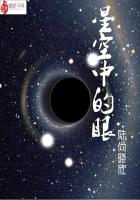李耳在这“虚心静观体悟”的一刹那间抓住了“道”,就像一颗巨大的“恒星”,几乎把整个宇宙都照亮了。这就是有了“道”,才有宇宙,才有天地,才有万物,才有人类,才有社会,才有生活……道,是至高无上的,是“先天地生”,是“天地之根”,是“象帝之先”。这就完全打破了当时的传统观念,把上帝和天等同,而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现在则要由“道”来指挥一切了。
《道德经》中“道”字的出现,共74次,其基本的涵意是,事物运动变化所遵循的轨道、轨迹、规律、规则、原则等,但李耳显然不满意于这种基本涵意,他把“道”提升到高于一切的高度。在李耳看来,做为世界本体的“道”,是不可言说,不可名状的,“道可道,非常道”。因此,是无法给它起名字的。他抓住“道”继续发展、推衍和升华。
李耳的思想升华,是与他担任史官的长期思维定势有着密切的关系。史官思维的一个特征,就是要“推天道而明人事”。
从形式上来考虑,史官负责的领域是很广的。既包括天道,也包括人事,这就为其把天道和人事结合起来考虑准备了条件;进一步看,史官之天道观,也并不是进行纯自然的研究,而是和人事的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他们观察日月星辰等运行位置的变化规律,一方面是为了制定历法,指导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占卜人事的吉凶、国家的兴亡等。这方面虽然有别,但是,在人事必须顺从天道这一点上。却是非常一致的。这种工作的性质使得史官形成了把天道和人事结合起来进行思考,并从天道来推明人事的习惯。
李耳担任了多年的“周室守藏史”,他的工作就是为上述两个目标而进行的。他现在回想自己走过的思想转变历程是极富有意思的。他这个人在治学上有句格言:‘知人者智’,也就是说在研究学问上,一定要懂得前人和自己的同行在这方面的建树,只有懂得了他人学问的精髓,才能丰富自己的智慧,发展自己的才学。他想到这里,走到《鲁史》书简前,不由得想起他的好友,鲁国史大夫梓慎。梓慎是个大阴阳家,善于用天道来推衍人事,他清楚记得梓慎给他讲的一件事,便翻出《鲁史》,只见上边记着那次谈起的事:
鲁襄公二十八年春天,没有冰。鲁国大夫梓慎说:“今年宋国、郑国大概要发生饥荒吧?岁月应当在星纪,但都已超越了玄枵,这是因为要发生天时不正的灾荒。阴不能胜阳,蛇乘坐在龙的上边,龙是宋国、郑国的星座,宋国、郑国必定发生饥荒。玄枵、虚宿在中间。枵,是消耗的名称。土地虚而百姓毫,怎么能不发生饥荒呢?”
夏天,齐侯、陈侯、蔡侯、北燕佰、胡子、沈子、白狄到晋国朝见,是因为在宋国那次结盟的缘故。齐侯准备出行,庆封说:“我们没有参加结盟,为什么要向晋国朝见?”陈文子说:“先考虑侍奉大国后考虑财物,这是合乎礼的。小国侍奉大国,如果没有获得侍奉的机会,就要顺从大国的意图,这也是合乎礼的。我们虽然没有参加结盟,怎敢背叛晋国呢?重丘的盟会,是不可以忘记的。您还是劝国君出行吧。"
卫国人讨伐宁氏的亲族,所以石恶逃到了晋国。卫国人立了他的侄石圃,以保存石氏的祭祀,也是合乎礼的。
邾悼公来鲁国朝见,这是按时令来朝聘。
秋季八月,举行大雩祭,是由于大旱。
对了,李耳又想起梓慎另一回用望气的方法进行过一次预测。望气也是古代星象学中的方法之一。望气之气有云气,也有日月星辰之气,还有极光,甚至还包括地气,内容也非常复杂,不是一句话能说清楚的。李耳翻到了这另一次的记载:
十五年春天,将要对武公举行大的祭祀,告诫百官准备并斋戒。梓慎说:“大的祭祀那一天恐怕会有灾祸吧!我看见了红黑色的妖气,这不是祭祀的祥兆,是丧事的恶气。难道会应在主持者的身上吗?”二月十五日,举行大的祭祀,叔弓主持祭祀,在奏龠的人进入时突然死去,撤去音乐把祭祀进行完毕,这是合乎礼的。
李耳对此略有疑问,不过他更怀疑梓慎对宋国、郑国要发生大旱,产生饥荒的记载。因郑国的星象学家裨,对这同一星象却做出了不同的解释。那这另一种不同的解释是什么呢?史料是这样记载的:
游吉回国,复命,告诉子展说:“楚王要死了。不修明他的国政和德行,反而贪图诸侯的进奉,来满足自己的愿望,想要活得长久能办得到吗?《周易》有这样的记载,遇到《复》卦变为《颐》卦,说:‘迷路又往回来,凶。’大概说的就是楚王吧!想要恢复他的愿望,却舍弃了他的原路,想回来又没有地方,这叫作迷复,能够吉利吗?君王还是去吧!送了葬回来,让楚国痛快一下。楚国在十年之内,不能在诸侯中争夺霸权,我们就可以让百姓休息了。”裨灶说:“今年周王和楚子都要死去。岁星失去了它应在的星次,而运行在明年的星次上,危害了鸟尾星,周王室和楚国要受到灾祸。”
同一天象不同的判断,引起了李耳的疑虑进一步向前推进,他不断地翻着史料,惊喜的发现了郑国大夫子产对梓慎和裨灶的反驳:
十八年(昭公)春,周历二月十五,周朝毛得杀死毛伯过,并取代了他。苌弘说:“毛得一定得逃亡,这一天是昆吾恶贯满盈的日子,这是因为骄横的缘故。而毛得在天子的都城以前骄横成事,不逃亡还等得什么?”
三月,曹平公去世。
夏季五月,大火星在黄昏出现。初七日,刮风。梓慎说:“这是春风,是火灾的开始。七天以后,恐怕要发生火灾吧!”初九日,风刮得很大。十四日,风刮得更大。宋国、卫国、陈国、郑国都发生了火灾。梓慎登上大庭氏的库房向远方眺望说:“这是在宋国、卫国、陈国、郑国。”几天以后,四国都来报告发生了火灾。裨灶说:“不采纳我的意见,郑国又将要发生火灾了。”郑国人请求采纳他的意见。子产不予回答。子太叔说:“宝物。是用来保护老百姓的。如果发生了火灾,国家差不多会灭亡,现在可以救灭亡,你还爱惜什么?”子产说:“天道悠远,人道切近,天道不能涉及人道,凭什么由天道而知道人道?裨灶哪里懂得天道?这个人说的话太多了,哪能说那么准。”于是就不采纳,以后也没有再发生火灾。
“好一个子产!”李耳看到这里,不由得拍案而起,嘴里喃喃重复着子产的话:“天道悠远,人道切近,天道不能涉及人道,凭什么由天道而知道人道?”他这一拍,又想起晋国大夫史墨的话:“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那原文记载的又是什么呢?
赵简子向史墨询问:“季平子赶走他的国君,可是民众却顺服他,诸侯却亲近他,而国君死在外边,却没有人去向他问罪,为什么呢?”史墨回答说:“万物生成有的成双,有的成三,有的成伍,有的有辅佐。所以,天有三辰,地有五行,身体有左右,各有配偶。王有公,诸侯有卿,都是有辅佐的。上天生了季氏,让他辅佐鲁侯,一时间已经很久了。民众顺服他,不也是应该的吗?鲁国国君世代放纵安逸,季氏世代勤勤恳恳,民众已经忘记他们国君了。虽然死在外边,有谁同情他?国家没有一定不变的祭祀者,君臣没有固定不变的地位,自古以来都是这样。所以《诗经》上说:‘高高的堤岸变为深谷,深深的谷地变为山陵。’三王的子孙,在今天变成了庶民,这是王所知道的事情。在《易经》的卦像上,代表雷的《震》卦在《乾》卦之上叫《大壮》,这就是上天的常道……
何以使“高高的堤岸变为深谷,深深的谷地变为山陵”呢?李耳在不断地问着自己。他抓了抓头上本来就不多的白发,不由得扯下十几根。他放在手心摆弄着,仍然解答不出。他又理了理飘冉的白胡子,也扯下了几根,放在手中,这白胡子是比白发长,可就是回答不出他的问题。他把白发和白胡子全扔到地下,推门而出,站在院子里静静地望着天际:已是到了后半夜的时刻,“三森星”明显地偏西了,只有它显得亮些,其它的星竟然全都黯然无光,就像在天空这个黑暗的大铁锅上钉着不太亮的钉子。天空像个锅似的紧扣在大地上,压得大地在这黑夜中不断发出喘息。李耳望着不由得感叹着。自古以来,人们就以为天是圆的,地也是圆的。天如斗笠之状,中空外低,盖在其上;地如鼓盘,中高外低,住于天下;天地之间相距八万里,北极是天的最高点;日月星辰挂在天上,随天的转动而旋转。这种“盖天说”不是有它根深蒂固的传说吧,从这个民族的传说创世的那一天,就已形成了吗?于是,李耳想到了盘古的传说。
很久很久以前,天地还没有分开,宇宙问一片黑暗,什么东西也没有,想来就像一个硕大无比的鸡蛋。盘古的精灵就孕育在其中,他吸收鸡蛋中的养料,发育得非常快,一天变一个样,逐渐长出像龙一样的头,人一样的躯干。身体逐渐长大,而且有了知觉。大约过了一万八千年,盘古终于发育成熟了。他慢慢地睁开双眼,可是什么也看不见,黑乎乎的一团;他想伸伸手脚,可不是碰到这就是碰到那,动弹不得,就猛地把身子一挺,只听“咔嚓”一声,鸡蛋分成了两半。上壳随着阳气上升,下壳随着阴气下降,就形成了天和地。盘古睁开眼睛一看,天空的上半截还倾斜在那里,那是因为上壳和下壳还有粘连的地方,没有彻底分开。他不知从哪儿找来了凿子和大板斧,左手拿着凿子,右手拿着板斧,一会儿用凿子凿,一会儿用板斧砍,总算把上壳和下壳分开了。但上壳浮在空中还有些摇晃,盘古就用高大的身躯像柱子似的支撑了一万八千年,这时天地才算稳住。盘古终于坐到地上休息了。本来很高兴,可他一坐下来才发现地面上仍是一片黑乎乎的,什么也没有。他很烦恼,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当他急得抓耳挠腮的时候,低头看到自己庞大的身躯,便会心地笑了。他要用自己的肉体创造万物。果然后来他用口里呼出来的气变成了风和云,声音变成了惊天动地的闪电霹雷,用左眼变成了太阳,右眼变成了月亮。在一般情况下,天已不再需受支撑,盘占为了以防万一,又用胳膊大腿和身躯变成了支撑天际四边的大柱子和五方的名山,用血液变成了江河,用筋脉变成了道路,用肌肉变成了肥沃的耕地,用头发胡须变成天上的星星,用皮肤汗毛变成花草树木,用牙齿、骨骼变成金属和石头,用骨髓变成珍宝玉石,用汗水变成雨露,用他身上有生命的小虫子变成了人类。
“小虫子”难道就爬不出这坚硬的“盖天说”外壳?李耳清楚记得是有的,那就是“被褐而怀王”的人。别看有些庶民们穿着破烂的衣服,吃着粗茶淡饭,可他们的有些思想,却像珍贵的宝石一样,光彩夺目。有一次,他到乡下收藏书简和采风。作为图书馆长的他,他总觉得周室的藏书量,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需要进一步收集。收集书简的来源一方面是各国史官送来的史料,一方面还得到民间征集。那时民问已有私人著书立说的,他觉得这是极其珍贵的。他来到楚国的一个地方,当收集了一些民间藏书后,这天晚上休息在一个山村里。吃罢饭,他踏着淡淡的月光,准备到村外转一转,看看山村的夜景。当走到一问茅草屋旁边时,只听一个小女孩甜甜的童音:
又是盘古开天地,
开天辟地生乾坤。
生得乾坤生万物,
生得万物人最灵。
四大名山为境界,
天上日月分阴阳。
小女孩唱到这里,嗓子不知被什么东西噎住,咳嗽了好一阵子,似乎把什么忘了,停了好长时间又唱起来:
死于太荒有谁问,
浑身配作天地形。
头配五岳巍巍相,
目配日月晃晃明。
头东脚西好惊人,
头是东岳泰山顶。
脚是西岳华山峰,
肚挺嵩山半云天。
左臂南岳衡山林,
右臂北岳恒山岭。
三山五岳才形成,
毫毛配着花草秀。
血配江河荡荡流,
江河湖海有根由。
虽然这歌声和盘古的传说一模一样,但民间的小女孩用诗歌把它唱出来,可就不是一般的了。李耳轻轻拨开茅草屋,只见一个小女孩正在喂着羊唱歌。李耳便问:“这歌是谁教你唱的?”。
小女孩把头上的羊角辫一翘,盯着李耳反问道:“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偷听我唱歌!”
李耳随口回答道:“我是个过路人,听到你唱的歌非常好听,歌声就把我吸引过来了,叫我跟你认识一下,难道不好吗?”
“好是好,就是我喂的羊太饿了。”小女孩走过来拉着李耳的手,“你能不能再给我的羊扯几把草喂喂!你瞧,我为给羊扯草,把手都划烂了。”说着,她把手伸到李耳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