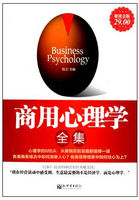我走到那片披着红衣的野地时,风把一片片落叶踢到路边,给我清理出了一条清晰的道路。我停下脚步,盯着道路呆呆地站着,像一棵停止生长的老树。
我大半辈子都在荒野上走过来了。
我一路走,一路问:“你知道哪里是自由国吗?”人们把头像钟摆一样摇来摇去:“我们也在找,如果你先找到了就跟我们说一声。”他们的声音被旷野的风撕得粉碎,像落叶一样在空中飘荡。路上到处是这样的游荡者,这样的声音。我分不清这话是谁说的。他们话未说完,却早已走远。
我没日没夜地走,不厌其烦地问同样的问题,得到同样的答案。后来我不再问了,我想这些游荡者肯定还没找到,不然他们早呆在自由国生活了。于是我把嘴闭得严实实的,像哑巴一样跟着人群晃荡。
走累了我倒头便睡——没有谁催我赶路,他们只顾着自己。那次我醒来的时候,发现跟了多天的一群人不见了。我呆立在旷野上,像棵随风舞动的细草。一只鸟呜叫着从我头顶掠过,我便有了新的方向。我不需要路,我似乎走在空中,像那只自由的飞鸟。
后来,我看到了一片长着红草的野地,还有一条清晰的路。路边有几个老头靠着粗大的树根坐着,望着远处发呆。我走过去,很小心地问,你们知道哪里是自由国吗?老头懒懒地抬起眼皮,说:“你找自由国?再往前走一里就到了。”我怔了一下,不敢相信自己竟然找到了。想到那群人还在路上瞎转悠,我便禁不住兴奋了起来。
我抬起老化的双腿向前狂奔了一里,看见了一面古砖垒起的城墙。墙壁的右角开着一扇木门,我便走了进去。“我找到了!”我喊了一声,然后扯着嗓子吼起了我一直羞于唱的歌谣。
我自由了,我可以在自由国度里畅所欲言、随意做我喜欢的事情。我甚至可以开一片荒地,种上庄稼,一年只顾播种和收获。
我奔进城里,突然愣住了。这里的人们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自由活跃——年轻人和老人都靠着墙根坐成一排,和我来时见到的几个老头没什么两样。看到我进城,有人抬了抬眼皮,而大多数人并没有改变目光的轨迹。我在城里转了一圈,只偶尔看见几个沿街道走动的人。他们只顾低头看路——似乎眼睛长在地上~一完全是一副服刑罪犯的模样。这些人令我沮丧不已,来时的兴奋一下被抹去了大半。
我回到城门口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和我一样兴奋地狂奔进来的年轻人。他喘着气,乐呵呵地问:“这是自由国吗?”我点了点头。他笑着说:
“找了两年了,真不容易呀!”我说:“你这么年轻,来得够早了,我都找半辈子了。”年轻人吁口气:“夹了就好,以后我们就自由了。”
他看到靠墙根的那一排发呆的人,脸上的兴奋立刻被迷惑取代了。怎么都坐着不动?难道我们走错地方了,这里不是自由国?
年轻人走到墙根问那些发呆的人,他们只说一句话:这里就是自由国,以后你自由了。
天黑的时候,靠在墙根的人都纷纷起身,走进了自己的房子。我和年轻人也找了一间空房住下了。第二天,我们找来~辆轿车,在城里溜达了几圈,还骑着马疯跑了半晌。我们无所顾忌地玩乐,为自由欢呼。仓库里有的是粮食,我们不愁吃喝,但我还是开了一块空地,种了些蔬菜作物——这是我的自由。年轻人从马场牵出十多匹马,在房后养了起来,他说这是他最大的愿望。他不分:昼夜地和马群在一起撒欢、戏耍。
那天,他说,他玩累了,想到墙根下坐一会。我说,去吧,那:黾你的自由。年轻人一坐下,就聚精会神地望着地上的一块土,眼睛眨也不眨。
后来,城里新来了一群人。他们问年轻人:“这里是自由国度吗?”
他头也没抬,说:“这里就是自由国,以后你自由了。”
“那你们怎么老老实实地坐着,一点也不自由啊?”
他重复道:“这里就是自由匡,以后你自由了。”
他们便欢呼着在城里奔跑起来。
城里大约每半年都出现一群新面孔,他们欢呼雀跃,做他们乐意的事情;但玩累的人多了,坐在墙根发呆的人也不断增加。有的在墙根找不着地儿,就坐到树枝上,盯着树叶发愣。谁也不会叫他们下来——那是他们的自由。
几年之后,我开的那块地不再像以前一样肥沃了,庄稼都懒得生长了。我对年轻人说,“我不再种那块地了。”他说,“这里是自由国,种不种都是你的自由。”
我把地撂荒,整天背着手在城里转悠,没有二事儿。那天我走到了城外,一阵凉风猛地撞在我脸上,像是给我了一耳光。我抖抖僵硬的身体,慢悠悠地向远处走去。
我不知道自己走了多远。路上有人间我:“你知道哪里是自由国度吗?”
我的头像钟摆一样摇来摇去:“我也在找,如果你先找到了就给我说一声。”我的声音被旷野的风撕得粉碎,像落叶一样在风中飘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