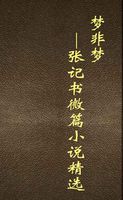五婶的儿子春来突然死了。
死在玉米上浆、西瓜上市时节。五婶当时正在自家地里摘西瓜,等春来把麦秋打下的麦子送到粮库回来,再往城里送趟西瓜。飞来的塌天之祸把五婶吓呆了,西瓜“叭”的一声在地上开了一朵鲜艳的花,人也瘫若一堆泥。
五婶早晨起得早,烧熟了饭,喂了猪,然后喊起春来吃饭。饭后先往城里送趟麦子,听说粮库的麦子快收满了,今天是最后一天,就改了先去果品公司送西瓜的打算。唉,如今的庄稼人种粮难卖粮更难。五婶帮着春来把粮装好,看着他把拖拉机发动起来,上了路,目送着抖动的红点儿消失得无影无踪后,就去了西瓜地。
五婶过日子心盛、能合计,就是命不好。最初,五婶和第一个男人过了不到两年,男人就得冷热病死了。于是,她嫁到了回水湾,男人老实厚道,对她言听计从,一年后,有了独生子春来,一家和和美美的。谁知,那年公社里修水库,第二个男人又被山头上滚落的石头砸死了。当时,许多男人正在崖下吸烟,一块脸盆大小的石头正砸在男人的头上,不偏不斜,他连惊一声都没来得及。
回水湾的人极厚道。见五婶孤儿寡母,日子艰难,就劝她改嫁。五婶出入意料地说:“我命不好,克夫,怎好再去害人。何况,嫁人也得过日子,自个儿一人也得过,命苦,就这么过呗。”
于是,娘儿俩,苦煎苦熬过日子。
五婶在瓜田里一抬头,就看见春来的车在山道上熄了火。春来跳下车,摇着了。然后一转山弯,不见了。
五婶心里寻思,拖拉机开了快三年了,也该大修一回了。修车的事春来同她说过。五婶说:“等忙过这一阵子再去修吧,钱是不能疼的。”
春来的车是在回来时出的事。交粮很顺利。县城里有一条铁路通过,一天到晚也就两三列车,一根横杆,每逢火车进站,就有专人负责将横杆放下,挡住两旁的车辆和行人,火车过去后,再将横杆抬起来。县城不算大,这条来往道上更为冷清,从没出现过什么事,久而久之,管横杆的人也就疏懒了。
那时,春来刚把拖拉机开上铁道,火车便来到了跟前。春来一慌,拖拉机就息了火,要是不息火,也许拖拉机就过去了。春来一下子被眼前的情景吓晕了头,竟然忘了躲……春来就这样去了,连句话都没来得及给娘留下。
五婶一贯刚强,平时从不轻易落泪,而今天的泪囊把五婶平生“积蓄”全部洒了出来。泪水流干了,哭变成号,号得亲戚四邻浑身起鸡皮疙瘩……丈夫的叔伯兄弟说话了:“他婶子,别哭了,想开点,别哭坏了身子。
发生了这样的事,我们心里都不好受哟。”叔伯兄弟在乡政府工作,有些见识,话说得分寸适度。
于是,大伙都劝五婶:“人死也不能哭活,要能哭活我们大伙都帮着你哭,从来没听见哪个人死后能被哭活。”
不知过了多久,五婶才止住哭声,心里觉得豁亮了一些,看看屋里屋外站满了人,大忙的秋,那么多的人来忙里忙外的,自己还哭个什么劲哟!
叔伯兄弟和回水湾的人安排完后事,就去乡里开了个证明,证明车是去交商品粮时出的事。国家规定:交粮车出了事故,当地粮食部门要负责一定的医疗费和丧葬费。还有铁路部门,假如他们及时放下横杆,也不至于出了眼前这件事。铁路部门家大业大,至少要赔车和几千元的抚恤金。
安排好这些事,大家又安慰了五婶几句,就全走了。空旷的屋里留下五婶一个人。昏黄的灯火把五婶的身影悲哀地投在墙上,灯火一跳动,五婶就想起春来。春来文静,安详。每天五婶做针线活,春来就守在她身边,赶都赶不开,可现在他却永远去了……几天过去,五婶脸黄了,体瘦了。想念独生子像中魔一般,让一村人可怜。人们都说,假如不是先去送粮,不是恰巧来了火车,春来是不会死的。
五婶想,即便不是又怎样。五婶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失去了唯一的精神支柱和依托。
五婶并没像人们想象的那么惨。五婶没有寻死觅活,她不让叔伯兄弟去粮局、去车站,儿子去了,她还有这个家,地里还有许多活等着她去干:西瓜、玉米……都等着人去收拾。金秋时节,有多少事等着五婶去千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