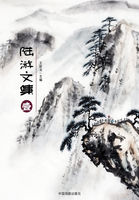印刷术在三国时期诞生。诸葛嶷一改雕版印刷,直接采用活字印刷术。这是印刷史上一个奇迹,印刷术整整提前四百年。诸葛嶷根据北宋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载,采用毕升的泥活字印刷。只用了周围铁框的两块铁板就产生让人匪夷所思的新技术。两块铁板一作印刷,一作排版。方便灵活,易于储存保管,效率远超手写书籍上万倍。
经商有道的刘琰迅速看出这是一项赚钱的大买卖,两人一拍即合。但如此浩大的工程不是刘琰私下就能承办的,订立三七分成后,他们还是以充实国库为由请示诸葛丞相。诸葛嶷也趁此躲过私自贩卖手抄书的罪责。
当诸葛嶷和刘琰将这一成果上书朝廷后,很快得到朝廷重视。刘禅嘉奖诸葛嶷为“巧工”,表彰他在造纸和印刷的成就,这让他的名望进一步提高。
CD出现第一座印刷作坊。这里有全益州最好的工匠,这里有防御森严的士兵。印刷坊成为官府监管的重要对象。这违背诸葛嶷推行印刷术的初衷,他的本意是推广文化,推广印刷术。遭到诸葛亮强烈反对,本着专利法的原则,活字印刷术的保密程度上升为蜀汉一项国家机密。除CD外,蜀郡另外几座大城市也兴建官方作坊。
成批书籍的发行一时间成为蜀汉最轰动的事件。书籍的大量涌现以及价格的低廉,读书很快成为士人津津乐道的常事。CD的学舍如同雨后春笋,这座繁华的都市成为西蜀士人的乐园。诸葛嶷发明书籍的消息不胫而走,造纸和印刷术的创举被以讹传讹地放大。这位年仅二十三岁的青年事迹成为士人传颂的佳话。
不过仇恨诸葛嶷的也大有人在。手抄本退出集市,当初卖书的老板失业,背地里大骂发明印刷术的诸葛嶷。世事总是这样,当新技术诞生,被取代的旧技术拥有者总有些不甘。技术总是需要改良的,没有一成不变的技术,有如没有万古不变的制度。
建兴元年秋,蜀汉的文化事业率先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新气象,教育事业的新格局也随之而来。
书籍的销售状况好得一塌糊涂,诸葛嶷开始担心学舍会像一千年后两宋末期的书院名存实亡。不过还有更令他头疼的事情,顽固守旧分子对欣欣向荣的学舍制度开始发难。
国家兴办太学和学舍,一定要人读书。除非第一,学校中真有学问,是校外所学不到的。其次,法令严切,不真在学校读书就找不到政治出路。否则耗费巨资,收效微弱。书籍广泛流传,各家各户均可买书研读,何必远离家乡跑到京师求学。再者当今的选举都是察举和征辟,学舍求学得到的是学术,得不到仕途。这些学者在一起就会针砭时弊,赚取名声。这样有失治学精纯的本意。
学舍成为朝野不少守旧人士抨击的对象。他们认为学舍的兴办是好大喜功,华而不实。
杜琼等人眼光毒辣,看得很准。东汉时期,党锢之祸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东汉时期,党人劫持选举,而太学为私党聚集和声气标榜之地。此时学术在社会上渐渐占重要地位。功臣外戚及官吏多遣子弟入学。于是纨侉子弟掺杂其中,不能认真研究学问,接近政治,成为《后汉书儒林传》所说的“章句渐疏,多以浮华相尚。
自古任何一项制度都是有利有弊,上位者懂得驱利避害,因此才有历史上诸多改革创新。倘若因为顾忌弊端就贸然舍弃学舍之风,将会给新建立的蜀汉政权一头冷水。岌岌可危的蜀汉需要活力,百废待新的事业需要人才。诸葛嶷忧心忡忡,提笔写下《论学篇》上疏丞相,坚持学风建设。
诸葛亮与诸葛嶷所见略同。犹为重要的是他深深认识到西蜀人才的短缺,以及西蜀文化较之中原非常落后。将来推行科举制度,这就会变成障碍。
实行科举制度必定以教学为先,社会上只有真才实学的士人增多,科考才能得以施行。自古典章名目繁多,不可能一一尽得,那么就有取舍。这也是科举制度值到唐宋时代才兴盛的重要原因,印刷术发明以前书本罕贵,各人得书有限,学识也大不如后代渊博。而学舍制度加上印刷术的诞生,使得一所学校可以容纳数十部书,取长补短,博采众精。譬如将各家子弟拥有的书籍全都搬到学校供就学弟子资源共享。学舍老师水平有限,但启蒙教育,引导弟子读书依然不可或缺。
朝野某些人士也有自己的见解。庙堂之上以蜀郡CD人杜琼,江湖之远以梓潼涪人杜微为代表的士人,跟新近推行的学舍制度大唱反调。诸葛亮终于忍无可忍,暗中授意诸葛嶷到学舍讲课,重视教育的同时恨恨回击反对派的呼声。
第一个邀请讲学的是侍中廖立。他闲暇之余兼职管理城北的“潜龙学舍”。“潜龙学舍”取《易经》乾卦:潜龙勿用之意。然而学舍里所学弟子都是荆楚名宿之后,将来都是国家倚靠的人才,哪里像无用之人。学舍无论名气规模在CD仅次于太学,为各大学舍的冠首。不得不引起诸葛嶷的重视。
廖立属于荆楚派代表,诸葛嶷也被认定荆楚一派。没有半点阻力,也不敢半分推辞,诸葛嶷爽快答应到学舍授课。
很难想象古代士人对学问的兴趣有多浓厚,书似乎变成他们精神寄托的一部分。就好比粮食之于农夫,知识是士人的精神食粮。不可或缺,还要推陈创新。月旦评就是自开学舍后,西蜀学者智慧的结晶之一。
西蜀学者追求的不单纯是儒家学说。在这个乱世,他们需要更多更有用的学说,法家的治国,纵横家的捭阖,以及黄老的清净无为、杂家的朴素哲学都成为他们追捧的热点。当然很难动摇儒家学说的统治地位,儒学内部延续着东汉时期的分化。关于今古经学的争辩自东汉末党锢之祸后重新燎原。
在学舍的一周里,诸葛嶷惊奇地发现许多事情似乎偏离原来的初衷,背离他学以致用的原则。许多事情已经不是他一个人就能把握的。就在开学的第三天,他在讲授儒学修身之道时,就遭到学生问难。幸亏他机灵过人,勉强敷衍过去。双方价值观的巨大差异,让他隐隐感觉到还原儒学真谛的理想在现实面前不是那么顺风顺水。还原儒学精华的出路在哪里?如何凭借一人之力找到志同道合的人?诸葛嶷陷入深深的忧思。